我,赵玉成,一个战败国公主。
我被远送到西魏和亲,嫁给他们最阴郁残暴的七皇子,一个残废。
入宫之前,我还要在暗殿里脱去全部衣物,接受身体检查。
与其说是一种安全保障,不如说是一种羞辱。
柳承泽是随我远嫁而来的侍卫,他看出了我强装镇定的紧张,所以在我进去之前,他在我耳边轻轻安慰:
「不要怕,你身体的每一处痕迹我们都已处理过,和真正的玉成公主一模一样。」

没错,我不是真正的玉成公主。
真正的公主金枝玉叶,国君国母又怎么会忍心让他们最受宠爱的女儿远嫁敌国、生死未卜?
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计划:找一个人代替公主。
而我就是被选中的替代品。
我和公主容貌相似,又毫无背景,出事之前我只不过是一个女奴。
即便从这世上消失,也无人在意。
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宫里请了最好的神医为我换脸、换皮。
割肉刮骨的痛楚,无需多言,即便多年之后梦到,我都会一身是汗地惊醒。
被扒掉一层皮之后,又有宫人培养我的言行举止,让我做到和真正的玉成公主一分不差。
当我穿戴华服坐着马车,进入西魏国都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分得清我和真正的玉成公主。
当然,事后那些知情之人也全都被「处理」了。
在这场盛大的伪装里,我和他们全都一样,本质上也不过是一只受摆布的蝼蚁。
我能活下来,只不过是因为我是唯一有价值的那个。
我被送进西魏皇宫半个多月,没有见到任何重要的掌权人,也始终没见到我那位未来夫君,七皇子薛珩。
但我听了他的不少传闻。
他的母亲出身并不高贵,也不受宠。他出生之时正值战乱,皇帝在外行军,他是在军营出生、军营长大的。皇帝对他并没有什么管教,所以他的举止教养也和那些从小长在深宫中的兄弟们无法相比。
七岁时,因为遭遇伏击,皇帝将他丢在营地当中。他在兵乱中侥幸逃出,但从那以后就跛了一条腿。
也许是因为出身,也许是因为那条腿,总之,他是个阴晴不定凶狠阴鸷的人。
我要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凶残,是在我们的大婚之夜。
那天晚上,他险些将我打死。
没有任何缘由。
从头到尾,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哪一句话冒犯了他。
一开始,一切都还像一对寻常夫妻那样,稍显生疏、但礼貌地进行着。
他随口问我一些姜国的风土人情。
我则按照一个公主的视角,自然地叙述给他听。
他安安静静的时候,是个很让人心动的青年,俊美温柔、周到体贴。
坐着时,看起来和常人完全无异,只是一旦站起来走动,就会暴露出两条腿的长短不一。
那种沉默的摇晃的步态,使得他周围动荡出一种阴郁的气息。
兴许是我那随他行动的自然一瞥,让他误以为我多看了一眼他的腿。
突然之间,我眼前的世界就颠倒了。鲜红的光影在眼前跳动,一切感官因为身体的急剧被拖动而全部留在了身体后面。
我的脚不在地上,腰间被一只铁一样的手臂箍得生疼,我整个人被拽倒在地。
耳边只来得及听到一阵风声,随后,一根钢鞭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仿佛被拦腰斩成两半,下意识张开嘴巴像要喊疼,却被一股腥气堵在了喉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在第一轮痛苦刚刚传遍四肢百骸的时候,第二鞭、第三鞭就已经落了下来,我像粘板上的鱼在地上痛苦翻滚。
而我的丈夫,那个刚刚还与我谈笑的男人,此刻就带着一脸想要将我置于死地的阴冷,居高临下看着我在他脚下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那一场鞭打最终以我疼晕过去作为结束。
我醒来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柳承泽。我不知道自己晕了多久。
这期间没有人来看护过我。
一个刚刚以异国公主的身份嫁进皇室的女人,在新婚之夜被打得半死不活,就这么被丢在偏殿的一个矮房间里,像一团烂布,无人问津。
等到我能下床之后,我随着薛珩去拜见我所谓的父皇母后。
那一对高坐在殿上的中年夫妻,以一种雍容华贵的姿态面见了我。
没有人问起我苍白的脸色,虚晃的身子。
所有人脸上都是一派的从容,一派的和平。
在言谈的间隙之间,皇帝提起我和七皇子在新婚之夜发生的小小「争执」。
他以一种长者的慈爱安慰了我,然后避重就轻地对七皇子进行了一番训诫,提醒他作为一个丈夫,要懂得尊重爱护自己的妻子。尤其在我是姜国和亲公主的情况下。
当时,太子和太子妃也坐在我们上首处,观看了全程。
太子笑着说:「七弟毕竟军伍出身,举止不似我们平常兄弟。七皇妃往后需要多担待他些。」
太子妃坐在旁边,捂嘴笑看我们。
而那个在我面前凶相毕露的丈夫,面对来自兄嫂高高在上的调笑,此刻却只是神色恭顺,笑而不语。
真有意思。太子看不起七皇子,太子妃看不起我。
我们这对又残缺又窝囊的夫妻,以一种近乎凄凉的方式被放置在了同一国里。
不同的是,七皇子毕竟比我好一些。至少他还可以折磨我。
这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折磨我。
独自退居到院子里时,我披着薄薄的衣服,对着一池塘的残荷发呆。
我问身边的柳承泽,如果今天是真正的玉成公主遭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做?
柳承泽一言不发。
从他跟随我嫁到这个地方,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一言不发。
他像一个影子一般跟在我的身后,在我快死的时候拉我一把。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站在一个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对我遭遇的种种痛苦不闻不问。
不等他回答,我自顾自笑了:「不,真正的公主从一开始就会有人保护她,根本不会让她遇到这样的事。」
就像我替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她免于遭受我所遭受的。
那之后我就深刻意识到,姜国没有我的安身之所,这座华丽的宫殿里也没有。
假如我想活下去,我就得想办法在这个地方立足,在这些人当中谋得一份尊重。
否则,往后的人生,我将生不如死。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个西魏人。
西魏最早是南迁的草原部落,虽然和汉族通婚多年,但仍旧保持了自身的许多文化习性。
我在半年多时间里,努力学习西魏国的语言、风俗、习惯。我把自己彻底融进周围的环境当中。
半年之后,在西魏国传统的祭祀庆典之上,我以流利的西魏语,参与主持了仪式。
大典之上,我随着丈夫举刀祭天,然后娴熟地划开牛羊祭品的肚子,按照既定的规格,将煮过的肉分给坐下远近的臣子们。
整个过程中,我举止自然,态度虔诚。我比最纯正的西魏人还要认真。

皇帝和皇后看着我,不住微笑点头。
只有太子妃脸色难看。
她已经嫁过来两年了,但始终还是吃不惯西魏的食物。假如没有一个我这样对比着,倒也显不出什么。结果我来了这么一手,她一时就被衬得无所用心。
但她的喜怒与我何干?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要讨好的,是这后宫之中我所能接近的最高权力者——当今皇后。
对待皇后,我极力投其所好。从穿衣打扮,到举手投足,再到爱好习性,我满足了她对一个儿媳妇的全部要求。
很快我就取代了太子妃,成为她陪伴出行的首选。
至于皇帝和太子,反倒不必太过费心,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将我放在眼里。我只需要符合他们的期待,做一个为了谋生而逆来顺受、乖巧听话的外来皇妃,就足以讨到他们的欢心。
我花了一年时间,同整个皇宫上上下下都相处融洽。从可以被任意践踏的底端,爬上了不可或缺的中心位置。
可是唯独一个人,我始终无法取得他的信任,那就是我的丈夫。
半年、一年……我在他身上投入无限的耐心和柔情。
我一直等着他相信我,相信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不足以戒备的女人。
他有时候好像吃这一套,有时候又根本不为所动。更多的时候是不为所动。
他会在我努力讨好他的时候,用一种轻蔑的微笑看我。
那表情不加掩饰的就是在说:「你无非就是这点本事了,来,我的皇妃,让我看看你还想演什么把戏?」
我在讨好他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一把打破手上的瓷杯,用碎片捅进他的胸口、划破他的喉咙,割破他那双漂亮的、带着讽刺的眼睛。
但是我要忍。
皇后也好皇帝也好,这个男人才是我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的最大筹码。
有一天他回到寝宫的时候,看上心情很好,我便迎了上去。
我早已听说了,今日的狩猎之上,他赢了太子,得到了皇帝心爱的玉如意作为赏赐。整个皇宫都在传七皇子的出彩表现。
我笑着恭喜他:「殿下勇猛卓群,最有父皇之风。」
他接过我递过去的醒酒汤,眉目微挑,看起来在今日的酒宴上喝多了些,有些醉意。
忽然,他一把将我拉到腿上。
我呼吸一滞。我们在过去从未靠近过彼此的身子,这时却忽然有了一个夫妻之间的距离。
薛珩将头倚在我的脖颈间摩挲,低喃道:「那皇妃觉得,我和太子相比又如何?」
这是个惊心的问题,即便他的语调再漫不经心,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自顾自说下去:「父王不止一次说过,那么多儿子当中我和他最像。可就因为我是个残废,出身又低,所以太子之位,就白送给了我那文弱优柔、虚荣肤浅的大哥,你说我怎么能甘心?」
我身体僵硬,完全无法接话。
他抬起头,带着戏谑的笑意看我:「怎么,一句真心话都不敢说了?你不是我的妻子吗?一天到晚说着和我同心同德,原来那些话都是假的?」
我勉强笑道:「我是怕殿下喝醉了,隔墙有耳。」
他贴近我,我听到他轻声细语地说:「是,我是醉了,那皇妃知道怎样醒酒最有效吗?」
他呼吸落在我耳畔,最亲昵的姿势,却让我犹如和野兽贴近而浑身轻颤起来。
就在这个最温存的时候,他忽然一把推开了我,将我连拖带拽地拉出寝宫。
外面天寒地冻,我只穿了薄薄一件內衫,迎面而来的冷风像刀一样刮在身上。我的手脚一下就麻痹了,动弹不得。
可他根本就不管我,甚至看也不看我。夜色下他将我整个人拖着往不知名的方向走,侧脸在月光下显出一种妖异的森冷。
那种身体无法控制的感觉,让我忽然间回忆起大婚之夜的遭遇。
我浑身冰凉。
我被他带到了荷花池边。
冬天里池塘结冰的寒气一阵阵向外冒,一潭黑水深不见底,如一张大口。
薛珩回头看我,露出森然的微笑:「夜间风寒露重,一跳下去,马上就能清醒过来了,皇妃,你替我试试?」
我什么伪装、什么温顺也顾不得了,我拼命挣脱他的手,咬着牙强笑道:「殿下你不要开玩笑了。这种天气跳下去……我会死的!」
他不顾我的挣扎,看似温柔实则强硬地扯过我。他俯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真正的玉成公主是不会水的,你千万不要自己游上来。」
这句话给我造成的雷击让我愣在原地,忘了挣扎。
就在那短短的一个空档,他一把将我推入水中。
身体被冰水包裹的一瞬间,仿佛有千万把刀割开我的皮肉。
隔着黑色的水面,我看到薛珩被水光所扭曲的脸,一脸冷漠地从高处看我。
已经有无数侍卫被惊动,纷纷跑来,看到站在岸边的薛珩和水中的我,他们惊讶,然后沉默,然后退居一边。
没有人对我伸手。
求生的本能使我迅速划拨水面,我的大脑已经疼得一片空白。不是冷,是疼,同时那种疼痛的感觉在迅速僵硬、失真。
我要游上去,我得马上离开!
可是当我接触到薛珩比水更冷的眼神,心里的清醒一下子压过了身体的疼痛。
你是想要眼前的活命,还是想要长久的活下去?
身体已经仿佛被撕裂成一块一块,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我带着破釜沉舟的对薛珩的恨,违逆身体的本能,压制千刀万剐般的痛楚,强迫我自己,一点一点沉了下去,被黑暗吞没。
再次醒来时,我只是默默睁开了眼睛。
我知道我没有死,我恨我为什么没有死。
但马上,我又看着头顶的帐幔笑了,老天都不让我死。你看,我又活下来了。
薛珩来看我的时候,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九死一生之后,我连掩饰都没有力气。他那张冷漠而扭曲的脸,是我在濒死前一刻最后印在眼睛里的东西。
我知道此刻我的脸上充满了掩盖不住的警惕怨恨。
我衣衫单薄,脸色惨白,头发纷乱,这一刻我一定像一个凄厉而无力的怨鬼。
而他看着我那样子,却温柔地笑了。
他亲手替我端药,用一种摆弄娃娃般的耐心,一口一口喂我喝了下去。

我若不喝,他也不生气,只是拿着汤勺,默默等着我。
他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做事欠些考虑,他希望我不要记恨他。
他又说,我一定是真正的玉成公主,没有人可以在那样寒冷的水池里假装自己不会水。
「假如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那这个人,可真是连我都要心生畏惧了。」他望着我,笑得宠溺而愧疚。
当我喝完他为我准备的药汤,他收起碗勺。房间里的氛围因他那种脉脉的动作而显出一丝温情。
但仅仅是一瞬间,仅仅是将视线从碗里抬起、落到我脸上的一瞬间,他眼中的所有温存又敛为无情。
我一直吊着的心,因他神情的忽然变冷而沉了下去。
他又要做什么?又要做什么?
他看着我,嘴边带着冰冷的微笑。
「你喝了鼠屈草,肚子不疼吗?」
我仿佛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了脚。
玉成公主吃不了鼠屈草。
他在这里等着我。
大局已定,我被他抓住了。
他望着浑身发抖的我,仿佛一只猫逗弄指尖的老鼠,脸上没有过激的愉悦,只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得意。
我多蠢,连死都不怕,却轻而易举就被表面功夫所迷惑,掉以轻心,被他捏在手里。
他俯下身,在我僵硬的脖颈边,一字一句缓缓地说:「你说,若是嫁给我兄长,姜国的皇帝敢这么做吗?」
他在我耳边发出轻轻的一声冷笑,「不过是因为是我,一个残废的、不受重视的庶出皇子,所以就随便敷衍,送了个低贱的假货过来。」
我默默握紧了拳头,对这句「低贱的假货」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最后的最后,他对我下了最终宣判:
「我不会让你在我手上好过的,我的皇妃。」
那一次之后,我病了整整半年。
我恨薛珩。
每一天我都想他死。
皇帝因为他把我推下水而重重责罚了他。
我拖着病体去为我的丈夫求情,展现出一个妻子最大的包容懂事。
那次受罚之后,薛珩对我确实很好了。他变得温柔体贴,和我相敬如宾,像一个真正的丈夫。
柳承泽说,即便薛珩知道我是假的也没关系。短时间内,西魏国再和姜国开战没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和亲公主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名头。
我冷笑。
不错,姜国的确不会再遭遇战争,可是我呢?
一个两头都无人在意的假货,我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死在薛珩手里。
所以我一直想着,与其等死,不如我先下手。
秋天围猎的时候,我等来了一个机会。
我和七皇子的队伍受到了行刺。
队伍被冲散,马车被撞翻,当一切混乱结束之后,已是深夜,我从车里爬了出来,看到车夫死不瞑目地大睁着眼睛,倒在我面前。
我独自一人沿着溪流,踉踉跄跄地往水流尽头处走。
又饥又冷之下,我一个不稳,一头栽倒。草丛后面是空的,我滚下去,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搅在了一起。
短暂的昏沉过后,我醒过来,发现头顶只有一束天光。
我掉进了一条深深的沟壑里。
还来不及为孤立无援感到恐惧,我就先透过模糊的光线,看到石壁上还倚靠着一个人影。
那是薛珩,我亲爱的丈夫。
他脸色苍白,呼吸微弱,腰间的衣服上透出了大片血迹。
那个时候,我忽然顾不上自己虚弱饥饿的身体,我只想笑。
薛珩,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有今天,落到我手里?
薛珩即便在重伤之下,仍然保持了非常的警惕。仅仅是来自我的一点响动,就让他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看清面前之人是我的瞬间,他眼中滑过一抹幽深的暗色,黑宝石般的瞳孔有轻微的放大。
我仔仔细细盯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捕捉到任何一点点戒备或恐惧的神色,并从中获得快感。
我知道他一下子就会醒悟过来眼下的局面——在这个狭窄密闭的空间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虚弱而我健全。我占尽上风,而他只能受我摆布。
我假惺惺地问他,「殿下,你觉得伤势如何?」
我渴望他与我虚与委蛇,渴望他脸上流露出一点点不安和讨好,就像我曾经对他做的一样。
可他看穿了我的这点小心思。他不领情。
他微微眯着眼睛,嘴角带着一抹虚弱而嘲弄的笑意,「皇妃,你知道自己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很可笑吗?」
这男人,竟然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还要这样高高在上地看我。
我咬着牙,也笑了。
我温柔而和煦地问他:「殿下,你的命在我手里,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他看穿我。他不吃我这一套:「你有本事杀了我吗?你有那个胆子?」
我怎么能容忍他在这个时候还继续看轻我。
我说:「我是不能杀了你,但我总可以有很多办法折磨你。」
我走到他面前,像他曾经对我那样,居高临下地俯下身。
因为高度差,他必须仰着头看我。苍白的脸,漆黑的眼睛,使他在那一刻显出一点任人宰割的表情。
我抚摸着他的脸庞,学着他曾经对我的语气,轻声对他说:
「我不会让你在我手上好过的,我的殿下。」
这个任人摆布的薛珩,是我遇到他以来最讨人喜欢的薛珩。
我用山洞里能找到的草药替他止血,同时我狠狠戳进他的伤口,欣赏他一瞬间变得惨白的脸色。
我自己摘果子吃,但不让他吃东西。我在他口舌干裂失去意识的时候,让他喝山洞里的泥水,吊着他的一口气。
在这里,我是他的施虐者,我也是他的救世主。
我在熬着他的意志。我得让他认输,我得让他屈服于我。
我一边折磨他,一边软着语气对他说:「拜托了,殿下,让我照顾你吧。」
我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拉锯战。
如果我不能在这个山洞里击溃他、收服他,那么一旦我们离开,我面临的只会是更加暗无天日的地狱。
可这个男人,这狗男人,他的心就仿佛是铁打的。
柔弱屈从对他不管用,强势暴虐对他也不管用。
他看我的神色永远不变。他洞穿我内心随时间逐渐加深的焦虑、恐惧。
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瞧,我们俩,到底是谁先害怕,谁先用光底牌?」
我们俩在一方狭窄的山洞里和对方死死耗了两天。
他伤势严重,我筋疲力尽。
半夜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一抹月光照进山洞。
我忽然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清醒透亮。
我坐起身来,拿着一只匕首走近了薛珩。
我驯服不了他,我迟早会被他咬死。我不想再受他折磨。

薛珩有着高度的敏锐,他一下子从昏睡中睁开眼睛,看到我在阴冷的月光下,拿着匕首朝他逼近。
我脸上冷峻的表情使他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女人。
他白着脸,抬起眼皮,带着微冷的笑意注视我,「用匕首杀人可不够干净,我身上的刀口你要怎么解释?」
我一下子从冷静的冲动中被拔出来。
我还是拿着刀,但转而将视线落在他细白的脖子上。
「勒死也是一样,你觉得不会留下痕迹吗?」
我的呼吸渐渐急躁起来,有种厌烦的感觉。
而他还是不紧不慢,他以一种让人浑身发冷的置身事外,指导着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由我自生自灭。我受了重伤,若不换药,不喝水,两天就会虚弱下去。我会在距离你咫尺之遥的地方一点一点失去血色,失去呼吸。」
「闭嘴……」
「只是在我死后,你可能还不知道要和一句尸体共处多久。」
「闭嘴。」
「我会当着你的面,一点一点腐烂……」
「闭嘴!闭嘴!」我受够了,我从他腰间抽出被盘起的长鞭——他曾经狠狠抽打我的那一根。
一鞭子落下去,他的脸被打到一边,苍白的脸上现出一条血痕。
这一鞭子忽然让我所有厌烦的情绪都被打通了,我浑身上下被一种报复的快感所贯穿。
我忽然觉得,我陪他耗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在他身上打下这鞭子。
就像他曾经对我所做的那样,我用尽浑身的力气,紧接着在他身上落下第二鞭,第三鞭……
所有的怨恨,愤怒,恐惧,我将其贯穿在手臂上,我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
直到我用光了力气,我丢开鞭子,跌坐在他面前,死死盯着他,痛快地笑了。
他比我更糟糕,被我打得几乎只有出气的份。
可他却忽然低着头笑起来,笑得厉害了,开始咳嗽,咳出一嘴血沫。
他说:「两年了,你终于也有忍不住的这一天。」
是,两年,我忍受了两年,整整被他折磨了两年,却似乎比一辈子还要长。
我不知道我是输了还是赢了。
我恨恨地盯着他,恨恨地质问: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只是想要活着而已,我有什么错?我来到这世上天生低贱,被人看不起,是我自己能选的吗?我被人选择,随波逐流嫁到这里,是我能选的吗?我嫁给你,是我能选的吗?」
我的问句一句比一句用力,问到最后,几乎是用上了全身的力气。
太恨了,真的太恨了。
薛珩的半张脸掩在阴影里,看不出表情,但我知道他在盯着我。
一阵风吹过来,我才感到脸上凉凉的,我居然在他面前流眼泪,真没用。
我不指望那晚的爆发和哭诉,可以让薛珩就此对我改变态度。
但我知道,他不会无动于衷。
我在他面前掉眼泪时,说的每一句话看似发泄,其实都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他和我一样出生低贱,这些话最能引起他的共鸣。
我也知道,当我拿着匕首靠近他的时候,他看似无力反抗、决定认命,但他的袖子里正藏着一把弩箭,对准了我的喉咙。
也幸好他当时手上有武器,不然我可能真的会失去理智杀了他。
被困在山洞里的第四天,我和薛珩开始交谈。
是那种正常的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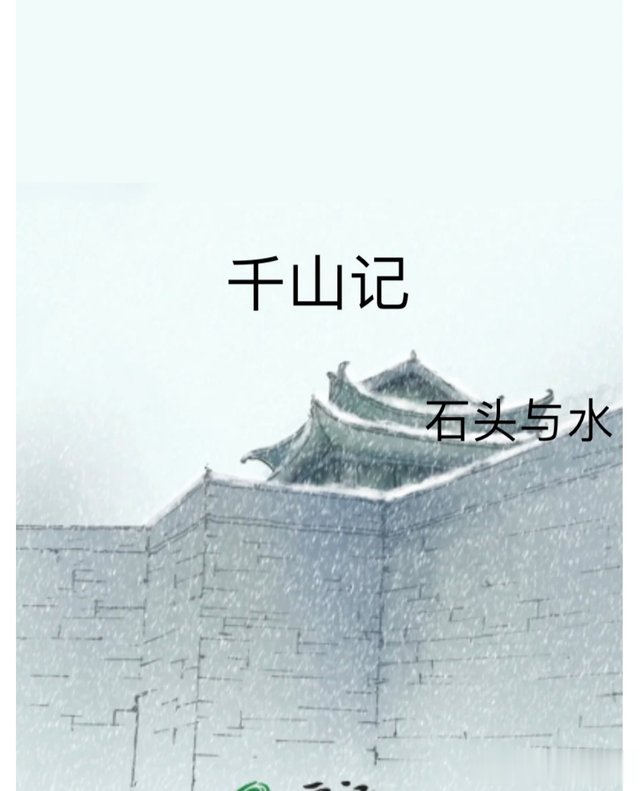


这才是高位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