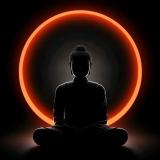1919年的印度旁遮普邦,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愤怒。
2月6日,英国殖民当局,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法案允许警察无需证据即可逮捕“可疑分子”,甚至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
这一法案,无疑针对的是那些为了印度民众公平待遇的积极奔走的活动者。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法案的颁布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印度人的怒火。
旁遮普省,曾是英国殖民者眼中的“模范省”。然而,针对这次法案,该地区率先爆发抗议,3万民众涌向阿姆利则市政厅,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者。
4月13日,约5万人聚集在札连瓦拉园广场。
他们中有老人拄着拐杖,有妇女抱着婴儿,甚至有人带着午餐盒准备聆听演讲。
下午5时15分,戴尔将军率领149名士兵封锁出口,并对着密集人群连续扫射10分钟,直到子弹耗尽才撤离。
一瞬间,自由的广场浸满血色!
“有人跳井逃生,井里塞满尸体。”
“婴儿趴在母亲遗体上哭,血水浸透了纱丽。”
英国官方宣称死亡379人,但收尸者发现,仅焚烧的遗体就超过500具。
戴尔将军屠杀后竟说:“我开枪是为了拯救整个旁遮普。”
而英国议会最初将他誉为“果断的英雄”,直到全球舆论哗然才假意谴责。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都看不下去:“殖民统治就是一群恶棍,假装自己是圣人。”
这种虚伪的殖民逻辑,在印度人心中刻下永不愈合的伤口!

“我们种的棉花被抢走,自己却穿不起布!”英国统治印度200年,嘴上喊着“文明开化”,手上却攥着三把刀,在抢走印度的富裕产出后,更割裂了整个社会:
法律歧视
《罗拉特法案》只是冰山一角。在法案中,除了无需证据就可逮捕“可疑分子”外,荒谬的事被捕者连聘请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殖民官员甚至扬言:“印度人不需要争议,只需要服从。”
日常法律规定,印度人不得进入白人专属的餐厅、俱乐部,连火车站都分“白人车厢”和“本地人车厢”。
一名英国军官曾嘲讽:“让印度人挤在闷罐车里,他们才会记住自己的身份。”
甚至在法庭上,他们使用“双标”的展露种族的歧视,印度人的证词效力自动低英国人一等。在加尔各答曾出现10个印度人的证词竟然不及一个英国地主的一面之词。
经济吸血
殖民统治者强迫印度农民废弃粮田,种植棉花、靛蓝等原料,低价收购后制成工业品再高价倾销给印度民众。
19世纪中期,为防止竞争,英国甚至颁布《纺织品禁令》,摧毁印度传统纺织业,导致数百万手工业者沦为乞丐。
一名孟加拉织工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折断我们的纺车,却让我们花钱买曼彻斯特的布料。”
更残酷的是土地政策。
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定居制”,将土地税提高至收成的50%-70%。仅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就有1000万人饿死,而殖民政府反而趁机收购破产土地,扩大种植园规模。
文化阉割
英国殖民者深谙“分而治之”挑拨离间的毒计。
他们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划为不同选民类别,在旁遮普设立独立行政单位,让锡克教徒与主流社会割裂。
最终造成各教徒、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割裂,冲突不断。
同样,这种策略在文化领域则显得更加阴险和隐蔽。
英语,在印度政府被强加为官方语言,印度本土语言遭贬低。
种姓制度被刻意保留,低种姓人群甚至被禁止进入英国人的俱乐部。正如甘地所言:“他们给我们戴上手铐,还让我们感谢手铐上的雕花。”

就惨案发生时,49岁的甘地正乘坐火车赶往阿姆利则。
当他站在弹痕累累的广场上,颤抖着捧起沾血的泥土:“这是英国人亲手埋下的独立火种。”
非暴力不合作
1920年,甘地发起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他号召印度人抵制英国商品、辞去公职、拒绝纳税。
在孟买,家庭主妇当街焚烧进口布料;在加尔各答,学生集体罢课游行;连殖民政府的印度籍职员也纷纷递交辞呈。
一位英国官员在报告中哀叹:“我们的法庭空无一人,监狱却人满为患。”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但是,他的理念却充满矛盾。
当农民烧毁警察局时,他绝食三天要求停止运动;当英国承诺战后给予自治时,他又号召支持战争。
这种“以德报怨”的策略即遭激进派质疑,却也让殖民者陷入道德困境——镇压越残酷,越暴露统治的野蛮性。
精神觉醒,比子弹更强大的力量
阿姆利则惨案仿佛迎面泼来的硫酸,彻底撕碎了印度人对殖民者的幻想。
到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时,就连英属印度军队都出现骚乱、倒戈。
一名起义士兵在法庭上说:“我曾为英国征战欧洲,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敌人就在眼前。”
这种觉醒如野火燎原,漫漫不息,至1947年独立前夕,英国每天需耗费400万卢比维持镇压,但英政府最终不得不承认:“我们再也买不起一个帝国了。”

阿姆利则的枪声惊醒印度,震撼世界,也撕碎了帝国文明的面纱,它敲响了大英帝国的丧钟。
殖民体系的崩裂
历经血腥残酷的二战,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千疮百孔。
它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帝国梦想,让它在这个残破的世界中重新崛起,独占利益的鳌头。
甚至,有的时候,在美苏两大力量的夹缝中,这头英格兰雄狮有了一种暮年之感,它的爪牙不再锐利,连脖颈之上隐隐有了枷锁的光环。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勾结法国、以色列入侵埃及,却在美国压力下狼狈撤军。
这场闹剧似的战争,让世界看清,昔日的海上霸主,如今不过是苟延残喘,变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儿。
联邦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1947年,印度独立。
1948年,缅甸、锡兰相继独立。
1960年代非洲殖民地在民族觉醒浪潮中全面脱离帝国统治。
1982年,英国靠马岛战争短暂重温帝国旧梦,但这场“用航母争夺羊群”的战争,以损失军舰和商船的惨烈结果,彰显着夕阳最后的余晖。
如今的英国,蜷缩在不列颠群岛上,连欧盟成员身份都已失去。
而那个曾覆盖全球3350万平方公里的“日不落帝国”,最终只剩下53个松散联邦国,其中16个仍将英国君主视为元首——这与其说是殖民统治的延续,不如说是一曲帝国的安魂曲。

如今的札连瓦拉园,弹孔墙上依然嵌着1650颗子弹的痕迹。
英国政客们的“遗憾”仍在敷衍着那段不光彩的经历。
但历史早已给出判决,当戴尔将军扣动扳机时,同时,他也亲手点燃了埋葬帝国的火把。
今天的印度,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实力证明,殖民者的枪炮可以摧毁肉体,却永远打不垮一个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灵魂。
正如那首在惨案后传唱至今的民谣:“我们的血浸透土壤,来年这里会开出自由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