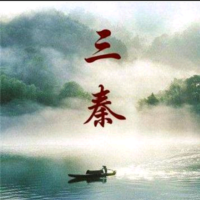声明:本文的所有内容皆是参考网络资料并融入个人观点而创作的,特此告知。 一位红军烈士的遗孤由地主家庭抚养长大,十几年过后,亲生母亲寻来,孩子却立刻跪地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 在1937 年的一个寒冷夜晚,屋外北风怒号,田野和村庄都被纷飞的大雪淹没。王学文在火炉边坐着,怀中抱着刚刚出生没多长时间的孩子,妻子秦子莲轻手轻脚地为婴儿把被角掖好。在这温馨的房间当中,另有一个孩子,正躺在他们备好的摇篮里,睡得十分安稳。这个孩子并非他们的亲生子女,而是一位红军母亲交给他们抚养的遗孤。

秦子莲凝视着酣睡的婴儿,轻声向丈夫发问:“真打算养吗?”王学文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投向窗外漆黑的夜色,紧咬着牙颔首:“养!”为何一个地主家庭会做出抚养红军孩子的决定?这件事要从井冈山讲起。吴仲廉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普通家庭之中。她天赋聪慧,尽管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可父母深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于是节衣缩食支持她求学。

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成功被衡阳市立第三女子师范学院录取。在此处,她不但接受了新型教育,还接触到了革命理念。她有位同学叫曾志,是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者。曾志常常组织学生投身于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当中,积极倡导男女平等。二人彼此欣赏、互相敬重,没过多久便成了好友。正是在曾志的带动之下,吴仲廉走上了革命之路。当她与曾日三相遇之际,命运的转折时刻来临了。

曾日三最初在旧军阀处效力,其与吴仲廉所在的队伍处于敌对状态 。然而,战争使他们得以结识,同时也让曾日三认清了现实。最终,他毅然投身革命,与吴仲廉一同并肩战斗,二人还在井冈山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婚后,二人相处时间较少、分离时间较多,直至1936年,吴仲廉怀有身孕。然而,这样的时代并不能让她安心地等待分娩。

西征即将开启,战事吃紧,她没办法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孩子该如何是好?送给什么人抚养?曾志给出了一个大胆提议——将孩子托付给一户地主人家。吴仲廉的最初反应是予以回绝。她们的革命目标中,有一项便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又怎能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个地主呢?然而现实并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空间。

王学文,实际上这位“地主”与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地主存在差别。他出身富贵之家,却并非那种巧取豪夺、鱼肉乡里之人,在当地颇受好评。更为关键的是,他与妻子多年来一直没有孩子,此时正急切地盼望着能有个孩子。就这样,在那个狂风裹挟着雪花肆意飞舞的夜晚,吴仲廉忍着内心的不舍,咬着牙将孩子送到了王家。

收养一个红军的孩子?这难道不是给自己增添麻烦吗?然而他的妻子秦子莲心地善良,瞧见吴仲廉跪在地上,满脸泪痕地苦苦哀求,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孩子获赐新名——王继曾,饱含“承袭曾家血脉”之意。自那以后,这个地主家庭里增添了一个“红色身影”。王学文夫妇对待王继曾就如同对待亲生子女一般,将最好的食物、最暖和的衣服都给予他,深怕这个孩子遭受哪怕一丝一毫的委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地主这一身份已不再是能起到庇护作用的东西,反倒成了充满危险意味的标识。

为避免孩子受到牵连,王学文刻意行事低调,从不在人前说起这个孩子的身世。然而,命运并未对吴仲廉手下留情。在革命征程里她不幸被捕,目睹了丈夫曾日三壮烈牺牲。数年之后,她成功获救,随后再度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在数不清的夜晚里,她总会忆起那个在雪夜与她分别的孩子。

新中国建立之后,吴仲廉终于获得契机去寻觅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时候,王继曾已然13岁。他于王家成长,早已将养父母视作自己的生身父母。当吴仲廉领着部队人员抵达王家,表明自身身份之际,王继曾的首要反应是——抵触。“你又不是我妈,我就只有那两位是我的爸妈。”

吴仲廉的眼眶泛起了红晕,她心里明白,孩子不认得她,这并非孩子的过错。是自己这些年来的缺失陪伴,致使孩子将他人视作最为亲近的人。王学文夫妇并未加以阻拦,他们安稳落座后,语重心长地向王继曾讲述,他的亲生父母并非将他遗弃,实是因国家大事所迫,才不得已做出这般艰难抉择 。王继曾沉默良久,最终开了口:“那……我可以喊你妈妈吗?”吴仲廉颔首,泪水忍不住涌出眼眶。

然而当她表示要带儿子返回浙江时,王继曾竟双膝跪地,对着王学文夫妇连磕了三个响头。“你们会一直都是我的父母。”最终,他还是跟随吴仲廉离开了,然而自那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忘却王家对他的养育之恩。闲暇之时便回来看看,带上礼品奉养自己的养父母,每逢佳节一定写信致以问候。吴仲廉始终没有忘却王家,她竭尽自身的能力,助力王学文一家摆脱困境。

这是一次别样的“亲子团聚相认”。在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不少革命者无奈之下只能做出舍弃小家庭的抉择。在这场革命的汹涌浪潮里,存在着如王学文夫妇这般的平凡人。他们虽未奋战于前线,却以别样的途径,捍卫了革命的火种。有人讲,历史的恢宏之处,隐匿于这些被时光掩埋的细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