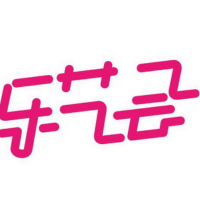东一美术馆观画记
郑朝晖
此次东一美术馆从乌菲齐美术馆引进的《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展,主打的是波提切利的作品。其中《三博士朝圣》(1474—1475)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与半人马》(1480—1485)应该说是此次展览的聚焦之作。当然,展览最后展陈的《春》(1482)和《维纳斯的诞生》(1487)因为是乌菲齐美术馆授权复制版本,也同样吸引了观展者的注意。

很多人关注波提切利,都是从《维纳斯的诞生》开始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被那样美好的画面所感动。丰子恺说:“从海中的贝壳上生出来的女神,现出着这世间最美的全裸体,而临风立着。空中两个天使飞来,右方一女人献上衣裳。全画的优美与艳丽,实可谓达人间感情的极点了。”丰子恺画过很多有趣的画,也写过很多美的文字,但这一段话却并不得要领。一则,空中飞的并非是天使,而是西风之神泽菲罗斯(Zephyrus)和妻子春神克罗丽丝(Chloris),那“右方一女人”也并非凡人,而是花神芙罗拉(Flora),那件袍子自非凡物,而是缀满了星辰的锦衣。至于维纳斯之美,也不是“这世间最美的全裸体”可以描述的,因为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不仅美在体态,也美在五官和神情。低垂的眼眸和慵懒又寂寞的眼神,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据说,波提切利很多画作都是以当时佛罗伦萨的公众“女神”西莫内塔·维斯普奇(Simonetta Vespucci,1453—1476)为原型的,在《维纳斯的诞生》里,她是维纳斯,在《春》里她是花神芙罗拉,在圣母像中她又是圣母玛利亚,总之,波提切利将一切美好都归于这位他心中的女神。而在所有的绘画中,他心中的女神又总是忧郁而又寂寞的。在波提切利的笔下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对于西莫内塔的那种强烈的怜爱之情。西莫内塔是1476年去世的,4年后,波提切利按照她的容貌绘制了《女神帕拉斯·雅典娜与半人马》,6年之后又按照她的容貌绘制了《春》,9年之后,波提切利又让西莫内塔的容颜永留在《维纳斯的诞生》这幅巨作上。或许,在任何西莫内塔出现的地方,她都不会过于关注这位容貌平常,身材圆胖的画家,但这并不妨碍波提切利用炙热的眼光将她的盛世美颜牢牢的记在心间,这很像但丁与贝特丽丝之间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那是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爱情。

很多人都觉得波提切利对女性容颜的刻画是深受他的老师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年)的影响。的确,在同时代的画家中,菲利波·利比和波提切利都是属于格外关注画中人物的神情的那一类。可以说,“神情”是波提切利从利比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最重要的特点。很多人观赏波提切利常常会被他柔美细腻的笔触所打动,比如在《春》中美惠三女神身上的薄纱就很能让观赏者发出阵阵赞叹,更有甚者,会赞叹波提切利在画面上撒上云母粉而让画面显出繁星闪烁的效果。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最主要的,作为文艺复兴的伟大画家,波提切利通过他的画面,展现出的最为可贵的价值在于让具体的、生动的、复杂的人情人性成为了画面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波提切利笔下美人的容颜所具有的那种忧郁与悲悯的眼神似乎较之他的老师更浓厚,更深沉。即便是那个唯美的维纳斯,从海浪中涌现,被风神、春神、花神呵护着的时候,眼睛里流露着的依然是浓浓的孤独和惆怅。

此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一幅作品就是完成于1475年的《三博士朝圣》。三角形构图带有的神圣性,对自然风光的生动描绘所体现的文艺复兴的风尚,还有他将自己的形象至于画面的右前方,这些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更吸引我的,则是画面左下角的那群人,他们显然没有被眼前出现的“神迹”所震慑,他们的身姿、神情和动作是松弛自如的,他们更像一群偶然遇到热闹事件的路人,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而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很喜欢这样自然随意的状态,它让我想起了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名言:“如果我别无所长,至少我永远保持自由、无拘无束的好奇心。”

波提切利向内探索人类内心的寂寞与孤独,并用美的笔触和色彩去赞美这种真正发自人们内心的情感,因为它们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心灵的深处;另一方面,他又向外探索,去展示人们外在的松弛自然的形态与神情,让人们懂得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人应该都是自己的主宰,任何强权和阴谋都不应也不能够剥夺人作为自己的主人的神圣权力。这只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因为做自己的主人并不意味着获得利益,也包括直面风险与承担责任,但人就是在成为其自身的过程中,才完成了自我的同一性。——文艺复兴的伟大精神内核或许就是这个吧。
为什么我会格外关注波提切利这一时期绘画中人的形象的这种“松弛感”呢?那是因为在此次展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1490年之后波提切利画风的急剧转变。绘制于1495—1500年的《圣母、圣子与施洗约翰》,让我们看到一个僵硬了无生趣的波提切利。圣母似乎是被画框压迫着,不得不90度屈身,以这样的别扭动作抱持着比例明显不协调的圣子,圣子几乎要从圣母手中滑落,右下角年幼的施洗约翰则上前用别扭的方式拥抱着圣子,圣子所有的重量似乎都压在了幼小的施洗约翰紧绷的左腿上,构图僵硬而重心摇摇欲坠,而且,无论是圣母还是圣子,他们的面部表情呆板,眼睛则都是闭上的,波提切利笔下人物眼中那种温柔慈爱而略显寂寞感伤的眼神在这里终于熄灭了。这一切简直令我无法相信这幅画出自曾经绘制出《春》和《维纳斯诞生》的那个波提切利的笔下。

根据历史记载,波提切利的改变与佛罗伦萨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有关,这个人就是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这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带领着佛罗伦萨陷入到了一场癫狂的宗教狂欢之中。他建立了“佛罗伦萨宗教共和国”,新法律反对同性恋(可以死刑)、反对通奸、反对醉酒、反对赌博。他强制关闭了所有酒馆,还建立了巡逻制度确保街上的女人穿着得体。他大量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销毁“不道德的”奢侈品。1497年,萨伏纳洛拉主导了一场“虚荣之火”(Bonfire of Vanities),熊熊大火烧毁了无数的文艺复兴艺术品,一并毁掉的还有全城的乐器、画像、雕塑、象棋等游戏用品、女人的时装、化妆品、镜子、古典书籍、诗集等等和世俗享乐有关的东西。而作为萨伏那洛拉的忠实信徒,波提切利异常虔诚地忏悔了自己过往的一切,并自己亲手将自己所绘制的12幅画作投入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以表示与过去的自己决裂。——要知道就1470—1490的二十年间正是波提切利绘画达到艺术巅峰的阶段,《三博士朝圣》、《女神帕拉斯·雅典娜与半人马》、《春》、《维纳斯的诞生》都完成于这一时期,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亲手毁掉的具体是怎样的作品,但可以肯定是,一定是与《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一样繁花似锦一样洋溢着人性的温暖的作品。虚荣之火,也让我想起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种种类似的打砸抢烧的事件,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以“正义”与“道德”的名义去掩盖背后的野蛮与愚蠢。
波提切利在1490年之后,就陷入了他的创作黑暗期,题材狭窄,画面呆板、主题突出,他抛弃了由他一手缔造的温情、丰富、生动的艺术创作风格,回归到僵硬灰暗的哥特式风格的宗教作品的绘制中。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的画作所展现的那个斑斓多姿的世界已经打开了佛罗伦萨市民的眼睛与心灵,正是这些人现在迅速地抛弃波提切利,似乎连一点悲悯的留恋都不愿留给他,而波提切利也就在这种被抛弃的潦倒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顺便说一句,那个在1497年虚荣之火中达到自己人生高光时刻的萨伏那洛拉,在第二年也就是1498年就被那些曾经追随他狂欢的佛罗伦萨市民扔进了火堆丢了性命。
我在波提切利1495年绘制的《圣母、圣子与施洗约翰》面前站立了很久,我想感受一下曾经画出那么美好的画面的波提切利绘制这幅作品时的心境。站在这幅画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真的会有某种貌似正义实则黑暗而愚蠢的力量能让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将自己否定得面目全非。但是整个世界却不会因为波提切利的倒退而倒退,在波提切利进入它的神性时代的同时,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已经站立起来,他们正沿着曾经的波提切利开创的道路一路高歌猛进,人性的光辉,正在透过云层,散发出更加辉煌的光芒。望着不断站到《春》、《维纳斯的诞生》前合影的男男女女,我想,在后世人们的心中,波提切利毕竟是和《春》、《维纳斯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而绝不可能与《圣母、圣子与施洗约翰》联系在一起。这大概可以看作人类的未来尚足以寄予希望的表征吧。
本图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