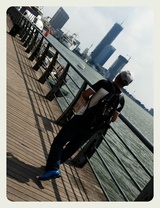当惹雍措像一块被天神遗落的蓝宝石,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金光,远处的达果雪山沉默地伫立,山顶的积雪与低垂的白云几乎融为一体。我们坐在湖畔,美美的吃一次野餐,再泡上一杯茶,耳边只有风声和偶尔掠过的鸟鸣。这样的景色美得不真实,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


但行程紧迫,我们不得不启动车子。就在车轮碾过砂石路时,前车的对讲机突然响起:“文布村有苯教求雨仪式,再晚就赶不上了!”一句话,让所有人的疲惫瞬间消散——苯教,这个西藏最古老的宗教,如今已鲜少公开举行大型仪式,更何况是求雨这样与自然直接对话的秘典,这是一场难得的古老仪式的现代回响。


文布村坐落在当穹措湖畔,村子不大,石砌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当我们赶到时,寺庙前的空地上已聚集了上百人。村民们身着厚重的氆氇袍,女性头戴镶满绿松石和珊瑚的“巴珠”,男性腰间别着藏刀,许多人背上绑着鼓鼓的布袋——后来才知,里面装着青稞、糌粑、酥油,甚至活羊的头颅,全是献给天神的贡品。寺庙外墙被烟熏得漆黑,门楣上挂着一串风干的鹰骨,这与常见的藏传佛教寺庙截然不同。苯教寺庙多供奉“赞神”(山神)和“鲁神”(水神),而佛教寺庙则以佛像和唐卡为主。一位懂汉语的老者告诉我们:“苯教求雨,靠的是与神灵‘谈判’,不是祈求。”


寺庙内在举行着仪式,我们只能在外面等着。一会儿,一群人在巫师的带领下排队走出寺庙,他们手持铜铃与法鼓,脚步沉重如擂鼓,口中念诵着古老的咒语。据说,这些咒语能唤醒沉睡的雨神“恰那多吉”。仪式的高潮是求雨队伍上山。巫师领头,村民扛着经幡和贡品紧随其后,他们沿着陡峭的山路蜿蜒而行,身影渐渐隐入云雾中。我身边一位年轻的女子(后来我知道她是乡里的老师)喃喃道:“雨水是神的眼泪,得用眼泪去换。”


我们被拦在寺庙外,只能听着远处的鼓声与呐喊,看着山腰的经幡在风中狂舞,仿佛整座山都活了过来。仪式结束后,我们走进寺庙。寺庙内部与藏传佛教的寺庙在布局上差不多,但内部供奉还是有区别的,里面并无佛像,只有一面绘满星辰与闪电的壁画,中央供着一块黑色陨石——苯教认为这是天神坠落的“心脏”。寺庙角落堆着古老的象雄文书,内容无人能解,但那种神秘感让人心生敬畏。内部禁止拍照,所以无法展示。


离开文布村时,我们翻越海拔5000米的垭口。回望文部村,当穹措已笼罩在烟雨中,湖面与天空模糊成一片青灰色。我忽然想起那位女老师的话,或许“求雨”的本质并非迷信,而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谦卑。在现代社会,我们习惯用科技“征服”自然——人工降雨、水利工程,似乎一切皆可控。但苯教的仪式提醒我们:自然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对话的伙伴。干旱时,村民没有等待上面来救援,而是选择用最古老的方式与天沟通。这种信仰,本质是对生存智慧的传承。但那一刻,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人与自然千年契约的延续。


路上,我们争论起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别。表面看,两者寺庙都有转经筒、经幡和酥油灯,但内核截然不同。苯教保留着原始萨满教的痕迹,崇拜自然神灵,仪式充满野性力量;而藏传佛教融合了印度哲学,强调轮回与慈悲。记得一位学者曾说:“佛教教人如何面对内心,苯教教人如何面对天地。”


遗憾的是,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苯教逐渐边缘化。如今,只有偏远的象雄故地(今阿里、那曲一带)还能见到完整仪式。这让我想到:文明的进程是否总要以湮灭某种古老智慧为代价?那些随风飘散的咒语,是否也承载着未被解读的宇宙密码?



回来后,文布村苯教的求雨仪式常常会在我脑海中出现,我也常常会思索,某一刻我突然明白,其实苯教的求雨仪式无关“是否灵验”,而是一场关于信仰的集体记忆。在高原,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共生于这片土地的默契。当工业社会的暴雨预警取代了巫师的鼓声,我们是否也在失去某种与天地对话的能力?答案或许就藏在文布村的求雨里,藏在当穹措的涟漪中,也藏在每一个俯身向山湖磕下的长头里。


感谢诸位友人拨冗莅临狼窝,诚望不吝批评指导。欢迎各位留言点评、转发、分享、收藏并关注本号,您的支持实乃老狼创作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