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取焦知识分子题材、文人气息浓厚的长篇小说,自问世起便引起士林的广泛关注。以评点而言,已发现的各家评本已达十种之多,[1]或言简意赅,或论述精当,评点的话题涉及全书的主旨思想、人物刻画、情节结构、讽刺艺术等多个方面,是《儒林外史》接受、传播、研究史上的重要资料。

《文献》杂志所刊《新见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考论》
笔者新近发现抄本《儒林外史》新评本一种,题名《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作者为晚清文人童叶庚,故以下简称此评本为童评。
童评本从形式上看,与其他评本有个显著的不同,即完全由评语构成,没有一句《儒林外史》原文,在相应的位置仅注明为“某回”“某页”。其依据的版本为齐省堂增订本(以下简称齐本),[2]且齐本的每页都有对应的评点文字,次序井然,其标记的“某页”即针对齐本而言。故而虽然完全以评语行世,也不影响阅读。
童评尽管仅评全书前二十三回半的文字,但由于每回每页都有评,加之特殊的评点方式,其评点字数达六万五千余字,在现存已知《儒林外史》各评本中高居首位。据童评凡例,其完成于“光绪癸巳(1893)秋七月”[3],在清代诸评本中也是成书相对最晚。[4]
这样一部内容丰富、见解别致、写法特别且成书较晚的一部评点本,在《儒林外史》评点史、甚至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童评的存在,扩大了中国小说评点的表现内容与书写方式,在“小说评点进入尾声”的时代,[5]最终更新并确定了小说评点的版图。
一、《儒林外史》评点源流上的童叶庚评本
童叶庚评点《儒林外史》的底本是齐省堂增订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齐本的影响。他在凡例中宣称完全赞同齐本的意见,因此其本在对《儒林外史》朝廷评点也尽量避开齐本的已评内容,所谓“惺园批注,先得我心。凡经评出者,不复赘言。”他所不满的只是齐本的评点过于简略,“惺园批注,亦尽善尽美,惜稍略耳”,对于齐本未能评点全书颇感遗憾。

《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例言
言下之意,童叶庚要全面评点《儒林外史》全书,力求不遗漏任何的精彩情节,至于是不是继承齐本的评点风格则又另当别论。事实上,从目前发现的前二十三回半来看,童氏的评点密度、评语的繁复程度都要远超齐本,当然也超过其他诸家的评本。
我们全面考察童评后,发现童评并非受齐本影响最深,童评与卧闲草堂评本(以下简称卧本)、张文虎的天目山樵评本(以下简称张本)有着更深的渊源与承继关系。[6]
先看童评与齐本的关系。
首先,童评并不如凡例所说,完全避免了与齐本重复议论。
就现在童评的评点范围来看,对《儒林外史》某一内容的评与不评似乎并不受齐本的限制。在不少齐本有评点的地方,童叶庚还继续发表自已的意见,哪怕二者观点完全相同。

童叶庚画像
如胡三公子在西湖诗会上提到严贡生的立嗣官司结果,齐本评曰“带结前文”[7],童评则稍做引伸为“归结赵氏立嗣之事,处分得还算公道”。两者的观点只有详略之分,并无本质区别。齐本与童评的意见相重之处有二十余处之多,这里就不一一缕述。
更重要的是,对于同一处文字的评点,童评往往从不同角度阐发,发现文本的另一重意味,甚且有与齐本完全相反的评论。
如万雪斋被牛玉圃揭出阴私后“气的两手冰冷,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齐本从牛玉圃的角度评道“老牛尚不觉得,何其笨也。”[8]童评完全在调侃万雪斋的窘态“满脸绯红,两手冰冷,一句话说不出来,一口气几乎塞煞。”
还有原书中写到潘三周到地为匡超人谋划房屋、娶妻等事,齐本从文法的角度评为“反照后文”[9]。童评则就事论事,大谈潘三的慷慨仗义,侧重于人物形象。可见,童评对齐本的看法并不如凡例中所言的“先得我心”“尽善尽美”。
就是在一些具体人物的品评上,两者也常常是大异其趣,对二娄的不同评价就很能说明问题。齐本将他们的好发异论、喜寻异人的行为,统统斥为“纨绔口气”[10]。童评则不然,对二人充满着溢美与赞赏之辞,“娄琫、娄瓒是蘧太守之内侄,乃娄中堂之公子。潘杨戚谊,阀阅门楣,写出高贵声华,洗尽寒酸气象。”
这足以说明童叶庚尽管以齐省堂本为底本进行批评,在凡例中也对齐本的评点评价甚高,但其并不是齐本的附庸,其观点更不是对齐本的证明、阐释或扩充,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崭新的批评文本,有着不亚于齐本的批评史意义。

齐省堂刊本《增订儒林外史》
对于张文虎评本,童评虽没有明确宣称曾受其影响,但两者有多处评语相近,不能简单地解释作巧合或所见略同。
有的是对文法的提示,如洪憨仙死后,其女婿向马二先生解释为何憨仙能知马二姓名,张本评曰“扶乩即是憨仙,马二先生在书店里自已说出站封面,皆于此补清”[11],童评则说“又把片石居请仙,书店里歇脚,前文一齐归结。”
有的涉及到对前后相似情节的比照,如乐清知县请匡超人相见,张本与童评都联想到了时知县见王冕。张本的评语为“若是时知县,必要传他到衙门里去了”[12],童评则是“李知县发帖子拜匡超人,与时知县发帖子约王元章,居心各别。一个是贤宰爱才,一个是俗吏附势。”两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不过童氏略做引伸而已。

《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例言
对于齐本、张本都曾评点过的文本,童评的意见也倾向于张本而不是齐本,这更能说明其与张本更有渊源。如蘧太守在教训二娄时透露出自已的本名,齐本的评点为“老成典型,声口酷肖”[13],侧重于人物品评;张本则说“始见蘧太守名”[14],童评也同样评道“蘧祐名字,在太守自己口中提出。”
童评与张本对于《儒林外史》的多处地方同时都有评点,且意见大多相见。很多时候,童评可以视为对张本评点意见的扩展。张文虎的评点多简短零碎,童叶庚的评点相较而言更为繁复,这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前者的说明。
比如周进任学政时立下决心“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张本评作“有良心”[15],童叶庚则解释周进何以“有良心”,道“周进不曾进过学,看得秀才甚是着重。如今身为学道,自己当权,还想着做小友时的吃苦处。”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严监生妾赵氏在妻子王氏的床前哭诉之语,张评道“其言甚巧。”童叶庚则解释其言如何之巧。由此,或者可以推断童叶庚有可能读过张文虎的评点本并深受其影响。
其实,联系到童叶庚的生平与晚清上海的文化环境,童评与张评有如此深的渊源就不足为奇。李汉秋在做《儒林外史》的汇评工作时,注意到《儒林外史》的大多数评本都出自上海附近,都以张文虎评点为中心,因而断定“清末上海周边有一个‘儒林外史沙龙’”“这个沙龙中的同道都以天目山樵为嚆矢。”[16]

《张文虎日记》
张文虎的评点本在上海一带喜爱《儒林外史》的文人中间广为流传,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童叶庚是上海崇明人,又长期在上海周边做官与生活,所以接受张评本的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
《儒林外史》评点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最早的卧评本奠定了后来所有评点的理论基础。“所有评本均以卧闲草堂本为唯一底本,卧评是《儒林外史》评点的共同之源。而在以后的发展中,评点者以卧评为基础,或增评,或生发。”[17]
童评的完成距卧评已有百年的时间,[18]但无论是主题思想的勾勒而是文章法度的剖析,都明显受到卧评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丝毫不弱于齐本、张本与黄本等与卧评的关联。以下择其大端而作简要介绍。
卧评本的闲斋老人序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19]的观点,以各人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将全书人分为四种类型,并在第一回的回评中指出“功名富贵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其后的各家评本都没有绕过这一结论。“此种说法,抓住了全书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概括性。”[20]

清卧闲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比起其他评本,童评更是有意识地要在评点中践行展开此种说法。童叶庚在第一回的评点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儒林外史》一书,着眼在功名富贵四字,开篇先写一不贪功名、不慕富贵之王元章,以为儒林之规矩绳墨。有守规矩绳墨者,为儒林之正士;有背规矩绳墨者,为儒林之败类;有未尽合乎规矩绳墨而不远离乎规矩绳墨者,为名流、为豪侠;有并不道夫规矩绳墨而仍不失为规矩绳墨者,为畸人,为高僧。此儒林中之大较也。”
这明显就是对闲斋老人序中关于士人对功名富贵态度四种划分的摹写。所不同者,只是童评将对功名富贵的四种态度转化为具体的四种人物形象类型。其对人物形象类型的界定完全以王冕为“规矩绳墨”,这也与作者的标准相暗合。
再就创作方法而论,童评的此论文字虽然不多,但也能明显看出源自卧评本的辙迹。如卧评注意《儒林外史》中波澜起伏的情节,发现其间曲折的韵致,强调“文字最忌直率”[21]。在文贵曲而不贵直这一方面,童评本多有致意。
如牛浦郎乘船不顺,童叶庚如是推测作者的文心:“走出店门,就看见江沿上一乘轿子来。三担行李,正好上船,亦未始不可,然而嫌其直矣。文章贵曲恶直,故先写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方好去搭。此用笔之曲也。有此一曲,就添出几许情味。”其他评本包括卧本都未注意及此。
在分析作者用笔方面,童评本的不少文字是对卧本的直接承袭。如《儒林外史》对严贡生行为形象的刻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认为“作者不是由概念出发,而是按照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势,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地描绘人物形象,给人以可信的感觉。”[22]

《增补儒林外史眉评》第一回
卧评即认为严贡生在严监生死后并没有立刻生吞并家产之心,当看到赵氏所赠“两套衣服、二百两银子”时,“已志得意满,又何求乎?”原书的描写“有次第,有先后”[23]。
而童评在涉及这部分的评点时,就秉承着卧本的意图,将其间的次第与先后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对严贡生刚回家时的反应,童评道“两套衣服、二百银子。此時严大老官,欲壑已满。”这一段话几乎是卧评的翻版。
童评还详细地交待了严贡生如此心理的原因“有兒子,焦急的?此是大老官心中原无他意。”使得严贡生的性格发展更为真实可信。在人物描写须合乎情理方面,童评无疑是继承并完善了卧评的观点。
综上所言,童评的出现在《儒林外史》评点史上并不算突兀。它的生成是深受此前的诸种《儒林外史》评点本共同影响的结果,并不如凡例中所说其只受齐本的熏染。

《童叶庚:清代益智大玩家》
事实上,童评受卧本与张本评点的影响更大。具体说来,在总体性的思想与文法的论断上,童评与卧本一脉相承;而在对具体人事的评点上,又与张本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
客观地看,童评在对《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的揭示与创作方法的提炼方面,相比起前代评家,都没有显著的突破之处。它的价值在于评点角度的选取与评点语言的呈现上均有独到之处,不仅在《儒林外史》评点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都有其特殊的意义。
二、“论事”转向:小说评点角度的更新
小说评点萌兴于明万历年间,其最初的形态“在形式上一般不脱训诂章句和音诠释义,在内容上大都为历史事实的疏证”,[24]可谓极其粗陋,并未触及小说的文学本质。李贽等著名文人参与到小说评点中后,提升了小说批评的水准。
此后小说评点基本上沿着品评主旨大义与勾勒艺术章法的两个面向展开,正如金圣叹所说“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25]。所谓的“道”多指道德批评、伦理评价。[26]偏向所谓“文”当然就是指文法,具体而言,即是“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27]。
“文”与“道”构成小说评点的两翼。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王希廉、冯镇峦、但明伦等著名评点家的评语中皆是“文”“道”并提。

冯镇峦、王士禛等合评《聊斋志异》
如冯镇峦评价《聊斋志异》“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28]而其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就围绕着“文笔”与“议论”展开。再如王希廉等人评点《红楼梦》也能兼顾这两个方面,“在价值评价上展开了道德批评的视界,在艺术形式上则展开了八股文法视界。”[29]
无论是评“文”还是论“道”,传统的小说评点都展现出对故事情节——小说中最基础元素——的轻视,甚至认为读小说只注重故事情节是不关于读小说的表现。
金圣叹等人在评点中反复表达这样的看法,“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30]说得更明白一点,他的小说评点主旨是“略其行迹,伸其神理。”[31]
正因如此,有学者评价其“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的提法,实际上是也有侧重的。“言下之意,他是舍道论文。”[32]

《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有学者甚至还认为金圣叹是在以点评论说文的方式在评点小说,“金圣叹对‘事’也相当忽略与淡化,与之相对应,他常常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33]
由于金圣叹的巨大影响,小说评点中轻视故事情节的观念具有巨大的受众,甚至成为有清一代小说批评的主流风格。如冯镇峦也认为“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34]“《聊斋》每篇只是有意作文,非以其事也。”[35]类似的观点在张竹坡、王希廉、张新之、但明伦等人的评点中也是俯拾即是。
小说评点重“文”与“道”而不重“事”,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文学评点的兴起与吕祖谦《古文关键》的盛行颇有渊源,吕祖谦在其中的“论作文法”中事实上奠定了后世评点的基调,“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36]故而评点要么阐扬“道”之“有用”,要么发挥“为文之妙”。
童叶庚之前的《儒林外史》诸种评点本也是沿着“文”与“道”兼重的路数展开,在思想上指出其“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在创作方法上力图发掘其“描写世事,实情实理”[37]的一面,揭示其“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38]的表现手法,同时也存在发掘人物原型的朴学倾向。[39]
像“直书其事,不加论断”[40]的人物刻画,惯用反笔、侧笔的描写方式,人物声口的宛肖逼真,等等,都为评点者们所津津乐道。换言之,评点者们关注的是小说家的出色的文笔与深刻的思想,而对作为载体的故事情节同样重视不够。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本目录
童叶庚评《儒林外史》时已届暮年,[41]历经一生的荣辱沉浮,此时闲居无事,他谈道“今岁里居多暇,重展是书而读之,心有所得,随手札记。”既没有借小说传授子弟以文法的现实需求,也更乏藉评点小说来骂世济时之心,故而其评点中谈“文”论“道”的部分为数不多,更多的时对书中人物事迹的品赏。
这样的评点侧重可以反用金圣叹的话,概括为“详其行迹,略其神理。”同时,目前发现的童评本单独以评语的方式流传,并不带有任何小说原文,评点更不是栖身于原文的角落里,这使得评者有足够多的空间与篇幅来讨论小说情节。[42]
这也決定童评与卧本、齐本、黄本、张本等评本对于《儒林外史》同一处情节的评点角度有着明显的区分。由于童评对故事“行迹”的格外留意,其批评风格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善于体贴人情,洞察幽微,能够详密而具体地指出人物言语的言外之意与行为的内在根由。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这样的例子在童评中数不胜数。如第二回中薛家集诸人在观音庵里商议闹龙灯之事,对于荀老爹、申祥甫、众乡民的发言次序,童评有一段评论,极为精彩。“荀老爹先开口者,明知自家必要多出银子,故不得不先开口也;众人不开口者,明知各家可以少出银子,不敢先问也;申祥甫劈口阻住者,要等亲家来分派,不能独出主见也。”切入各人的心曲,言人所不能言。
再如张静斋、范进与严贡生问及汤知县时,二人的话题完全不同。对此,童叶庚有这样一番解读。“张静斋道:‘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是要想寻他短处做讹头。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不过借此夸张自己才情。两人心思不同,而问答处又身份恰合。”这些都是人情练达之言,但终究既不“论文”,也不“论道”。
如果要从中发现笔法之妙或者微言大义,多半会一无所获。也正是因为童叶庚在评点中不执着于文本中发现文法或阐扬道理,故而能于人情中下工夫,在《儒林外史》的评点中能开一新天地。
其二,运用了大量的情节对比以呈现小说故事的趣味。用童评“凡例”中的话来说,就是“此书前后有用笔相犯之处,必为逐句对勘,逐层交锁”。
这构成童评本的一大特色。本来关注“相犯”之笔是中国小说评点的重要面向,“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性格,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自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以来的小说评点派都注意剖析这个方法。”[43]

童叶庚《睫巢镜影》
此前的评点家列举小说中的“相犯”之处,指出小说家能“犯而不犯”,能做到同中见异,强调小说的文法之妙,而不侧重于小说情节的前后关联。[44]评点家不厌其烦列举此类情形,意在说明“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恶人的共相中写出同中有异的微妙变化”[45]。
《儒林外史》的其他评点也常涉及对比,但意在评价人物高下。卧评比较杜慎卿、杜少卿两个“豪华公子”,指出“一个慷爽侠气,一个痴呆皮”[46];张文虎多次比较匡超人与牛浦郎,意在说明牛浦郎的“庸恶陋劣”更在匡超人之上。童评当然也在对比中呈现人物的优劣,如其评价“杨执中固难比元章,鲁编修尚不及危素”,又说“周学道又在鲁编修之下”,都是将不同故事单元人物间的比较。
而纵观童评,其运用最普遍的是情节间的比较。如第八回评价王惠向荀玫示好时说,“王惠劝荀玫移寓,与张静斋请范进搬家,似同实异。”童评常常抓住人物的相似言行,从而展开议论。

《儒林外史》群玉斋活字板
童叶庚注重于此,多半是为了趣味起见。如权勿用的帽子被卖柴人无意挑走,童评联想到另外的一个情节:“乡里人搬盘,踢起钉鞋,打烂大媒人的热点心。乡里人卖柴,掮着扁担,挑掉走路人的高孝帽。两个乡里人,堪称一对。”
又将权勿用与杨执中联系在一起,“盐店里盘查帐目,杨执中对着东家,指手画脚的不服。街道上撞翻轿子,权勿用向着厅官,指手画脚的乱吵。两个冒失鬼,亦是一对。”
这里面并没有深意可寻绎,不存在道德评价问题,也没有涉及到对文笔评价。更多的是在品味由故事情节类似而生出的趣味。童评中的仅就情节而谈情节的比较,这是此前的小说评点里都未曾出现过。
其三,评语文字中有大量的对于小说原文的重写性文字,客观上构成了对小说故事的重构与再创造。
童叶庚所改写的情节以及改写的方式,看不出对于原文“文”或“道”的考量,应更多完全是出于对小说故事的激赏。《儒林外史》前半部中的经典性情节如范进中举、张静斋打秋风、严监生之死、严贡生讹诈船钱、蘧公孙婚礼、二娄访杨执中、马二先生游西湖、匡超人孝亲、牛浦郎偷诗、牛夫人寻夫等,童叶庚都在评点中以生动的语言重新做了一翻讲述。
由是,小说评点在事实上对小说正文构成了重写的关系。“所谓重写, 指的是在各种动机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种文体, 以复述、变更原文本的题材、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意境、语辞等因素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文学创作。”[47]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
于评点中不厌其烦地重写复述小说的情节,在此前的小说评点中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以习惯性思维来说,这样不惮笔墨地复述正文已说明、读者已熟悉的故事,是不经济、不明智、不讨巧的行为。
如果我们联系到童叶庚的批评背景,就可明白其如此做的用心,是为了纯粹享受小说故事带来的趣味。在对小说原文不断的改写、重写中获得一种情感的愉悦,其间不乏戏谑的意味,甚且是在文字的腾挪变化间尽情游戏。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评点终究没能给小说意义以阐释,但其作为一种新的接受、传播方式,恰恰证明《儒林外史》的魅力,也从实践的角度证明其作为经典的属性。[48]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下面就以童叶庚对蘧公孙婚礼上一场“突发事件”的反复书写,以见其对童评的重写意趣:
乡下小使见了戏,那得不看,只管眼里看着小旦,忘却手里捧着粉汤,还记得盘里的汤脚要掀掉,不顾得盘里的汤碗未端完,听得叮当一声响,才知打碎两个碗,慌得弯下腰去抓,忽见跑过狗来抢,恨得跷起脚去踢,不料趿的鞋会飞。要写小使踢脱一只钉鞋,先从小使趿着鞋说起。逐层写来,文心有剥茧抽丝之妙。
脚趿钉鞋,手捧粉汤。身立丹墀,眼看戏场。丫头小旦,做势装腔。看得出神入化,未免失措仓皇。只道碗已端完,倒却盘里残汤。两碗落地,一声叮当。不可收拾,着实惊慌。急忙弯腰去抓,可怜有粉无汤。末了两条大狗,抢着吃得精光。不觉怒从心起,顿时手乱脚忙。气力用到十分,钉鞋踢脱半双。蠢牛已吓昏于墙下,飞凫竟翱翔乎高堂。
陈和甫举起箸来,正待吃点心也。点心未到嘴,而盘子已打得稀烂也。何以打烂?是一个乌黑的东西滚来也。钉鞋从何而来?从丹墀里飞进来也。丹墀里何得有这件东西?是搬盘小使脚下之物也。小使因踢狗而踢脱钉鞋也,踢起丈把高,使尽平生气力也。用力太猛,的溜溜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滚到右边席口也。乒乓一声,把大媒吓了一惊也。慌得衣袖招翻汤碗。可惜热烘烘三样点心,一概吃不成也。
由于《儒林外史》秉持其“慼而能谐,婉而多讽”[49]的创作风格,虽有意展现其间的欢谑,但下笔极为克制,这一段的描写前后不足四百字,且采取顺叙之法,不紧不慢,娓娓道来。

《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
其他评家在此处的评语也是寥寥数语,如齐本评作“虽欲不笑,不可得已”[50],张本则为“好看”[51],黄小田评作“得不笑杀”[52]。惟童叶庚的评点篇幅驾小说原文而上之,其间尽情施展,将吴敬梓极力遮掩的欢谑之情抬至顶峰。
童叶庚在这里将原文以三种方式各重写一遍。第一种按照事情发展的次序从容写来,不过其间使用了大量的如“那得”“只管”“还记得”“不顾”“听得”“才知”“慌得”“忽见”“恨得”“不料”等提示性词语,以小使的视角,将其间的紧张感烘托得淋漓尽致。
第二种也是正叙,但每句句末押韵,且是声调绵长的韵脚,写尽文中的戏谑感。
第三种则以倒叙的手法,层层倒推,将慌乱的结局写出欢乐的味道。由此可见,童叶庚评点中对故事情节的醉心,这其实也是赋予小说片断以经典性的一种途径。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8期转载《新见〈增评儒林外史眉评〉考论》
童叶庚评点《儒林外史》一改重“文”与“道”的惯例而以论小说故事情节为主,表面上似乎没有太大的文学批评价值或道德意义,但客观上对于抬升小说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批评家重视小说价值的一大惯技即是论证小说有《左传》《史记》等经史正典的文章法度或劝戒作用,闲斋老人评《儒林外史》时也多次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
但这并不能真正说服人心,申涵光的反驳就很有力道:“每怪世人极赞《金瓶梅》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53]
像童评这样悬置小说与经史的比较,纯粹欣赏小说情节之趣,写人绘事之生动,而不做过多的价值提升,可能反倒更有利于客观认识小说的文体性质。
三、小说评点主体性的确立与评点语言风格的更新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谈到评聊斋的五种角度:“往予评《聊斋》,有五大例:一论文,二论事,三考据,四旁证,五游戏。”[54]这也是对古代小说评点基本面向的全面概括。特别是“游戏”,在小说评点中展现得相对来说更为充分。“对小说作评点的人,有时也故意或喜欢运用一些通俗的语言和词汇,插科打浑,使文字显得诙谐幽默,亦庄亦谐,较之传统的诗、文评点,要风趣生动许多。”[55]
自李贽、金圣叹等人起,评点家们都惯于发现小说中的趣笔,类似“趣甚”“妙甚”“快绝”“一笑”之类的文字在评语中屡见不鲜。

《李贽全集注》
但总而言之,明清两代的小说批评,虽表现出对趣味的激赏,真正的谐趣之语在全部评语中却占极少数。其原因有二。
其一,评点家们多乐于发现其认为有趣的文字,而缺乏将原文中的趣味在评语中以再现出来的能力或动力,往往以“趣”“妙”“谐”“笑”等抽象化的词语概括了事。至于小说原文为何有趣,或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或是觉得过于浅显而懒于交待。因此便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小说文本与简单概括的小说评语的严重对峙与反差。
其二,正统的文人思维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小说批评谐谑化风格的生成与发展。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可分为书商型、文人型、综合型三类,[56]书商型评点致力于推销图书,综合型评点则以导读性为其主要特色,自然与谐趣之风相去甚远。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而文人型的评点侧重追求个人精神的寄托与慰藉。传统的儒家教育使得文士在相当程度上排斥过于谐谑化的语言风格,即便是那个通脱无羁的金圣叹也不例外。他在评点《水浒传》说:“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者也。何也?”[57]
其对所谓“插科打诨”的厌弃也就可见一斑,深受金圣叹影响的清代小说评点在追求谐谑这方面则更等而下之,谐谑色彩日趋淡薄。
因此,冯镇峦所举论小说之五例,在小说评点中的分量是不平衡的,就其大较而言,“论文”之语最繁,而“游戏”之风最弱。即便是面对有趣的小说情节,评者承认其有趣,也不过评作寥寥数语。评点文字的趣味性与对应的小说原文不相匹配。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小说评点长期以来被当作对小说原文的附庸性文字,评点的使命是要发现原文中有意义的部分。一旦达到这一目标,便可得鱼忘筌,由此小说评点的语言趋向于简洁甚至粗陋便是定局。
就评点本身而言,童评的出现堪称一大变革,调动多种修辞形式,尽力腾挪文字之美,客观上使小说批评成了一场狂欢性的语言实验。
整部《整补儒林外史眉评》对评点语言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视前所未有,以精心建构的语言评论小说人物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漫不经心地记录着阅读的心得体会。

《文镜秘府论校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童叶庚对《儒林外史》的评点本身即是一次文学创作,这也证明了当小说评语获得主体性地位时,将会释放出怎样的活力与机趣。在小说评语整体缺乏幽默色彩与狂欢精神的背景下,童评欢腾谐谑的语言风格显得更为矫矫不群,也与《儒林外史》幽默的语言风格相得益彰,把握住小说的精髓。
从表层的语言层次来看,对偶句式的广泛使用是童叶庚评点《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征。对偶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修辞手段,《文镜秘府论》甚至认为未能运用对偶的篇章都不能称之为“文”:“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58]因此,对偶的广泛、持续使用可看作童评的评点文字的主体性、文学性的象征。
一般来说,包括《儒林外史》评点在内的古代小说评点,“在形态上比较简净”,“除卧评纯为回末总评外,一般以眉批、夹批居多,就是总评也言简意赅、短小精致。”[59]
纯粹从经济性的角度上来说,评点语言应是排斥对偶修辞的。童评反其道而为之,不仅以此来揭明小说的文法与思想,更是以评为戏,展露其本人文采与巧思。

《文学研究》所刊朱泽宝《“论事”转向与语言狂欢:论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的小说评点史价值》
从数量上来看,童评中有对偶成分的评语占据着绝大多数。或是概括故事场景,如评论范进中举后命运转变为“新孝廉气象巍焕,众绅衿奔走逢迎”;或重述人物对话,如将严监生临终叮嘱儿子读书的心思概托为“读了书,已得个岁贡生,便尔扬眉吐气。有了钱,捐得个监生,只好吞声忍气。自家一生受了大房里的气,无处可以出气;惟有盼望儿子将来进个学,好替他争气。”
甚至在揭示文章的情节安排时,也使用对偶句法,如评第四回道:“滕和尚做揽头之事毕,慧僧官养婆娘之事起”。
就对偶的形式来看,整饬严密的对偶居多,有的甚至采用了典范的四六句式,如点评范进与张乡绅在高要县落荒而逃时道“两条光棍,系出北城;四只草鞋,奔向南海。秋风白打,谁怜范叔之寒;春月黄昏,空吃张公之酒。”
同时也有在同一则评语中的局部对偶,童叶庚描画严监生去世前的场景时说“赵新娘扶正,五个亲侄子一个不到。严监生病重,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医弄药。无他,不过贪图些别敬耳。没想头,一个不到;有想头,五个齐来。此等亲侄子,何异蓦路人。”
除了中间的“无他,不过贪图些别敬耳”皆是对句。有的则是在散句中缀以对偶,如形容匡超人前后的神气差异时说“匡超人到京师走了一趟,依傍了阔老师,攀附了阔亲眷,又仗着自家考取了教习,在这里取结,脚跟立得牢了,胆子放得大了,就敢大言欺人了。不是逼妻下乡,溜进京时的形状了。”总而言之,对偶成了童叶庚评点语言最明显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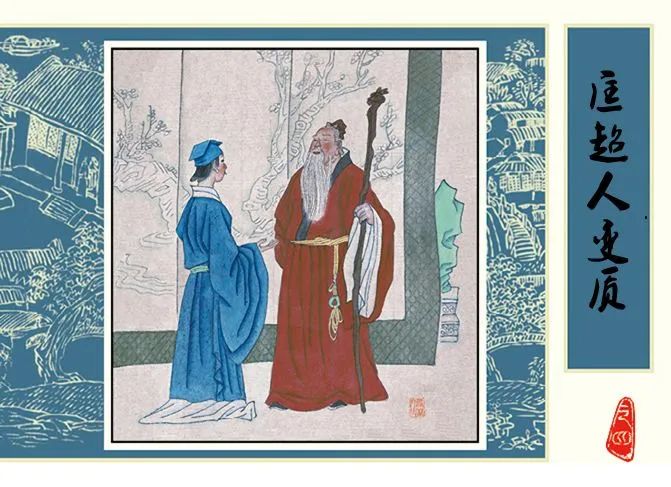
连环画《匡超人变质》
童叶庚在评点追求对偶修辞的广泛使用,有其以评逞才、以评戏谑的意图,而客观原因是《儒林外史》特殊的文本结构与情节安排,前后故事单元中的人物与情节每每能相互映照。
关于这一点,此前的评点家已经注意到了。由此,对偶式评点在再现原文意趣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童叶庚在运用对偶式评点时就于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将作者的文心抉发开来。
如点评王惠在宁藩败亡后逃走的情景时说“荀员外青衣小帽,昏夜乞怜;王观察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荀玫茫茫然似丧家之犬,王惠急急乎是漏网之鱼。”贴合文本而妙趣横生,以见这曾经的一对好友不过是一丘之貉。这是两人前后对比。
童评中还有以二人情形映照一人,以形成对偶句的。如将鲁小姐这个痴迷举业的闺秀与范进、周进相照,说“小姐之愁眉泪眼,与周进之撞头大哭相同;小姐之长吁短叹,与范学道之拍手大笑相反。”可谓相比得人,对偶贴切。
还有在对偶句中以多人的言行而类比一人者,如形容牛玉圃出场时说:“四个长随,依稀洪憨仙排场;一番大话,仿佛严贡生口角。”对偶句式具有和谐、均衡、整齐之美,也与传统的民族心理相契,广泛地运用于各种文体之中,“宋以后对偶不仅在词曲中花样翻新,而且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戏剧、小说、散文、新体赋、通俗讲唱文学当中。”[60]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译本
童叶庚将对偶引入小说评点语言中,不啻为一次有开拓性的语言实验,既扩大了对偶的运用范围,也更新了小说评点的言语面貌,一改言简意赅为繁辞俪语,对于重新认识小说评点的特性有着突出的意义。
过度使用对偶句式,容易导致板滞的毛病。对偶只是童叶庚的评点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文本面貌,其最终要呈现的是欢谑的语言意味、谐趣的审美风格。
黑格尔曾谈到过谐趣是如何产生的,“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任何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对比,如果显出矛盾或不对称,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我否定,或是使对立在实现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的。”[61]
简而言之,即能指与所指、言辞与意旨、内容与形式之间出现反差的时候,就往往蕴藏着谐趣。童叶庚对此深有会心,为表现谐趣之味,也为避免蹈陷板滞之弊端,童评在应用对偶句式的同时,调动反语、押韵、双关、戏拟、臆改、想象、荒诞等艺术手法与修辞手段,使得评点语言如行云流水,机趣横生,呈现出一副欢腾的语言狂欢之气象。
运用反讽,似庄实谑。反讽从本质上来看即为“表里不一”[62],是指使用与本意相反的话语来表达本意,呈现出言此意彼的反差意趣。
童叶庚深谙此道,时常在故作端正冷静的话语中暗藏讥讽,似庄重而实戏谑。如其在王惠接任南昌太守时评道:“两浙名流,遂初行赋;南昌太守,政令维新。”这里套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旧语,联系到王惠在南昌的政绩,其中的嘲弄之意也就一目了然。

邮票《马二先生游西湖》
这里还是引用了经典,一般读者的读下来难免有隔,童评中还有不少言辞通俗的反讽语。如评马二先生有一段记道:“马二先生看过《通鉴》,知道南渡典故,比范学道的学问,深得多了。”知道宋室南渡的典故对于马二先生、范进等人来说已是不易之事,那么举业的危害以及马、范的浅薄也就不言而喻了。
戏拟经典,寄寓嘲讽。戏拟“在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的模仿”[63],在模仿庄重的前代经典的同时宣泄着对世事人物的不满。
吴敬梓即是惯用戏仿手法,《儒林外史》中大量情节的形成与戏仿《三国演义》《世说新语》等前代经典有着莫大的关系。[64]童叶庚在评点中也顺势将戏拟发挥下去。如其在评马二先生在西湖问功名财富之事时说“马二先生初意要问功名,听见洪憨仙说发财,就趁势接到发财上去。‘贵,我所欲也;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舎贵而取富者也。’”

明嘉靖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这里戏仿了《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是马二先生必读之书,这里谈的是圣贤高贵的人格选择,经过童叶庚这一改造,俨然成为琐琐小儒卑污人格的写照,其用笔之老辣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讽刺严贡生的大言不惭,评道:“天下无难事,只怕用心人;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将励志的格言化为无耻的宣言,令人捧腹。在模仿经典的背后是游戏的态度,评者“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65]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兴味。这种反讽戏拟的评点风格也正与《儒林外史》的“奇书文体”属性契合无间。[66]
如上文指出,童叶庚的评点常常是对小说文本的改写,而将散文化的原文改编成韵文化的评语是常见的策略。原本平直的叙述化作童谣式的欢谑,原本不露声色的描写也在改写中成为大张旗鼓的评论与调笑。
对于匡超人进京再娶这一段,童叶庚评作:“将养甥小姐长成才貌出众,招赘新姑爷恭喜不消费用。来的老管家说得娓娓可听,害那小书生心中怦怦欲动。”这里共四句话,如绝句般在一、二、四句的句尾押韵,童氏这里就用诗一般的句调轻松诙谐地吐露出对匡超人再婚闹剧的不满。
再如上文列举的蘧公孙与鲁小姐大婚时因小厮而引起的意外,童氏的评点文字同样是韵文,每个偶句都押韵,分别押“汤”“场”“腔”“皇”“汤”“当”“慌”“光”“忙”“双”“堂”等。从这两例可看出其使用的韵部皆为宽韵,更便于戏谑的展开。

《儒林外史》邮票首日封
置身文中,介入批评。童评中最有特色的批评方式是置身于小说情节故事之中的介入式批评,这种情境下,评点家与其说是人物言行是非得失的评判者,倒不如说是小说故事情节的实际参与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戏谑调笑,充溢着浓厚的幽默感。或言之,评点语言并不由客观的分析构成,而是转化为评者与小说人物的对话。
童叶庚在评点中或化身为书中人物的朋友,与其打趣。如其在景兰江大肆吹嘘的那一段,评道“原来兰江先生,不但与鲁编修是诗友,与杨执中、权勿用、蘧公孙、娄公子是至交,连顾中翰、范通政、荀御史这些人都是相好的。失敬!失敬!”宛若评者本人也在西湖诗会上听到景兰江的谈论一般。
小说写到严贡生等人出现在西湖上时,童氏道“严大先生久违了,东崖先生一向在大部里得意。”好似老友重逢,画面历历如新。有时像知己一般替人物盘算得失,当严贡生讹诈船钱时,评者说“以云片糕抵喜钱、酒钱,大是便宜。以人参、黄连抵喜钱、酒钱,又算吃亏。费了几片云片糕,省了若干喜酒钱,回家大可买肉心包子吃。想府上花梨椅子,早已换完矣。”

连环画《严贡生》
像极了严贡生奸滑的口吻。有时跳入书中直接拆穿人物的慌言,如其直接抓出景兰江吹牛的破绽,道“严致中与范通政同行,严致中才到,范通政自然也是才到。然则景兰江未到杭州之前,在船上拈题分韵,却是何人?莫非赵雪斋天天看病,两眼生花,白日里见鬼,白日里捣鬼?”
有时则宕开一笔,为书中人物的荒唐言行找原因,做辩护,如洪憨仙与马二先生认表亲,评者似乎担心此举过于荒唐,不能取信于人,说道:“与三百多岁的人,认作中表弟兄,好笑之极。莫非是三百年前的表亲?俗语道是一表三千里,却不道是一表三百年。”
有时甚至更是为挽救人物的“过失”而出谋划策,如对胡屠户说道“菩萨计较起来,比阎王更加利害。怎么好?何不托文曲星去说情呢?”
童叶庚在评点中多次与书中人物展开对话,如陈和甫吹嘘其能请来各路神仙时,童叶庚表现得极为不满:“忽尔纯阳祖师,忽尔周公老祖,忽尔建文皇帝,随口乱说,有何对证?”俨然在当面质问对方。周进问范进为何迟迟考不中时,童叶庚也说“问得好笑,请教阁下当年,如何总不进学?”
最能展现这一特征的是,评语中使用了大量的“你”字,这个“你”当然指的是书中人物。

吴敬梓塑像
如诘问陈和甫“教你跑到汶上县去的”,“你难道另有个分身之法么?”对邹吉甫说“你还不晓得,他如何会晓得;你还是才晓得,他自然不晓得。”嘲讽支剑峰“你方才为何不向西湖里,照照这副尊容,可像穿宫锦袍的李太白么?”责骂匡超人“等你侥幸,等你得个肥美地方,等你到任一年半载,等你带银子来帮衬他。不知潘三哥有没有这样造化,有没有这样长寿?”
总而言之,童叶庚在评点中很多时候表现得更像是原书中的人物,而不是小说的评点者。行文之间,尽显轻松诙谐之趣,也堪称是真正的沉浸式阅读体验,深合传统批评的特点。这样的评点方式在此前的小说评点中未曾出现,童评在小说评点形式上有开疆拓土之绩。
小说评点在发展至晚清时代能有童评这样一部率满戏谑精神的评本,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现实依据。尽管传统的文学批评多以正襟危坐式居多,但也滑稽游戏之风留以一隅之地。

《江盈科集》
如宋人周紫芝就援引孔子戏子游、史迁立《滑稽列传》为例,说明“俳谐之中,自有箴讽,或能感动人情,使之改过,是以有取焉耳。”[67]晚明文人江盈科还认为“谐语之收功,反出于正言格论之上。”[68]
此前小说批评中若隐若现的戏谑之语也证明着这一潜流的生命力。童评能将长期潜藏于评点中的戏谑精神大肆绽放,得缘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因由。
童叶庚早年曾出任德清知县等职,光绪年间即隐居吴门,读书度日,手抄群籍,无复出仕之志。其性通脱,故其著述也多富有机趣,著有《回文片锦》《醉月隐语》《斗花筹谱》《合欢令》《蜗角棋》等游戏著作,还将拼板玩具七巧板扩展为十五巧板,名曰《益智图》。由于其性格诙谐游世,故而其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也多能发掘其中之幽默机趣,一改传统的抽象概括式的评点文字,而赋予其以丰富的细节与艺术的灵性,从而使评点文字即有诙谐可观的游戏效果。
再者,晚清时代,特别是江南地区,游戏文字也风行于士人群体中。有学者将这股思潮归结为清代统治的削弱与正统思想的消退,新兴报纸的出现又为游戏文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传统文学脉络中被压抑的边缘文体开始积聚爆发的力量。新兴报刊所提供的自由宽容的表达空间,对受社会文化规范束缚的传统文人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69]
以《申报》为例,其主张的文章风格即是“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70],“在创刊的第一年8个余月的时间内,《申报》共刊登游戏文章20余篇。”[71]

《申报》
至1890年代,上海地区小报的《游戏报》《海上繁华报》《寓言报》《采风报》《笑林报》等小报更是喜登游戏文章。可见在童叶庚生活的光绪年间,以游戏为文章的风潮一直不绝于世。在这种背景下,文人往往“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72]逐渐形成“集轻松诙谐滑稽幽默、插科打诨、噱头打趣于一体的笔调风格”[73]
童叶庚晚年长时期隐居于苏州地区,接近江南文化的中心,其评点《儒林外史》的文字正是典型的游戏文章,其间虽也有对贪官酷政的抨击,但更多的是表现滑稽幽默的趣味。
如果纯粹从小说理论的角度来看,童评的价值或不能独标一帜,但小说评点研究毕竟不能等同于小说理论、小说批评研究,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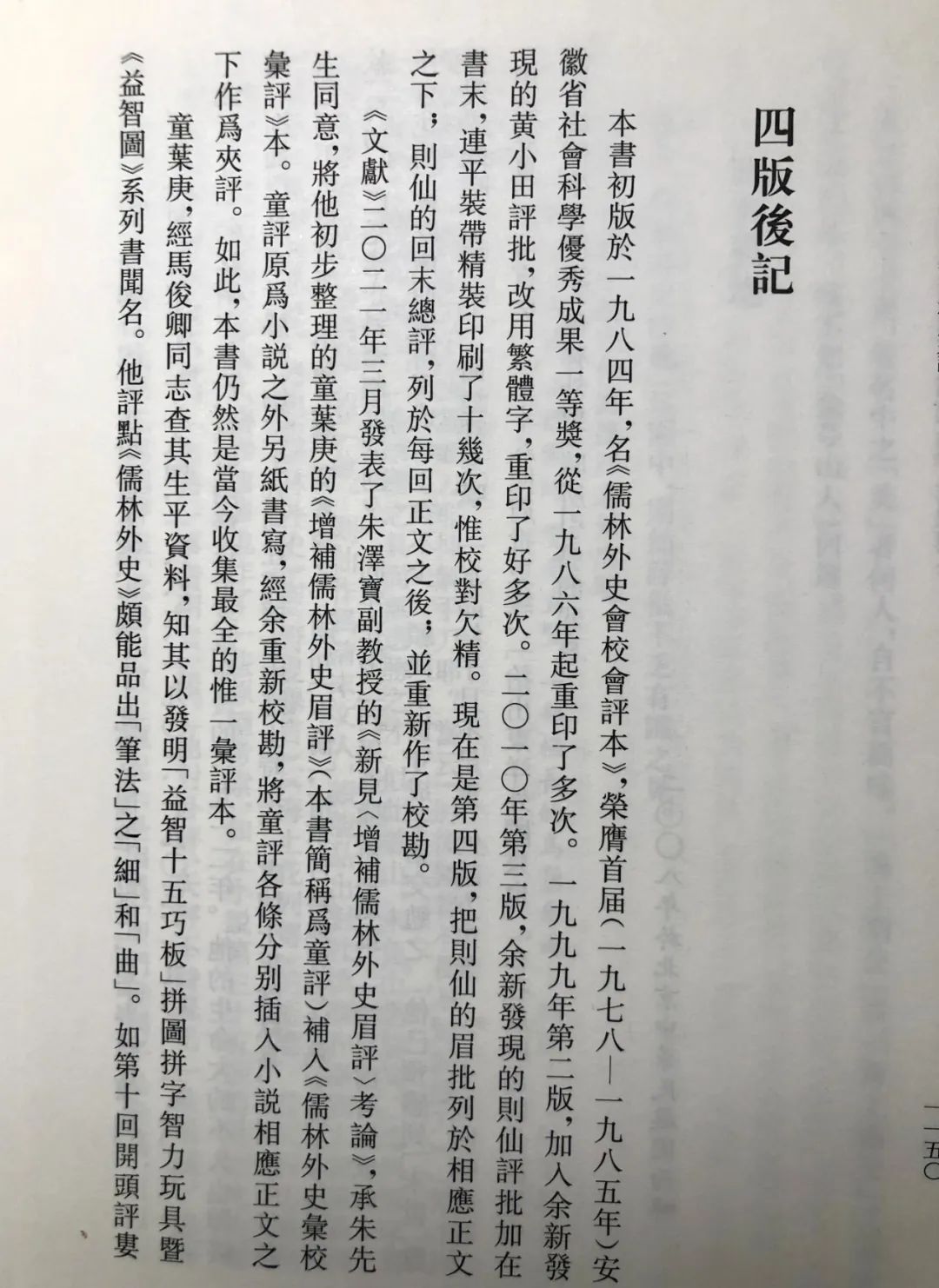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四版后记
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批评就可涵盖。”[74]童评的主要功绩就是在评点内容上的转换与评点语言的更新,极大地扩展了小说批评的表现力量。其对小说故事情节的深度关注,推动着小说主体价值的确立,而不仅作为文法或义理的标识或附庸;其对评点语言风格的更新,丰富了小说评点的表现形式,更生动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式的内涵。
附记:
这里汇报一下小文的撰写经过:我于2017年在浙江图书馆发现童叶庚《儒林外史》评点本,撰写《新见<增补儒林外史眉>》考论》,介绍此评点本的基本特征,并于2018年初投稿《文献》刊物,2021年3月见刊。《“论事”转向与语言狂欢——论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的小说评点史价值》则主要关注其小说评点史上的意义,发表于《文学研究》2021年第2辑。同样是2021年4月,李汉秋先生联系我,将童评资料收入其新修订的《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并于当年夏出版上市。谢谢师友们的关心。
注释:
[1]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九种,其中张文虎的申报馆评本与《儒林外史评》视作两种。后又新发现朱则仙评点本一种。
[2] 《增补儒林外史眉评·凡例》对所据版本有所说明:“后得齐省堂增订正本”“今岁里居多暇,重展是书而读之,心有所得,随手札记。”
[3] 本文所引《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中的文字均出自浙江图书馆藏抄本,下不出注。
[4] 在目前已知的十种《儒林外史》评本中,只有“则仙评本”中的若干评语作于1893年之后。见李汉秋《新发现的<儒林外史>则仙评批》,《文献》,2011年第2期。
[5] 谭帆《晚清小说评点麈谈》,《学术月刊》,2000年,第12期。
[6] 《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虽然数量丰富、价值巨大,但由于其评语抄于群玉斋刊本上,长期未见流传,且从其内容上看,并没有对童评本产生影响。
[7]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8]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9]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10]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11]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12]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13]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14]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15]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6] 李汉秋《新发现的<儒林外史>则仙评批》,《文献》,2011年第2期。
[17] 谭帆《论<儒林外史>评点的源流和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18] 卧草闲堂本前的闲斋老人序虽题作“乾隆元年春二月”,但学者根据评点出现的《燕兰小谱》推断其不可能早于乾隆五十年(1786)
[19]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页。
[20]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21]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
[22]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23] 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24] 谭帆《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25] 金圣叹《水浒传序三》,《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12页。
[26] 江守义《小说评点的伦理阐释》,《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7]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4页。
[28]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9] 陈维昭《论评点重构叙事》,《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30]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4页。
[31] 金圣叹《水浒传序三》,《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12页。
[32]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33] 王冉冉《以论说文文法评点小说结构——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一个本质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4]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5] 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36] 吕祖谦《论作文法》,清光绪廿四年江苏书局印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卷上
[37] 张文虎《天目山樵识语》,《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5页。
[38]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39] 周君文《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0]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41] 童叶庚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据凡例可知此评语写就于光绪十九年(1893)。
[42] 当然也不能排除童叶庚的评语先录于齐省堂增订本上、后来单独誊抄的可能。在目前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以下,本文仍以抄本为据。
[43] 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与评语》《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3辑。
[44] 如金圣叹评《水浒传》有“略犯法”“正犯法”,旨在说明作者“真是浑身都是方法”。(见《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5页。)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道:“《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见《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岳麓书社,2006年,第5页。)足见其意在借《三国志演义》前后情节的关联而讨论文章的“避”与“犯”。
[45] 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46]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2—393页。
[47] 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48] 詹福瑞在《论经典》指出经典作品具有“普适性”与“耐读性”。(见《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4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50]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51]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52] 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53] 申涵光《荆园小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54]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引自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55]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56] 谭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之类型》,《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57] 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607页。
[58] 遍照金刚著,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03页。
[59] 谭帆《论<儒林外史>评点的源流与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60] 李生龙《论对偶在古代文体中的审美效果》,《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61]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91 页。
[62] 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第48页。
[63] 张峰《戏拟的寓意与快感》,《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4] 陈维昭《<儒林外史>的互文、戏拟与反讽》,《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65] 朱光潜:《诗论》,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 页。
[66] 蒲安迪认为“奇书文体的首要修辞原则,在于从反讽的写法中衬托出书中本意和言外的宏旨”(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不妨称为“清代两大奇书”(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67]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372—373页。
[68] 江盈科《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439页
[69] 杜新艳《晚清报刊诙谐文学与谐趣文化潮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70]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71] 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95页。
[72] 《本馆重印丁酉戊戌两年全份〈游戏报〉明日出第一册》,《游戏报》1899年5月2日。
[73]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74]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