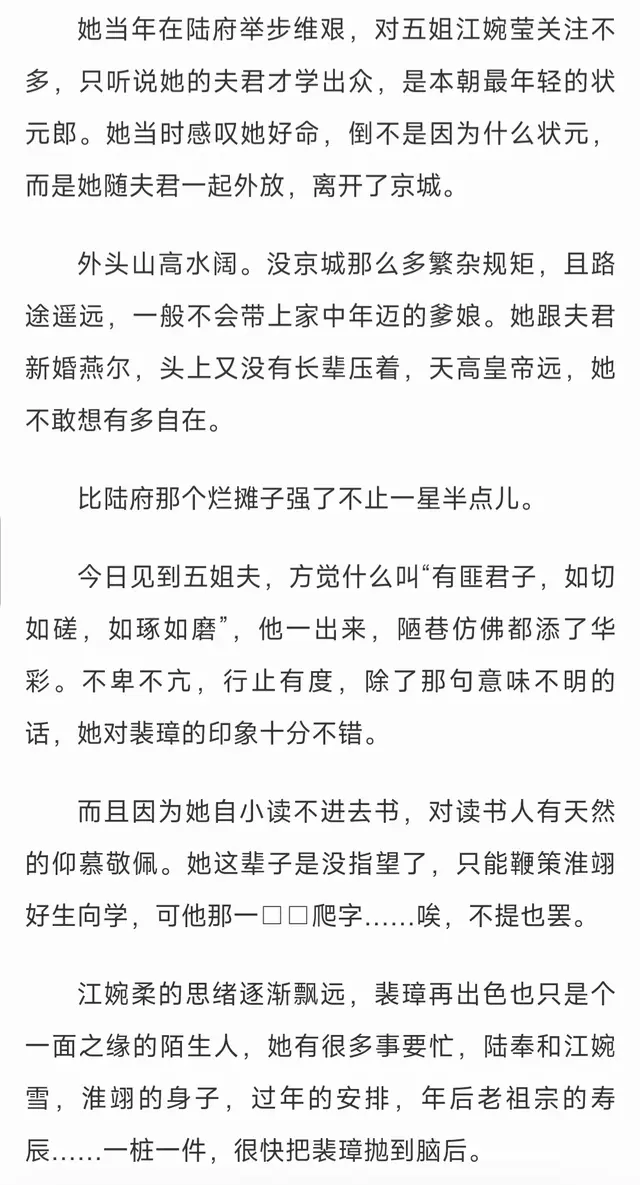太子不爱我,因为他嫌我脏。
可他忘了,我被马匪掳走,是因为他将我推出去,替他的心上人挡刀。
后来我想离开了,他却负伤来截我。
「孤想通了,若得不到你的心,得到你的人,也是好的。」
1.
我是太子妃,但太子不爱我。
这个王八羔子嫌我脏。
微服南下时路遇马匪,我被他推出去给柳书媛挡刀,不慎叫马匪掳了去。
我横在马背上,一边吐,一边给劫匪讲经、讲法、讲唐诗宋词三百首。
劫匪掏掏耳朵,顺手把我丢在路边。
「干特娘的,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能叭叭的婆娘。」
我爹没说错,男人果然最怕唠叨的女人!
我沿原路折返,晕头转向之际,突然看见宋檀驾马疾驰而来。
他来救我了!
我一下子酸了鼻头,眼泪汪汪地举起手,还来不及挥动,就看见紧紧贴在他身后、抱着他腰的柳书媛。
「殿下慢些,奴好怕。」
因她娇滴滴的一句话,宋檀立刻勒紧缰绳。
马儿溜溜哒哒地向我走来,悠闲得仿佛是在踏春。
若我是个外人,瞧见马背上那对神仙眷侣,一定会道声般配。
我瘫坐在路边,宋檀勒马停在我眼前。
他居高临下斜睨着我,半晌吐出一个字:「脏。」
我低头看着自己污糟的裙衫,一时不解,他是觉得我的衣裳脏,还是觉得因为我被马匪掳走,所以,我变脏了?
可笑我绞尽脑汁逃出生天,就是怕事情闹大,世人的唾沫星子会伤到我夫君的颜面。
可我死里逃生后,他的第一句话,却是嫌我脏了。
2.
惊吓过度,我生了场大病,这两日没怎么用饭。
宋檀来的时候,可巧我正跟春芜说笑,他自觉看透我,挑眉冷笑:「你装着茶饭不思,是在跟孤示威么?」
我没吭声,因为宋檀从不信我。
只是心口窝又开始绞痛,在我的胸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碎掉了。
我咬紧牙,身体蜷成一团,冷汗大颗大颗滚落,吓得春芜几近失声。
「呆着干什么,拿药!」
宋檀提脚踹在她身上。
其实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君子,唯独对我,对与我有关的人,冷漠粗鲁、毫不留情。
我和他青梅竹马十几年,他对我,从来没有好脸色。
他的青梅竹马太多了,而我,是其中最不得他喜欢的那个。
我之所以能如愿以偿嫁给他,不过是我比旁人听话,更愿意让他高兴罢了。
因为他喜欢的人,是个风尘的妓子。
他为她私建别苑、金屋藏娇,凡是高门大户的女儿,有几个忍得了此等耻辱?
可我忍了。
吃过药,我昏昏沉沉睡了一觉,醒来时发现宋檀居然还在房里。
他手里拿着话本,唇边带着一抹笑,瞧得津津有味。
我和他,鲜少有如此温馨的时候,可我竟觉不出高兴来。
我阖上眼皮轻咳一声,再睁眼,宋檀已正襟危坐,一张脸又挂上冰霜。
「起来吃口饭,一直耗着也不是办法。」
他起身吩咐春芜为我更衣,提脚先一步出门去。
春芜眉梢带喜,悄悄跟我讲:「娘娘,殿下这是关心您呢。」
我苦笑,关心一个人,不应是这样的。
3.
这桌饭,是柳书媛对我的答谢宴,感谢我挺身而出,才没让她落入劫匪手中。
她为我贴心布菜,见我半天不动筷子,宋檀忍不住敲打我。
「书媛贴心,知道你爱吃辣,这两日满城跑,试菜试得胃疼,才挑到这家酒楼,你尝尝,味道如何。」
我还是头一次听,给还病着的人吃油吃辣是一种贴心。
我对柳书媛笑:「你实在要谢还是谢谢殿下吧,若不是他推我一把,我也吓傻了,哪里顾得上你。」
她小嘴一瘪,握住我的小臂,喃喃细语:「姐姐,殿下也是情急失措,您千万不要误会,因此与他生了嫌隙。」
「不要叫我姐姐。」
我拂掉她的手,我再怎么也是堂堂太子妃,她一个妓子,凭什么与我姐妹相称。
「你不配。」
柳书媛愣在原地,宋檀陡然变了脸色。
我提脚回屋,他追了进来,肃然道:「周禧,此次出行为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书媛跟着你我东奔西跑,从未喊苦喊累,你不该戳她心窝子,太残忍。」
我此去迎我生母的牌位,本是件见不得光的事。
当日宋檀说会陪我一起,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结果出发那日,柳书媛却坐在他的马车里,开心得像个孩子。
原来他说陪我只是顺便,最要紧的,是要陪柳书媛游山玩水,为了让她高兴。
这一路,他们二人有多欢喜,我便有多难过,毕竟,我亲娘死了。
柳书媛如何戳我的心窝子,他看不见,听不见,她永远是他心里最最善良可爱的女子。
而我只是不愿与妓子姐妹相称,便是我残忍?
「殿下,你可知汴京城内,大家如何唤我?」
我拔下一只金簪捏在手心,半晌,温热的血水砸在桌上。
我是太子妃,但他们都叫我,哈巴狗。
我是太子妃,但在旁人眼里,我就是宋檀身边温顺的狗奴才。
宋檀耳目通达,怎会不知,可他却不曾为了我的名声收敛半分。
他说我残忍,可是他对我,何尝不是另一种残忍。
「周禧,一切是你自愿的。」
宋檀不冷不热地开口,他靠过来,泛凉的手指勾住我的下巴。
「如今你跟孤大吐苦水,是想以此为要挟,所图为何?」
是的,一切是我自愿,是我自轻自贱,才给他机会羞辱我。
可我也还记得,他说过,嫁给他或许得不到爱情,但是太子妃应有的尊重,他一分也不会少了我。
我强忍着酸涩,把眼泪憋回肚子里,冷哼道:「殿下若觉得柳姑娘受委屈,大可带着她回京去,将她好好儿地,供在软榻上,我看着你们二位,胃里恶心,实在摆不出好脸色,她若非要在我跟前碍眼,便得老老实实地受着!」
宋檀瞧着我,雾沉沉的眼底透着意外。
在他面前,我从来都是对对对,好好好,哪里说过一句刺挠人的话。
他以为是我本性懦弱,却不知道,那是我为讨他欢心的逢场作戏。
现在这戏,我不想再演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用不着二位费神。」
宋檀默了半晌,甩手走了。
4.
第二日早起,宋檀与柳书媛果然不见影了。
是了,他哪里舍得心爱的女人受我的闲气。
春芜换上一身小厮的打扮,闷闷不乐地抱怨:「娘娘,殿下的心也忒狠了,说走就走,当真是一点不怕伤您的心!」
我缓了会神,喃道:「本来也没指望他会陪我。」
此城离下一城有些距离,我租了辆熟路的马车,入夜前找到个落脚的小村子。
马车停在一户严姓人家门口,我挑开帘子一瞧,这家正在办白事。
白色的灯笼在冷风里摇晃,房子不大,一眼就能望到堂内的两个棺材,还有纸扎的童男、童女、马匹和宅子,映着一盏豆灯,格外瘆人。
「师傅,咱们还是换去别家吧,莫要打扰亡灵了。」
车夫已经跳下马,与我摆手道:「不打扰的,小公子莫怕,我常来他家里借宿,他家里穷,也靠这个赚些小钱。」
他如此说,我也不好再多话,不然倒显得矫情。
进屋后我给死者上了炷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死活想不出。
大概是眼下只剩我与春芜主仆二人,此处荒郊野岭,确实让人不踏实。
不过我想,宋檀应当留了暗卫守在暗处,倒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吃过晚饭,我觉得浑身乏得要命,春芜也是呵欠连天,我俩便早早歇下。
不知睡了多久,我听见车夫道:「这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要不是我之前见过,真要被她们这身男人装扮给骗了。」
「辛苦你,我儿总算不必孤单上路了。」
我头皮发麻,意识清醒着,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突然想起,那棺材明明是两口,却只有一个牌位,真是倒了大霉了,碰上配阴婚的了!
几人闯进屋,走到炕前,捏住我的脸左右端详。
「娘,我要这个当我媳妇儿。」
「不成,好看的要配给你哥哥,他在九泉下知你孝悌,也好保佑咱们严家发达,到时候要什么模样的没有?如今还是得留下个皮肉糙的,好干活,好生养。」
接着,我便听到春芜被人从我身旁抽走。
我惊恐交加,想喊想叫,却连哭都哭不出来。
有人扒下我的外套,趁机摸我好几下。
他们给我套上嫁衣,又在我的脸上涂涂抹抹,然后,我被人抬着手脚,放入棺内。
砰的一声,盖棺定命。
黑漆漆的棺内密不透气,我好不容易清醒的意识再次变得昏沉。
好多回忆像走马灯一样闪现,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恍惚间,我听到时近时远混乱的嘶吼声,棺材板被人撬开,眼前天光大亮。
「……小姐,别怕,我来接你了。」
来人不是皇家暗卫,因为,他们不会唤我小姐。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他的身影……此情此景,却和很久之前的一件事、一个人重叠在一起。
我开始怀疑,那时候奋不顾身前来救我的,真的是宋檀吗?
5.
春芜在我怀里醒来,第一句话,便是问我好不好、怕不怕。
我噙着泪,握紧她冰凉的小手。
她下身流血不止,难以想象,严家老二究竟有多禽兽,才会将她折磨成这样。
可是那个人/渣,却侥幸逃过一命,不知所踪。
秦方止驾着马车,衣料上有几个破口,稍显狼狈。
我从未想过,我与他还会有再相见的一日。
如今他是保荣府府主,是皇帝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是真正的一人之下。
如此高高在上、日理万机的人,怎会单枪匹马出现在这种犄角旮旯?
他是专程来救我的?可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越想越觉得头疼,疼着疼着,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是在一间雅致厢房,屋内有人,我下意识便喊道:「方止……」
那人身形一顿,慢慢踱过来,我才看清原来是宋檀那张冷脸。
一见他,我紧绷的情绪突然爆发。
我从床上扑向他,被子都被带到地上,他难得慌忙,伸手来扶我。
我揪着他的衣领,一遍遍嘶吼:「暗卫呢!暗卫呢!宋檀,你到底当不当我是个人!是不是我死了你也没所谓!我的春芜、我的春芜……」
按照规制,我本有两名皇家暗卫贴身保护,但宋檀说迎我生母牌位这件事不好声张,于是只带了他的几名心腹。
只是,他的心腹却不是用来护我的。
「周禧,你冷静一点,我留了追月……」
「追月人在哪里呢?我快要死的时候,她在哪里!」
我抹了把脸上的泪,盯着他的眼睛,不免自嘲地笑笑。
他是留了追月,可是,她根本没拿我当正经主子看。
她只用三分精力看顾我,又怎么能护我周全。
宋檀将我抱回榻上,我还揪着他的领口死不放手。
他看着我,眼里没有愧疚,没有疼惜,平静到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口吻都是公事公办。
「追月玩忽职守,孤会罚她。」
罚?怎么罚?什么样的惩罚能换回春芜的清白……她心里的伤,又该如何填平……
6.
宋檀之所以折返回来,是因为收到秦方止扣押追月的消息。
宋檀将她留下保护我,她却嫌我租的马车走得慢,快马加鞭先一步去下一城等着。
在那儿她约见几个同僚,喝酒闲谈起我,句句鄙夷,声声不屑,被有心人传到秦方止的耳朵里。
当时他正在青州城办案,那地方远在天边。
我实在想不出,他是怎样在短短半天的时间内查到我的下落,又孤身赶来营救。
若不是累极了,想他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刁民伤到皮肉。
追月的处罚,由我们几人一齐议定。
她跪在地上,浑身鞭痕累累。
宋檀沉着眼:「秦大人,你妄抓孤的人手,私自用刑,以下犯上,有没有把孤放在眼里。」
秦方止跷着二郎腿,大爷一样坐在首位,笑道:「殿下的人手,拿的可是我保荣府的月银。」
天下死士皆归保荣府调遣,只要身在朝内,还真没有他秦方止不能抓的人。
他转头问我:「小姐,你想怎么罚她?」
宋檀冷声接话:「她已嫁作人妇,自然是夫唱妇随。」
片刻停顿,又补充道:「秦大人,如今,你该唤她一声娘娘。」
秦方止眼底的杀意一闪而过。
我听着这话,更是想笑,去他奶奶的夫唱妇随。
「秦大人,按照律法,妄议主上受拔舌之刑,玩忽职守受斩指之刑,我可说错?」
秦方止笑眯眯地回话:「小姐英明。」
宋檀看着我凉凉的笑意,半晌无语,不说可或不可。
柳书媛轻抚着他的背,柔声道:「娘娘此番吉人天相化险为夷,追月这丫头也受了番皮肉之苦,不如,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罢?毕竟,她也为殿下卖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
我喝了口茶润润嗓子。
「柳姑娘还真是菩萨心肠,鞭子没抽在你身上,你倒替她觉得疼。」
我促狭地笑笑,恨道:「可我的春芜,谁人来疼?想来以姑娘的出身,怕是不知道好人家的姑娘丢了清白是什么滋味。」
「娘娘,您身份尊贵,不知咱们为奴为婢的苦处,今日看到追月的苦处,奴也是想到自己,才忍不住多说一句,娘娘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拿出身羞辱于我……」
她这番话要是跪着说还像样,她端着主子的架子,说什么为奴为婢,实在是无病呻吟。
秦方止将手里的茶杯重重放在桌上,他生得好看,笑起来却又冷又阴郁,唬人得紧。
「我平生最厌烦女人家哭闹。」
一句话,硬生生逼得柳书媛咽下哽咽。
「夫人。」
宋檀这时候记起来,我是他的妻了。
「拔舌斩指,追月此生便废了。」
他还指望着,我以他马首是瞻。
「废便废了吧,废掉一个,杀鸡儆猴。」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近追月,掐着她的下巴,一字一顿。
「若春芜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陪葬!」
7.
幸运的是,春芜的病好得很快。
可我却病倒了。
好几个大夫给我瞧病,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有个老大夫说,我这是心病,他劝我凡事想开些,然后开了几副滋补的药给我。
里头有一味叫金乌的药,似乎很罕见,听说宋檀将此城翻了个底朝天,才寻来二两。
春芜捧着药碗进来,欢欢喜喜。
「娘娘,您莫要再和殿下置气了,他心里是有您的,只是装作无情罢了。」
她从醒来到现在,从未在我眼前掉一滴泪。
我知她是不愿让我吃心,又怕我气坏自己的身子。
可她不知道,夜里无眠时我听到她咬牙啜泣,有多心疼,看着她强颜欢笑,我也心疼。
但有的事,她不提,我也不敢提,我怕戳到她的痛处,更怕她痛起来,我却无能为力。
直到某天,秦方止送来一只胖沙燕的风筝,春芜拿在手里爱得不得了。
我才想起来,她如今也不过十七,跟着我进太子府那年,她才将将十四岁。
正是贪玩的年纪,但因那死气沉沉的日子,要稳重,要端庄,要严肃,所以她再没摸过这些小玩意儿。
「放给我看看。」我笑着吩咐春芜。
她也实在馋了,半推半就地拽着风筝在院里跑起来。
我坐在石凳上,看她被一只风筝搞得焦头烂额,忍不住大笑出声。
她跺着脚嗔怪我:「娘娘,您别顾着看笑话儿,倒是来帮帮奴婢呀!」
我为她理理刘海,假装不经意问道:「我若不是娘娘,只是塞外的野丫头,你还愿不愿意跟着我?」
「当然了!塞外多好呀,奴婢听人说,那儿有半人高的草地,有五彩缤纷的湖水,可美了!还有吃不完的牛羊……」
春芜说着,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她眼睛亮亮的,只不过片刻又颓下肩膀。
「可惜,娘娘不是野丫头,奴婢也当不成小野丫头。」
我笑笑没说话,捡起地上的风筝逗她:「你连风筝都放不起来,还想当小野丫头,我可不认你这个妹妹。」
「谁说奴婢放不起来,放风筝本来就是要两个人一起的,不信您跟着我跑两步,再瞧瞧它起不起得来!」
我但凭吩咐,举着风筝跟在春芜身后跑,一口气没捯匀,忍不住咳了几声。
春芜听见动静回头张望,脚下却忘了停,正好跟转进院子里的柳书媛撞了个满怀。
8.
「狗奴才,怎么伺候主子的!」
宋檀将春芜踢翻在地。
他扶稳柳书媛,一转脸,结结实实挨了我一巴掌。
我大概是失心疯了,我怎么敢。
宋檀也没料到,他从来养尊处优,连一处皮肉都没擦伤过,却被我掌掴。
他眼红得像一只将要破壳而出的怪物,我却根本顾不得什么纲常伦理、君臣之道。
我只看得见春芜小脸惨白,捂着肚子趴在地上不敢吭声。
我紧紧抱着她,刚给她擦过冷汗,我的眼泪却又大颗大颗地砸在她的脸上。
「娘娘,奴没事。」
她死咬着嘴唇,抬手擦擦我的脸。
「春芜,你不要死,大夫马上就到,我求求你,你不要死,疼的话你就喊出来,你不要有事……」
我泣不成声,把头埋在她的怀里。
她跟着我着实是受苦了,我还没能好好补偿她。
我什么都不求了,钱、权、情,我都不要了,只求老天爷让她好好的。
「娘娘,奴,好疼啊……」
春芜的声音夹杂着细碎的哽咽,那些哽咽连成片,渐渐化作哭嚎。
「奴好疼,春芜好疼啊娘娘,春芜好怕……我疼……」
大夫说,春芜的身子骨,日后恐怕没办法生养了。
宋檀拉着脸站在旁边,他在等我怪罪,我在等他道歉,我们硬杠着,谁都不服软。
柳书媛幽幽地叹了口气:「娘娘,您就是再大的脾气,也不能跟殿下动手啊,那是大不敬……」
宋檀摆手打断她。
「春芜这丫头毛躁,若不好好教训,迟早出乱子,孤教她规矩,也是为她好,不过是一个奴婢,不值得你为她伤了身子。」
若我跟那些正经的高门小姐一样,或许于我而言,春芜确实只是个奴婢。
可我只是父亲征战途中留在塞外的一个野种,他连一个名分都不愿给我生母。
我是七岁那年被接回将军府的,只因为主母的女儿夭折,我被塞到她房里,以解她寂寞。
她心情好时便对我笑笑,心情不好时,便对我辱骂殴打。
对外我是将军府的小姐,荣光至极,对内我是塞外来的野种,不如猪狗。
幼时煎熬,我的身边,只有春芜。
而这些事,宋檀是知道的,他知道春芜于我而言有多重要,却还是轻飘飘的一句:不过是个奴才。
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拉起衣袖,露出一截手臂,上面有两道深深的爪印。
月前出发上路,柳书媛带着她的爱猫,她那猫脾气不好,她还非要往我怀里塞,结果,我就被挠了一爪子。
当时宋檀是怎么说来的?
哦,畜/生不懂事,他要我仁慈。
遇上柳书媛,所有事他都能宽厚,可遇上我,所有事都让他躁恶。
「既然殿下是为我好,那该罚的,便一并都罚了罢。」
我冷眼盯着他,便是要看看,他这副虚伪的嘴脸能装到什么时候。
他咬咬牙,缓缓开口:「孤让人把那小畜/生打死,可能让你心里舒服?」
柳书媛忙求道:「殿下,不要啊,玉儿是奴一手养大的,若是它没了,奴也不要活了!」
「不过一只猫,明日再寻其他便是。」
她见他心意已决,又扑倒在我脚边,哭哭啼啼可怜兮兮。
「娘娘,求求您饶过玉儿,它是个畜/生,它不懂人事的……」
「它不懂人事,但你懂啊。」
我笑盈盈地牵起她的手,「当日,可是你亲手将它塞进本宫怀里的,这么一双毛躁的手,若不好好教训,迟早惹祸,殿下,您说是不是?」
9.
我命人拔掉柳书媛的指甲,宋檀竟未阻拦。
那一巴掌后,我本以为他会与我渐行渐远,可没想到,他来我这儿倒是比以前还勤快。
他跟我服软:「春芜日后便养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必做,养着便好,孤看你日渐憔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人性本贱,果然没说错。
春芜近来常常发呆,我怕她做傻事,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有一日,她突然说想吃我亲手做的桂花糕,她难得有食欲,我便命人好好地看着她,抽身去了小厨房。
可等我回屋时,屋内却一个人也没有。
没来由的,我的心脏突突直跳,冲出院门,没头苍蝇似的找了两圈,听人说,后花园里有人投湖了。
一路飞奔过去,就看见春芜浑身湿透跪在地上,朝同样湿透了的宋檀磕头。
宋檀瞪着跪在一旁的另一个丫头,「让你看人你就是这样看的?自去领罚。」
又恶狠狠地扫过春芜,恨道:「你自寻短见可想过你家娘娘日后如何自处!若不是怕她难过,孤定成全你,让你死得干净!」
春芜只是哭着告罪,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
我冲过去将她揪出来,前后左右仔细检查一番,确定她全须全尾,方才松了一口气。
「桂花糕刚出锅,你回去趁热吃。」
我没头没脑地,只说出这么一句,接着一股委屈涌上来,我甩手转身走了。
春芜巴巴儿地跟在我身后抹眼泪,口中含糊不清。
「娘娘,您别生奴婢的气,是奴婢对不起娘娘……奴婢如今就是个破/鞋,哪还有脸活着……」
我一巴掌甩在她脸上,只想打醒她。
「世上哪有东西比命还重要!」
她低着头,半晌,哽咽道:「娘娘就比奴婢的命重要!柳姑娘说,回京之后若被人知道,您身边带着我这样一个生不出蛋的母鸡,一定会连累您的名声……」
我猛地攥紧拳头。
原以为拔甲的教训能让柳书媛学会收敛,可没想到她这么不安分,非要给我找不痛快。
她被宋檀宠坏了,她以为她是一颗珍贵的宝珠,而我会让她明白,她不过是一根注定会被拔掉的鱼刺。
10.
安顿好春芜,我打算去秦方止那里用晚饭。
出门前宋檀打着喷嚏把我拦着院里。
「孤救了她,你便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谢谢?宋檀啊宋檀,你能救春芜一命,那是老天爷给你个机会赎罪,你倒拿来请功了。
我沉着脸往外走,他将我拽进他的怀里禁锢起来。
「你要去哪儿?」
我像个死物一般,不推不攘,只是无比平静地开口:「去找秦大人,用晚饭。」
他的手臂收紧,勒得我生疼。
半晌,宋檀在我耳边哼笑:「自从你遇到秦方止,对孤便连个笑脸都没有了,怎么,旧情复燃了?」
天地良心,我和秦方止从无瓜葛。
我不知道宋檀怎么就冒出这样一句话,当然,也懒得解释。
我不吭声,他当我是默认,捏着我的肩膀将我推开,低声吼我:「周禧,你还要孤怎么样,从小到大,孤何曾对谁低声下气过,谁又敢动孤一根手指,这些你都得到了!你还想怎样?你若不爱孤,何苦当时要嫁过来!」
嫁给他,只能怪我年少冲动。
思春的少女,谁不想嫁给舍命相救的英雄,谁不渴望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谁不自视甚高,以为单凭一腔热血,就能捂热一颗冰凉的石头心。
我也想问一问:「殿下也并不爱我,又为何娶我?说到底,你我结合,不过是你瞧我好拿捏,我看你权势旺,顺势而为最好的选择罢了。」
他瞳孔微颤,慢慢松开手,表情寂寥。
「所以,你嫁给孤,便是为了一个太子妃的名号?你那些小意温柔,果然都是装的是不是……你爱的人,一直都是秦方止,是不是?」
他哀叹的尾音随风飘远了,我只是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殿下若是气不过,不如——和离?」
本朝还未有王公贵族和离的先例,我不介意成为先例。
宋檀神色突变,我很少看到他如此失态,只是片刻,他抹了把脸,又恢复一派镇定自若。
他笑着,眼底却全是莫名的悲伤,凑近我的耳朵,他道:「周禧,你就是化成鬼,也是我太子府的鬼。」
11.
我与秦方止做了笔交易。
宋檀一直忌惮保荣府,若他即位,秦方止八成会被治罪。
我有一计,可以把宋檀从太子之位拉下来,顺便,让柳书媛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出发去塞外前一晚,秦方止办了践行宴。
宋檀亲自来接我,近日他与我虽无话,但行为却处处体贴,柳书媛看在眼里,脸色是一日比一日难看。
到了地方,才发现席上还有几位外族的行商,听说是秦方止日前托他们找了些好宝贝,今日给送来了。
宋檀一下变了脸色,他自持身份,不肯与商贾同席,说了几句难听话。
我自当耳旁风,只道:「若秦大人不介意,那些好宝贝,不如同赏。」
「殿下平日里也不曾亏待咱们,即便娘娘爱奢,也不好如此眼热,失了殿下的脸面。」
柳书媛边说着,边两只手叠在一起揉搓,腕子上的金玉宝珠磕磕碰碰,叮当作响。
我眼一横,扫过她裹起的十指,她立刻噤声。
宋檀确是得过不少好东西,不过从来都是她挑剩下的,才拿来给我。
平日里不觉得,眼下两相对比,便显得我这个太子妃实在太过朴素。
「你若想瞧便瞧瞧吧,有什么喜欢的就告诉孤,买了当个玩意戴着玩儿,等回京,孤再为你寻珍宝。」
我笑而不语,宋檀轻叹一声,随我落座。
说起来,我朝地大物博,不缺好东西,唯一的,便是离西海远了些。
西海珠是远近闻名的宝物,每年朝贡必有它的身影,只不过数量稀少,宫里的娘娘/们瓜分过后便不剩什么了。
今日有幸,在宴席接近尾声时,看到一匣子鹌鹑蛋大小滚圆的西海珠。
那行商捧着它,话里话外都是炫耀得意。
宋檀问我:「喜欢吗?买来做副头面应当很配你。」
那边立刻接话:「对不住殿下,这东西咱们不卖。」
「对,不卖你。」
外邦人心眼小,宋檀方才无礼,他早狠狠地记了一笔。
我对珠子倒无甚兴趣,只是余光瞧着柳书媛,她果然看痴了。
柳书媛曾得过一串西海珠的挂佩,爱得跟什么似的,她对那东西可称迷恋,可依我看,她迷恋的是权利、地位,是旁人艳羡的目光。
她膨胀的虚荣,迟早会扒了她的皮。
等到行商离席去解手,她也坐不住了,找个借口跟了出去。
不过一会儿,一个小厮垂首近来,趴在秦方止耳边嘀咕。
他脸色微变,眼尾扫过宋檀。
以宋檀的脑筋,几乎是立刻,便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小厮小跑着在前头带路,女人的低吟声越来越清晰,我故意喊一声:「殿下慢些,小心路滑。」
低吟声戛然而止,忽然变成一阵凄惨的叫喊:「求你饶了我,救命!」
然后就听见男人打骂道:「臭婆娘,鬼叫什么!」
柳书媛被摁着趴在假山上,男人在她身上起伏,场面一片混乱。
她哭着叫喊:「殿下救我,殿下……」
男人听到脚步声,回头看见我们一行人,脸上错愕之后,望着宋檀狞笑。
「这女人是你的娘/们儿没错吧,她……」
他话没说完,柳书媛突然拔下金簪,想也没想就刺穿了他的脖颈
她捂着胸口跌坐在地上,摸着脸上的血,颤声道:「殿下,奴杀人了……奴,杀人了……」
她拽着宋檀的衣袍泣不成声。
「是他该死,是他该死的,殿下,他对殿下怀恨在心,就想欺辱我,奴是自保啊,殿下……」
另几位行商听到她这样说,立刻跪倒在秦方止眼前。
「大人!我哥哥是什么人品,大人是知道的,他绝不会欺压良民,这女人能近他的身,定是投怀送抱!如此浪荡的毒妇,如今杀了我哥哥,还要含血喷人,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秦方止略显为难地看一眼宋檀,后者强忍怒火,命人将柳书媛搀扶下去。
「秦大人,孤的女人会向旁人投怀送抱?你的朋友吃醉了酒,今日欺辱到孤的头上,那是死得其所,至于剩下这几个,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果然是护着柳书媛的。
12.
宋檀与柳书媛到底有了隔阂。
柳书媛虽是妓子出身,可遇到宋檀的时候还是清白的处子,如今,她却被另一个男人玷污了。
骄傲如宋檀,怎会容忍自己去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说到底,柳书媛于他,也不过一个玩具而已。
能做帝王之人,都是没有心的。
柳书媛这会儿倒学乖了,她做小伏低的样子倒新鲜。
解气是挺解气的,可还不够。
我们在天黑前赶到青州城落脚,这地方离塞外已很近了。
入城前受到好一番盘查,一问才知,近来城中少女频频失踪,出入城的车辆都要严查。
「今夜,孤陪你?」
宋檀不着痕迹地吞了口唾沫,见我点头,他眼中流过一抹喜色。
忽然想起年少初遇时,他对我也曾如此时一般,羞涩地别扭地示好。
只是后来不知哪里出了差错,他予我的温柔,像是一夜之间蒸发干净。
今晚正好赶上青州城的花神祭,进客栈时我多瞄了两眼满街的花灯,宋檀便提议带我出去走走。
「孤会护你周全,你只管放心玩。」
听他这么说,我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柳书媛也想跟着,我道:「人太多只怕殿下顾不过来,殿下带着柳姑娘去玩罢,我也乏了。」
曾经无数次,我如此番识趣地退场,眼睁睁看着我的夫君同别人柔情蜜意。
只是这次,我转身回房时,宋檀拉住了我。
「你日日闷在房里,身子都不好了,走吧,孤今日只陪你一个。」
柳书媛攥紧拳头,咬唇道:「可是殿下,奴一个人害怕……」
「好好待在房里,自己不往枪口上撞,难不成那些瞎了眼的狗东西还能整日只找你的麻烦。」
宋檀冷着脸,不知是不是又想起她在别人身下娇喘的模样。
他们两个撕破脸的样子,可真好看。
因为临近边塞,青州城内的外族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人高马大,我挤在其中,就像只随波逐流的小鸭子。
宋檀笑着搂住我,见我顺从地靠在他身上,他道:「夫人今日,好乖。」
我抬头对他粲然一笑:「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机会。」
他微愣,不明白我什么意思。
「宋檀,我们之间,永远没可能重修旧好了。」
我贴着他的耳,「你无数次弃我于不顾,我恨透你了,我/日日夜夜,都祈祷着你能下地狱。」
「孤没有……」
我把袖中的小刀捅向他,他猛地推开我。
身后有人顺势把我拽入羊肠小道,眨眼的功夫,我就被人流淹没。
最后一眼,我看到宋檀伸手想要抓住我,他大叫着我的名字:「阿蒲!」
那是我的乳名,蒲公英的蒲,意思是新生和自由。

13.
我骑着马,一路疾驰向我的家乡去,春芜应当已经快到了吧。
从今日起,太子妃周禧死了,死在青州城,死在那伙寻仇行商的刀下。
当然,这只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真正遭殃的,是落单的柳书媛。
她杀了人家哥哥,人家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
那伙行商一路尾随,就是为了找到机会对她下手。
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对她手软,那些胡蛮子有的是折磨人的法子。
我也不觉得,不能亲自看着她生不如死是种遗憾,我怕脏了自己的眼睛。
至于宋檀,他包庇妓子行凶,此等目无王法之人,怎么配得上太子之位。
我听见身后有马蹄声渐近,还以为是秦方止,回头一看,却是吓得差点从马背上跌了下来。
宋檀没命似的赶着马追上来,他的护卫弹了颗石子,惊动了我的马,我被颠下马背。
宋檀在不远处翻身下来,拖着步子走向我,血染红他半片衣襟。
我不敢相信,我想杀了他,可他居然负伤追了上来。
「宋檀,你不要命了!」
他蹲在我身前,笑道:「孤说过,孤会护你周全,以前会,现在依然会。」
他伸出染血的手抚着我的脸,喃喃问我:「阿蒲,你可看清了,我是谁。」
他眼里有疯狂、有期待,有放空的失神,仿佛透过现在,想到过去某一瞬。
见我不答话,他笑:「是我啊,我是宋檀,拼死救你的人是我,不是秦方止,永远都不会是他秦方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冷冷地瞪着他。
「你忘了,阿蒲,你真是个没有心的女人,你伤透了我。」
他猛地抱住我,「十三岁那年你遇险,明明是我救了你,我为你挨刀子,可你喊的却是秦方止的名字。」
我微怔,「我知道是你救了我……」
「可是你喊的是秦方止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却喊着别人的名字。」
他粗声打断我。
「明明是我救了你,可你遇险时期待的人却不是我,你让我像一个笑话。」
当年获救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即便我喊的是秦方止的名字,他那时是我家府兵的总教头,我希望他来救我又有什么不对?
「所以,你就因为我神智不清时喊出的一个名字,一直记恨着我。」
我突然反应过来,宋檀对我的态度,便是那时候冷下来的。
「它不止是一个名字!孤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想着其他男人!阿蒲,你心里明明装着别人,却装作爱我的样子留在我身边,孤是未来天子,怎么甘心做旁人的替身!」
他停下来,似乎是想听我说些什么,可我只觉得荒谬,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不过,孤想通了,与其看着你嫁给别人,还不如你心里揣着旁人,留在孤身边,孤得不到你的心,得到你的人也是好的。」
他把头埋在我的颈窝来回磨蹭,就像一只寻求安慰的小兽。
「阿蒲,你休想从孤身边逃走,孤说了,即便你死,也是我太子府的鬼。」
他身后,几个护卫已经全部倒地。
秦方止抽刀劈下,宋檀的血溅了我一脸。
他倒吸一口冷气,呕出的血顺着我的脖子往衣服里灌。
「阿蒲,你记住,孤就是死了……也是你的……夫……」
秦方止把他从我身上踹开,漠然道:「他识破了我们的计划,不能留了。」
宋檀居然就这样咽气了。
若他不追来,他本可以不用死的。
他是看破了我的计划才来的,还是说,真以为我遭了难,所以赶来救我?
……罢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真的会有人因为一个名字,赌气赌上好几年吗?」
我看着宋檀那张死不瞑目的脸。
秦方止将我从地上抱了起来,只说不知道,「反正我不会。」
他顿了一顿,告诉我当年的真相。
「我本可以早一天救出你,但宋檀为了让你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砍断了我的马腿,等我再赶过去的时候,你已经被他带走了。」
秦方止说,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宋檀偏执幼稚的人生中,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14.
之后的几年,我时常会梦到宋檀,梦里我与他隔着一条河,他浑身是血,站在对岸朝我挥手。
「阿蒲……是我……我是你的夫……我来接你了……」
那些声音离我很近。
无数次我被梦魇住,都是春芜摇晃着将我叫醒。
她三跪九叩,去天山上替我求了一尊佛放在床头,慢慢的,我的梦魇好了许多。
我与春芜安家的地方离青州城很近,闲时我会带她到城里去采买。
有一回,我在街角看见一个裸着下半身的女人,有个男人骑在她身上发泄过兽欲后,扔给她一个铜板。
听人说,女人是几年前来这儿的旅客,被一伙人糟蹋后光着身子绑在马上,在城里跑了三圈,然后就疯了。
女人名叫海珠,因为她嘴里总是在嘟囔:「海珠、海珠、我的西海珠……」
春芜小脸煞白,问我要不要帮帮她。
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善恶轮回终有报,我不是菩萨,管不了那许多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