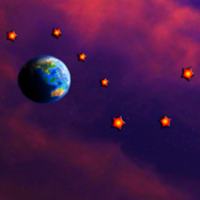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曹旭
前接:萌一、生二

仿佛梧桐从无婆娑共舞,层层叶片布满灰尘,惘然从无风和雨,再见清水的洗涤,那遥远家乡漕渠,前面水泥厂和此处火电厂飘落的灰尘,在整个春天,在夜里积累为垢,并不盼望雨水而来,那万千的桐叶,将会沿着斜坡,垂落黑色的泥滴,整个医疗室一墙之隔的房间,异常的热闹。
虽非新居,依然可以庆祝,因为从乡下终于搬来的城市;尽管旧房公房,毕竟一家团圆。不在城乡东西奔波的夫妻,孩子聚少离多,出门就是可以上的学校,抬腿就是工作。平缓的没有一沟褶皱。哪怕拥挤,尚可腾出地方,足够同室欢聚;哪怕抽屉拮据,不多的粮票和饭票,同事们买来七只猪蹄,一盘花生,摘来红绿的菜蔬,一碗开满松花的鸡蛋。还有呢,足够的三瓶伏牛山的烈酒,就是要庆祝。
农村户转商品粮了,孩子到许县高中附属的初中入学了,蒙月兰安排到子弟小学工作入职了,当然应该庆祝。摇晃起伏的口琴,岁岁悠长的竹笛,喜极而泣的三弦,即便只是紫檀色的桌面,是野的鼓点。上初中的斐斐兴奋地忘记了白天报名,改成李非,那是迁移户口时的祈祷,那是兰贵生郑重的期望与祈祷。
并没有多少安稳的日月,也许是足够房间拥挤的缘故,也许各种迁徙的困难一朝克服。没有的夜梦纠缠化为云烟,贵生兰不是便非,旧伤揭开,新创不断。黑夜不再是星光在唇间娓娓流出幽静的曲调,黑夜已经失落了家属区楼屋的轮廓静谧。在礼堂观看电影的人们,听到了被怒斥叫出去的蒙月兰的求救呼喊。又是一个殴打老婆的夜晚,谁能不在周末赋闲?李非从《上甘岭》的银幕上急奔而下,这个夜晚怎么了?父母怎么了?疯狂的夜晚。
不知度过多少喜乐悲欢,看见苦夏冬寒,尽管家属区的李非和厂区一墙之隔,却要绕过很长很长的一段黑暗,过两道门岗,方可到达厂区。医疗室前的那棵桐树一侧,曾经是斐斐疗伤后晒太阳的地方,光灿灿的暖和和的晃人的眼,而此夜却如此黑暗,只有医疗室的暗光,幽怨的明示。
“跪下,求你爸爸回去!”蒙月兰已忏悔工作忙,不顾家,旧怨恨不纠缠。李贵生分居多日,执意不回。蒙月兰带着孩子在夜里求他了。李非莫名其妙地跪下,麻木的回答母亲:“爸,回家吧”。弟弟喃喃着听不清哀求什么。黑夜之上的天空,看不到是否倾斜,深邃之中看不到天河与传说,却传来一阵琴声。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满天飞。”哦。是李贵生斜躺在折叠的褪色的绿军被上,两只鞋子交替着,冲着母子三人伸开,吹响着军营的傍晚。哦,难怪父亲曾用的笔名叫战飞,自己的斐斐是飞飞。似无志怪神话,李斐不无联想。“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满天飞”。

一口枣色木箱,一台方形餐桌,还有一口后来制作尚未油漆的桐木白榨箱。两只漆了枣色的钢条背的一小椅子。枣红床和五斗柜,还有另一口箱子,被拉到蒙月兰的二姐家,是娘家知道闹腾后的郁闷伎俩。
第二架车是两口木柴床,床面靠床面立在架子车上,一侧是铁锅炒菜的煮饭工具,一把刀一柳木案板,黄皮碗,印有鸟花呜盆之类的;一侧是被单包好的棉被衣物,没有带上李非木质的两扇木匣,以及那四片小木凳。
还是兰贵生兰分居期间的一个暑假,这个城市或者其他的城镇。工矿区生产计划下的不少机器停了很多,轰鸣声略以萎缩,一切仿佛平静,唯有几只疯倦的鸟儿偶或低鸣,还有树枝上的残蝉,盲目而嘶哑的喊叫。
少年李非和弟弟,在小木工厂捡来桐木条,在好多日未落雨的泥叶桐下,左测右量,菜刀劈砍,叮叮咣咣,制作铁合页可开合的两片木匣。单匣一米高,两尺宽,三寸厚,内钉隔层,可以放一百多本小画书。自行车推着,在五一路南口糖果店的橱窗玻璃下,摆摊租书。一本两分三分的,首日无果,次日挣了五毛二。分钱交给妈妈一块八的次日出摊,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酷烈的阳光照耀下伸展而来,是爸,严厉地给了五块钱,不准再丢人的八十年代。
李非并不遗憾那小劳作,还有很多东西,杂乱一地在阴暗的那间楼屋里,不必带走,无暇带走。他只默默的推着车子栏杆,看到母亲的后背湿透了素衫,汗染深浅褐色。所幸稍重的车,一个邻居帮衬着一同拉回,一件件财产,分别摆放在子弟学校五年级教室的讲台上,两辆木车由邻居叔叔和李非拉回去。空空还了;言言谢了。
刚要开学之前,有同事们的帮助下,租下了距子弟小学不远的一间草屋,收拾了满屋的杂物,刷了白灰。再少贴报纸于土墙,摆靠两张木床,房子里虽无窗却也阴凉,北面木门打开亦可采光,即使常常短路断电,有蜡烛可晚饭读书。
秋雨浸淫至极,不好,清雨渗入屋顶变浊,又透过几十年的暗红荆棚,滴落在床头的木箱上,在那白渣箱子无声洇下,却又怦然有音,是那当年作为嫁妆的枣红箱子被砸中,惊醒梦人。连阴了,雨大了,锅盆不够接了,还滴落在蓝色的单子上,只好睡在母亲的床头,称那只破伞在床,遮蔽漏雨,抵御漫漫夜,凉凉秋寒
赐夏侯氏以置塚的曹丕曰;“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草虫鸣何思,孤鸟独南翔?愿飞安得翼,欲既终有梁”。

几乎要忘记时日,到父母房间不大愿意看那口枣红色木箱,或者看一眼就跑开,在梧桐枝叶摇晃的阳光里,进入另外世界。青蛙的孩子小蝌蚪,大闹天宫的美猴王。已忘记那红色苹果的清香,那清香在父亲打开木箱的瞬间,扑鼻而来,喜落交融,霜降之前,存储已够,芬芳甜化。
生长在天空般的红色果实,在黑暗里亢奋成熟的红薯,霜降之前,食若青果而苦涩,木柴一样硌牙,煮熟也难下咽。四叔从七奶奶的屋里过来,一双筷子捣着黄皮碗里的红薯,一边给斐斐念叨:“白菜帮,吃得香,捣红薯,赛甜酱;白菜帮,吃着香,煮红薯,王母娘娘的白玉汤。”满屋的人无不喜乐。
紫红色的红薯,在霜降之后,甜脆若刚采摘的苹果,淡淡青涩,不宜多食,寒心伤胃;却易储存。走到去接父亲回来的那条铁道上,黑色的枕木层层向东,延迟到京广线的支线铁轨,有些莫名恍惚,而红色石块铺就的路基上,处处是一层晾晒的红薯薄片。
红薯干易于保存,不像榆树嫩叶、白色榆钱,槐花桐花,要吃个食鲜。“发霉的洗洗干净,还能煮”,疲惫的母亲虚弱的吩咐李非的褐暗桌铺。若岸沚静水,荡开肆意的涟漪。
原来的食物品种多样。母子荷荆篮,掂小铲,清明前后,槽水浇灌而猛长的野菜,已经布满麦垄,众人熟悉不过。只是若七奶奶生前的老一辈,恐惧那些树花嫩叶,那些河草野菜,无法面对解放前的苦难饥荒。而于斐斐母子,还算口食。而那秋玲中的蟋蟀,子弟学校那几盏如星的银灯映照,齐聚而来,左右蹦跶,捕捉不及,但现在的三天只能清煮红薯片,宴飨少年。以待蒙月兰工资发放,便一切无虞。
黎巴嫩的纪伯伦说:“当咀嚼苹果之时,你的籽儿要在我的身中生长,你来世的嫩芽要在的我的心田萌茁,你的芬芳要融为我的气息,我们要终年的喜乐”。
余音袅袅,七年不绝。
后来李非在纪伯伦的诗行下批注:我饮食你,正如大地将饮食我的血脉与尸骸。

橡胶厂的三百米之外,便是流淌了两多年的曹魏运粮河,河水潺潺,有不少的垂钓者。“哎,上钩了。”钓者沉静,像傍晚,若智者,并不言语,却按捺或根本无多喜乐的果断扬杆,只有孩子们雀跃抚掌。
于是,傍晚家属院的谁家,便飘出炸鱼的香味,贺鹏拾出几条,跳蹦下楼,来喊李非:“我爸钓的鱼,钓的鱼,尝尝。”那是夏季的天食美味了,味蕾铭刻于记忆深处,流淌在血液里,不知何处何时,总会醒来,在潺湲的生命流动中抽搐。两个少年在薄暮的梧桐下,旁若无人的偶尔言语,不觉微笑。
李非跟着师傅习武,简单的跑步压腿开始,弓步箭步,拳形掌立入门。“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李非默念着《长歌行》,稳扎马步,要和几个师兄比耐力,较意志。而不幸的一个傍晚,马步站桩,眩晕倒地。曹师傅对李非的母亲说:“蒙老师,孩子缺营养,饮食要跟得上”。
李非父母离婚的消息,在初中二年级三班中传播,明面暗里,李非沉默着,郁结了仇恨。母亲的二姐对人说,不是我去他厂里让他丢人,他的儿子都要改性了。新学期报到,他抑制着有些纠缠的舌头,好像不知道说要改名叫“蒙连杰”。
蒙月兰在家训导儿子,又给班主任解释,酷热渐退。那年代,李连杰是全国青少年的偶像,赳赳少年,喷张青年,在影院里,一遍又一遍的收看寺院里的拳法腿迹,刀剑枪棍。李非有章法的春晨夏晚,基础的五步拳,推掌勾手,盘肘弹腿。暑尽秋霜,年复一岁,依然“霸王举顶,左右缠丝,大鹏展翅,乌龙投海。”招招式式,英武少年,众师兄莫不喜乐;瘦弱的贺鹏壮实多了。
经多次申请,校领导和同事们帮衬,蒙月兰分到了家属院旧楼的三层小套房子,窗前就是那棵将要开满紫色花朵的巨大梧桐。春节前的梧桐下,李非拉着半车的煤块到楼口,抹污了汗湿的额头。对面新楼上的贺鹏,看到大声地喊着,跑下来帮,忙一摞摞搬上去,弓腰放在斗室的木床下,放在阳台做成的厨房里。在打煤场返回两趟,才能拉回的煤块,一部分要放在楼道里,报纸盖了,压上砖头,两个少年互相看看,拍拍掌中的煤屑。
夜已深沉,蛇一般的静寂里,仿佛听到了飞鸟的歌声。天狼星在运粮河波上撒下一道长长光泽的密言:生动的未知,通过梦想和身体的槽渠,流入少年的心田,生根萌芽,成长茁壮,根须向黑暗处探索,枝头向光明探望。

“这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她离开讲桌的目光,俯视一切,燥热的风,撩起她鬓角的一缕卷发。“本轮摸底考只有三个不及格。”她对门口的少年的报告和敲门声,置若罔闻。哪怕两种声音混杂着有些扭曲或者是浑浊。怎么又迟到了你?她想。“金黄的麦子要收割了,我们将面对人生重要的一次角逐,你的卷子已经铺开答题,还有五十天的时间可以预备”。
优雅的语文老师句句田垄,字字麦粒;田垄归正而绵延,麦粒圆润而坚实。已坐回到后排的李非,并不收听关于夏风或者麦田的信息,一行行推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必有得于天使者矣”的复习资料,窥视着卷子下的拳谱:“孤掌投林”的一招一式,那是晨练的新拳法。
“咔咔咔咔。”讲桌的敲响声,是要念分数了。李非从林子里抬头聆听,姓名过往,等了好久,不及格三人之中,仍有自己,“李非,五十分。”黑板擦儿敲击课桌的声响,并非夏雨敲窗晚睡早起的习舞者,不止一次听到炸裂的声音,敲碎死一样的瞌睡。不知身在何处,不晓初春夏浓。阵雨过后,运粮河水浑浊南流。
高中考场离开了运粮河畔,静静的零散在课桌上的一支笔,有时候会敲响,引来监考人过来指点桌面,像警戒的敲门声。直到电铃声在校园里响起,老师“起立”令中,桌凳一片喧哗,少男少女们影子一样晃动而出。忘了是几场考试,全部结束之际,整个考点的校园,偌大的操场上,球篮对球篮,阳光下暴晒,场地外的青草,正在狂长,一排高大的杨树,万千的叶片披着一层眯眼的光亮。二楼望去,一片迷茫。
拜把子的同学们都到了哪里?
去年秋阳高照的河坡上,黄草茂茂,别无人迹,周末的三个同学,在互诉班里的恶人。下午自习课,关上门之后,命令新转来的一个高大学生,趴在教室《学习园地》的黑板上,让李非皮带抽打他,李非怒目不从,那恶人掂着皮带过来,李非临桌两个同学一起站起来怒视。“放学小心着你!”那恶人一皮带抽在黑红色的后门上。全班男女同学,把头埋在课桌里,充耳不闻,习以为常,并不惊讶那敲门声。
放学后,在涌涌出门的人群中,没有李非和同学。付西城看到那个人领着四五个社会上的青少年,抽着烟在校门口张望。恶人走来走去的说笑让烟。便劝慰三人一块儿去学校后院躲避,卧在河坡上切齿愤慨,茂茂黄草,人迹罕至,三人插枯槁为香,小刀割血为誓,拜为兄弟。
如今,二楼下的一派迷茫之中,高大杨木的林荫下,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影。把兄弟都去了哪里?李非仿佛一下子清醒,初中毕业,所有的同学现已离散,再无玩伴,听到谁的敲门声,梦中惊醒。谁来了?他半夜听到。门外是什么?是谁在敲门?是谁在叩问命运?谁又敲了一下。李非打开三楼那令人疑惑的房门,漆黑的楼道上静寂无声,无凤翅之音,似有凉蛇蛰伏。

秋叶的玉米林风声,无星无月的四野大道,渺无人迹,路转之处,便可见远处一盏浅白的银灯,似曾相识,却不曾忘记,那年落考而无高中可上的李非,父亲温馨安排他到东坡后裔故里苏桥,当年叫许县五高就续。一年之后,母亲的同事相助,离开那周日夜来上学的银灯,回到城区。难怪在三高对面的月亮河畔等候,曾经的初中的运粮河畔徘徊,处暑节令的流风,终于传来入学的消息,高一《7》班是临时组建的班级,收拢了一批干部子弟教师子弟,班主任夏老师,河大历史系毕业,文革中一派系头子的身份,曾造反学校大闹省委政府,总理接见,握手主席,没有这样的本事,难控这样的奢豪男女。
最为欣喜的是贺鹏,早已经知道好友在此上学,可以同行同居,不误晨练夜打,他们成为许县第一批散打班成员,两人是最为年轻的对子,十五六岁,总是打得鼻青脸肿,蒙月兰以为打架斗殴,几经询问,才放心吃饭。一切的念想和窗口的那巨大梧桐,枝桠伸展,到对面贺鹏的楼居。
青春明晰,平原辽阔,大道分明。
“载我们的船就要到来,无论是捷足先登,还是柳岸徘徊,你们不必答复,我已追赶上来。不管是蛇一般的寂静之中,是否有生的悲哀,哪怕出发,正如归来。”李非在年级段话上的发言不感慨。
而同时发言的中段考试成绩第一的是《2》班的代表,是其班长付西城,体育和学绩之冠的两个代表,岁月重逢,也方知另一个把兄弟,已接班入厂,而那同班的恶人,犯强奸罪入狱。
不知道付班长学习成绩优异,时代的热网与帆篷已经扯满,待假日期去塚蒙李故乡,听夏侯家族,知晓乡邻油库。付西城在神秘的眼眶片后,睁着大眼说你天时地利啊,又有在油库开车的表亲,咋不倒一点石油?何鹏更为兴奋,一拍即合。几月过后,三人第一桶付钱。付西城说我没有参与,不劳不获,吃一顿饭吧。
李非年阶段一百米短跑第二名,一千米长跑第一。喘息的秋阳,对他而言,何来汗水流亮。曾几何时,少年李非围小城一圈,延安路、许南路、文峰路、八一路、五一路,远跑而回。一直到子弟学校,两腿机械,不能停步。即使逢雨着雨具,过春节也不停息。故此实力成名,何此帆满顺势。付班长付西城班长辅助,李非学习成绩速涨,开明的夏老师主持班委竞选,来年春学,李非任高一《7》班副班长。
“我不能迟留,那万物来归的大海,也在召唤,我必须登船”。

“啪”的一嗡,脑海的潮涌中,李非急回头啊,是夏老师,是骑车绕过来,滑过时的一巴掌,也回头怒视着自己。啪的一声,后脑勺极其响亮。“那是谁儿?两个师兄叫嚣着要回击滋事。李非已经看清楚,连忙解释:“我的老师,是看我抽烟了”。说着扔掉了烟蒂。
夏老师在年级段集会上曾经公开表扬《2》班的学习成绩和《7》班的体育成绩,要相互学习,互惠共进,全面发展,个人要自知,要安静,唤醒心中隐秘的涌泉,升溢吟唱,听从那天志的召唤,带着良知一起行走,眼望前方,不能借给他人你理想的翅膀,你要丰羽自翔;灵魂是千瓣的莲花,自洁开放;没有绝对相同的两朵莲花,出淤泥,濯清涟,不染苍于苍,绝染黄于黄。
课上所讲到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盗拓案剑瞋目,怒斥孔丘,天下第一骂:你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有巢氏,带领人民,昼拾橡栗,暮栖木上;神农氏,卧则居居,起则于于,耕食织衣,无有相害之心,后来涿鹿流血;汤放其主,武王杀纣。新的丛林在大小城郭,在脑滩血泽,疯狂生长,以众暴寡,以强凌弱。
又讲大众普罗,那漆黑或灰暗的时代,生存都是困难,存在悉为苦厄。
孔丘?李非翻出厢存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秋叶飘落,孔丘周游列国,宣扬学问,遭遇柳下季之弟盗跖。看那背弓按箭的跖,怒目厉声呵道:你这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坏蛋,诱我入套?办不到;你通行天下之理,为何在齐鲁无立足之地》在陈蔡被围,卫国几丧!你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道,若告我如何人事与生存,你狂狂汲汲,欺世盗名,你滚。
“孔子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正是破车秋叶翻落,一路狂坠,烂衣伏轼,白发斜冠,瘦皮垂眉。正是小儿书中的封面图画,当然作画者的思想,已追溯两千年的历史,以及时代的嘲弄,李非不由闭目神痴,只有恐怖。
生存,生存。搬往新居之后,城乡物质渐丰,收入上涨,蒙兰月购置了一张铁床,蓝底荷花飞鸟,套折叠桌椅,钢化玻璃桌面,褐色的大朵牡丹盛开铺落,权做厨房的阳台,下围垒齐红砖,上则罩上一层塑料,寒霜作风无虞。翌年,那窗台蓝瓦泥盆,不知何来的种子,竟然开出故乡草屋顶上的鲜花,碎碎细细,娇柔艳丽,在春风中跳动摇曳,那五色草。
然则花无百日红,生存苦厄多。曾经帮助贺鹏李非的蒙庄表亲,早已盗油犯事,熟悉事实的蒙月兰,肃然告诫李非,不要再做什么生意。但是高二的那个秋天,有些炫耀的李非,骑到学校的带链盒的自行车被盗,李非贺鹏付西城,找遍了校园的所有角落,真的是丢掉了。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母亲交代呢?三人还有另几个好友,出校门坐在河岸上,茫茫然,故若孔丘。
暮光风来,柳暗水鸣,何鹏轻言计策,不顾城西反对,两人在教师宿舍的筒子楼里面,李非望风,贺鹏动刀,何鹏推出来,李非故作镇定,安稳地骑上,缓缓地驰出学校门卫的眼界,狂奔到家。众人围着已拖到三楼的崭新自行车,惶惶然叹息,羡慕般崇敬贺鹏的义举。
“时代的热望与篷帆已经扯满,我不能滞留,我必须登船;那万物来归的大海已在召唤,必须登船。”这是什么样的出发呢?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