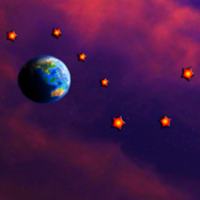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连载之一】七层道塔:萌一
文丨曹旭

该搬家了,从飘摇小学那低矮的狭小办公室,搬入新居了。
兰贵生部队结婚在凛冽的北方,在崭新绿色军服和红领章红五星的辉映下,在战友们的欢笑和北中国北雪房的银世界,贵生兰结婚了。短暂的一瞬间,蜜月过后,当年贫无居的蒙月兰,已从遥远的夏庄中学以婚嫁到李庄之故,调来李庄小学,借和同事一块儿的办公室暂居,白天办公,晚时歇息。
北方军营里,皑皑残雪野,奔跑过来的喜悦与消息,喘息说你的请示批下来了,指导员让你过去。雪国将别,军营中的行行白杨,满树的枝桠凌乱,李贵生舍去卫生员和宣传员的前途,提前退伍。为了兰贵生,为了盖新房,为了早点拿出退伍费,在七奶奶的筹措下。一家人聚心合力,盖起了一排五间半的草屋,几兄弟分别居住,而贵生兰出力为最,况且是公家的人,分到一间半的优渥所居。
那新鲜的土墙味道,那麦秸和泥的屋顶气息,那搬回来的门板简床,绿色的军被和棉衣,甜甜已归的安榻。还有蒙庄正在敲打的家具,那是蒙月兰的嫁妆呢,尽管迟来一年的期许。
仓促的没有细致打磨的一张枣红色矮桌,一台枣红色的五斗桌,一口枣红色的箱子,最为奢华的是那台有床头的卧榻了,高大的枣红色的大床,也许两年时光。贵生兰搬来小凳子,一点点,一分分,引导小斐斐如何攀登上无比宽敞的大床,尽管夜里惊醒,哭着寻找那比天地方还要宽广的母亲怀抱。
父母住在一间半的里间,当母亲在昏暗的灯下学习或批改作业的时候,婓斐会在半间里屋的床上,以棉被为凳,却打不开泥墙上的小窗,还要母亲站起身来,也爬到床上,为他开启自由光亮而尚未布满星辰的夜空。
随着弟弟的出生,小斐斐常要寄养在外祖母的家里。外祖母暖暖的麦秸为垫,老蓝色薄褥子为铺的夜晚,在她几乎咒语般的呵护声中,不知何岁何时的溘然深眠;仿佛听到千万年之前那遥遥迢迢的歌谣:人民少兮禽兽众,人民少兮禽兽凶;构木为巢兮避群害,有巢氏兮民悦之;构木为巢兮民悦之,构木为巢兮民悦之。
外祖父总是沉默不语的,报纸可以裁成一叠的小纸条,放了土黄色的烟丝细细的卷了。呲的一声火柴红焰,映照着他的脸点烟,在木条窗微微的亮中,那蓝灰色的烟雾吹来而渐渐消散。那裁烟纸裹烟卷的双手,是打制枣红色床的双手,是摘来西红柿的双手。
从生产队长退下专看菜地的棚屋处,他种植的丝瓜已铺满天空,矮床上的小斐斐,在沉睡之间,被午后的阳光摇醒,是外祖父摘来的泛光的西红柿,是清凉而沙瓤的红色果实;清凉的浇灌菜畦的清水,从泉台灵台而来,在浅浅的泥沟里缓流,洁净可掬。
蒙蒙水,夏荫凉凉,有蝉远鸣;蒙蒙水,夏阴凉凉,有蜩传声。李之榻,轩开星空,有亲笑容;李之榻,轩开星空,云何来风,云何来风。小小的孩子,想妈了。

在幽暗而温暖的宫室内,那红色的花蕾流落了。春天不胜伤悲,到万叶凋碧的秋风,几乎是遭遇浸漫的寒冬,那记忆岁岁盛开,那沉痛从不凋零。母子知道,三月的碎花开放在草屋之顶。
尚有万年穴居,遗痕的一排草屋,从西山神怪一指,运回那獠牙参差的红色坚石为基,土坯垒墙,架木铺箔,百里红色的高粱秸秆绩织,麦秸麻渣泥为顶。待到春阳来照,霖雨一场,昫昫和风晚醒,那屋顶泥土里无数的生命,无数的种子在三月,盛开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碎碎花,在清风中轻盈颤动。蒙月兰回顾儿子手指所向,那远远的屋顶,并不晓那不起眼的花草之称,便说那是五色草吧。
高大槐树的烂漫花串,谁不知其名呢?七奶奶说榆树的皮都吃过,春天的槐花是美味的。茫茫古原万丈,庄庄村落染染,榆树、槐树、柳树、梧桐,最为盛行。一旦柳叶嫩生,便有人采摘,况且满树的榆钱、槐花、紫色桐花,是一道道春天的美食。
蒙月兰高举捆绑在长杆上的镰刀,一镰一镰地割下那白色的花枝,一边想到七奶奶讲过的故事,行动不便的七奶奶坐在那里,教授如何制作玉米槐花饼,不觉神志迷糊。“七月半,鬼乱窜”,讲飞亷怪兽,白虎煞星。待到七月十五,忌出房门,讳望夜空,那晚若见凶星,必遭疾病,家庭不睦,云云。
斐斐一边捡拾槐花在荆篮里,一边喊妈妈好香啊。蒙月兰答应着,可能是一只什么风尘落在眼里,清泪淌流。什么迷信,真的是去年中元节的深夜,在外乘凉,遥望星空,路过坟头。
一张高粱皮竹席,蒙月兰领着孩子乘凉,讲嫦娥奔月的传说,小斐斐仰望着夜空,指着略有浮云缭绕的圆月,喃喃自语,真的有小白兔呢。那青蛙在哪里?为啥又叫蟾蜍呢?不就是癞蛤蟆?还是那只水青蛙好看哦,是七奶奶的那尊蛙形磁盂。
银河找不到,团团有哪条呢?牛郎星是哪一颗?织女星是哪一颗?鹊桥在哪里?牛郎挑的孩子真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吗?妈妈你能给我生一个小妹妹吗?蒙月兰欣然说会的儿子,妈要给你生个小妹妹。
夏季的丝瓜,在外祖父的菜地里,在棚屋外的竹木架子上,欢喜的生长,丝丝交织的线茎,一叶一叶的攀援,伸展开去,白色的短绒毛,一天一样地攀升。像谁的童年。如是一路向上,欣然在途中孕育花蕊,开出黄色的辐射状的花朵,结出一寸三寸近一尺的长条果实。
蒙月兰没有如儿子所愿,思忖盼望着自己的腹部,又是一朵女儿的花胎,正在温暖的宫室里孕育,已成花蕾,领着孩子在村外迎候下班归来的丈夫。
李贵生急迫回家,超近路,走坟岗小径,其时暮色已苍茫。后来,蒙月兰的第三个孩子,在劝诱下从血色黑暗的宫室里坠落。兰桂生已有两个孩子,蒙月兰想要个女儿,那花儿尚未开放,便已凋谢。
月出皎兮,遥怜小儿女;花房暖兮,遥怜我儿女。
月出皓兮,忉忉人不语;花室寒兮,忉忉人无语。

从雨后浅浅的草檐滴水沟里,那只蚂蚁爬了出来,在无际的黑暗宇宙里,一只圆形的球体,从远处㣪缓却是疾然滚动而来,巨硕之巨,几乎遮蔽了眼界,而那黑色的蚂蚁渐渐长大。长长长长长,大过星球,爬上去,张开獠牙啃食它。那星球像颓废的一团泥土,一块一块的陨落。
巨大的槐树上,那只赳赳雄鸡,从树枝上飞翔而来,从树枝上展开五彩斑斓的羽翼,张开巨喙啄击啃食。不料又有一只更为巨大的黑色蚂蚁,蜘蛛胸腹,其翼若垂天黑云,翱翔而下,瞪珠目,切黑齿,背袭雄鸡凤凰之红冠。
“哇”的一声,在里屋的蒙月兰,听到斐斐在外屋惨叫,挑起门帘,见儿子从红床上滚落在地,正放声大哭,连忙抱起来,呵护好久,方把斐斐从噩梦中唤醒。摸摸滚烫的额头,一面怪声喊来隔壁的四弟,抱起孩子,踏子夜,过坟岗,到学校,敲开卫生所的门扉,打针退烧。
三岁左右的孩子,夜里高烧,应该是常态,据说是生长期,必要经过的奈何桥。如若七奶奶仍在,也必然会做法,手托蛙㿻蘸水,绕着草屋转悠,像舞蹈,念叨着“乖乖你回来吧,乖乖你回来吧。”云云。的确,谁冥冥中保佑斐斐的,高烧一针即退,通红的脸已经平静,在母亲的怀里渐渐入睡。下夜班回来的父亲说,没事儿没事儿,多喝开水,酵母片要多吃。酱色的大瓶营养片,就在书桌那只红色闹钟的旁边。
来年春,四五岁的斐斐,可以撒欢玩耍了,可以跟爸爸到城里所在工厂的医疗室了,和同龄的几个孩子在砖堆里修碉堡,在沙丘上挖地道。却不料在攀爬闪着晶光的粗大砂砾堆中时,扎破了脚拇指,以为无妨,却又沾了污水,不久肿胀如小红萝卜。兰贵生又吵闹了一场。父亲有些内疚,带着斐斐到厂里和几个同事一块手术,那肿胀处切开一股毒液,若龙之焰喷射而出,溅满父亲的额头。
该年夏,古老的平原,暴雨不止,许县的人们,并不知道五十里外的石漫滩水库的水位,急剧升高,终于崩溃。雨灾过后,连连晴日,塚蒙李风平水静,七奶奶家的独室草屋,四叔悠闲的吹一只竹笛:“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旋律并不优美,断断续续的呼吸。忽然,听到屋外有大异响。一坑幼世在翻腾,激起生命浊浪。
是小斐斐落水了,一大家的粪坑,就在小院的大门前,为雨后进出方便,四叔弄来车架。搭坑上为桥,斐斐好奇为乐,一人在桥上走来走,去看看浑浊的满坑一水,漂浮着碎碎的几杆麦秸,无鱼无青蛙什么的,看看天空,无片云彩,只有阳光有些毒辣照的晃眼,脚下摇晃,从桥上落水了。
蒙月兰从学校里跑回来,看四弟端着那蛙㿻,并不蘸水,只是绕圈:“斐斐回来吧,回来吧,斐斐回来吧,回来吧。”等等招魂。她鼓气不及惊恐,嚷着冲回家里,见睡在丈夫怀里的斐斐,流下泪来。
那晚,斐斐的红窗外,又是一阵撕扯,一把银亮的剪刀,那花红的闹钟,从里屋里飞将而出,冲撞到月白色的门帘,落了下来,声音很小。帘上的和鸣鸾凤,在生长的风中,来回飘摇。

“暗想那织女分,牛郎命,虽不老,是长生。他阻隔银河信幽冥明,经年度岁成孤零”。这是当年秋天,中原遥寄军营里的相思吗?“月澄澄银汉无声。说尽千秋万古情。”当年贵生兰的爱情,春月啼鹃,秋晚残蝉,不知何时何处,竟惹得一缕哀思,无端恨怨。
那年蒙月兰怀孕小产,思想女儿流落,已经生怨。李贵生又是恋爱时甜言蜜语,翻来当年两人书信来往,情意浓时,铺设一条未来的康庄大道;已在争吵愤慨中,摔碎了那孟蛙,磁片,大呼什么图腾多子?蛙已是广寒宫里的蟾蜍了,封建迷信,浅井之蛙。如此如彼,恩威并施,哄骗蒙月兰做了绝育手术,植下仇怨。
从旧草屋搬往新宅,暂缓了兰贵生之间的矛盾。毕竟是工厂医生、代课老师,均有工资。是塚蒙李最早一批盖起瓦房的物阜人。起初,蒙月兰倾心育儿,烧茶做饭;李贵生下班之后,无论昼夜从西坡取土,一车车填补新房前的那口大坑。斐斐倾倒垃圾入内,看着成块的煤渣在土坡上一天天的滚下,甚为喜悦。待到院落齐整,植上高高的梧桐苗,父亲从村西南的那口井里,一挑挑担来清水,浇灌河护,精心培育。
那些年月,斐斐和弟弟眯着眼睛,望着越长越高的桐叶,父亲一扎一扎的测量,听到他在春末喃喃自语:“已经两扎了,又听到中秋时轻微地念叨,四扎了。”树干仿佛一天天粗壮,满院的梧桐可以成荫了,斐斐的小学快毕业了,而时间几乎停滞的和平记忆,不知何时开始雕刻?
深夜里常常听到新房东屋的吵闹和哭泣,甚至那夜兄弟惊醒,是父亲冲过来,对着枣色大床上的母子三人大声怒吼:“你去死吧。”那阴暗的门框里,一个高大的黑影,扔下一摞东西,盘绕着纠缠着是一条蛇形的绳索,还有那把银色的剪刀,在闯入的月光中闪烁,母子莫不恐惧。
母亲不知何时离家了,也许是那天地火续进不够,生了鏊子上的洛馍,又或者洛馍老黑了,起了黑色的磨泡,母亲的小杆杖敲打生长的头颅,或者是那晚矛盾升级,父亲从屋里追赶出来,从后面撕破了母亲的内衣,或者邻居相劝,家族大哥跑过来怒斥着响亮的一掌扇过去,又或者四叔闻讯,从老宅里过来和兄长理论,一个耳光从家族的夏夜里扇了过来?
那个暑假的一天,那个傍晚,雨下个不停,兄弟俩在瓦屋的雨搭下,寻觅村前铁路上那熟悉不过的身影,会从城里滑动着回来的父亲,却只能看到灰色的雨雾,听到哗哗的水声。四叔端来的煮红薯已经吃尽,收遍厨房的锅碗粮柜,只有清水,还有那绿荫中流落的夏雨。
天越发黑暗暴雨如注时,已经模糊了兄弟的视线,凉意浓了,寒冷浸染,斐斐哄劝着哭泣的弟弟,不觉之中,抱着弟弟,也流下泪来。忽然一个炸雷,从西天爆响,一个闪电,在南天撕裂,从那暴雨中冲来两人,一个推着踏车,一个撑着断了手柄的雨伞。湿淋淋狼狈而还的,是爸爸妈妈,是兰贵生是贵生兰。
那期间,雨阵阵梧桐打,叶叶凋;斯午后,一点点滴谁愁,枝叶瘦。念一身七患,天志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雨湿寒峭,霜染幼草,不肯相饶。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