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学观点与西晋一脉相承,除玄言诗一支之外,其他诗歌同样是丽藻繁富;好生厚生、乐生畏死的思想在东晋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精神世界的成长促使游仙诗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在现实世界的追求则催生了山水田园诗。
绮靡诗歌中对女儿之思的关注在六朝时即发展为单纯地对妇女容色的审美,绮靡诗歌中注重对外表服饰刻画、好用修辞的特点也在宫体诗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一、绮靡诗风的形成被钟嵘称为“文章中兴”,刘勰说其“人才实盛”,西晋绮靡诗风的代表是太康诗风,它既不同于建安的风骨劲遒,也有异于东晋的谈玄论理,它的形成,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文学地位的提升与文人的浮竞逞才
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诗赋风行的两汉,文学虽然成果硕硕,地位却不甚高,或是儒家教化的工具,或是消遣哗众的玩物。迄于魏晋,文学的地位却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人们将文学赋予了“立名不朽”的重任。这大大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逞才、文人弄辞也便成为风尚。

1.寄身翰墨,声名自传
著书立说而身名不朽,这一观点并非魏晋时期的首创。司马迁即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而这毕竟只是在志向不得施展时的无奈之举。
张华的例子为寒素文人指出了一条即能成就个人功业,用世理想道路的实现:自汉末以来博学勤著学风的主要承继者是西晋寒素文人,也是因为他们的寒素身份,佼佼者如魏舒、山涛、石鉴,傅玄与张华尤为杰出,又傅张二人往往言传身教,以自身的成功作为后进者的典范,是以士子如水趋下。

2.开国美诵,文人逞才
汉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纷争结束于三国归晋,归晋朝的四方俊杰悉,一时间“龙飞何蜿蜿,凤翔何翙翙”,“神化感无方,髦才盈帝畿”(傅玄鼓吹曲《玄云》)。人才的集聚,国家的一统,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这一切都成为太康诗坛的繁荣的沃土。
总而言之,文学地位在魏晋的提升,让诗歌成为了文人立名进仕的媒介。在张华等由寒素而腾达的前辈的影响下,又加上与嗜美世风相适的唯美目的,西晋诗歌走上了一条注重形式美的道路。

(二)、楚辞余韵的承继与建安诗风的延展
西晋诗歌虽然外表柔弱,但与“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继承也有所偏重,最终形成了一种变体。不仅如此,西晋绮靡诗风的形成根源,可以追溯到“楚辞”。

1.屈骚绝艳,晋士多情
西晋绮靡诗风与“楚辞”有显而易见的继承关系。两汉时期对屈原作品评价甚高,但多是关注屈原的个人遭遇和高尚品格,一些模拟之作也只是通过感叹屈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不遇于时的悲哀,他们的眼光都只是放在屈原的思想感情及个人经历之上。
但魏晋以后的文人却对屈原作品的形式更感兴趣,更关注“楚辞”的艺术手法,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的阅读和接受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钟嵘《诗品》中将“楚辞”标为诗歌的一大源头,其中的“楚辞”源流诗人有二十二家,其中潘岳、张协、张华、刘琨皆是西晋重要诗人,可见魏晋南北朝人对师法“楚辞”的重视与肯定。
西晋时期,“楚辞”对诗歌的影响主要在悲情的抒发和词采的华艳上。这二者也恰是西晋诗风的特点。

2.诗赋欲丽,得肤忘骨
建安诗歌向来以骨力著称,西晋绮靡诗风的柔软绮丽似乎完全与之相反。然而二者之间仅仅经过了十几年的正始玄风,建安诗歌的影响可能消失尽净吗?我们之所以常常将建安诗风与西晋诗风对立起来,只是因为在分析建安诗歌时,过多的注意到“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作风,却忽视了建安诗风的形式美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要注意的是,建安诗风的尚丽与西晋绮靡诗风并不完全一致,它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西晋诗人继承了曹植等邺下诗人以文被质的风格,学邺下诗歌仅得语言修饰,品悲凉之情而为悲伤哀怨,将二者片面发展,大量才情放在“华丽”的审美特征上,最终形成了西晋诗歌绮靡的风格。
 二、绮靡诗风对东晋诗歌及南朝宫体诗的影响
二、绮靡诗风对东晋诗歌及南朝宫体诗的影响正始玄风之后,半个世纪的西晋诗坛绮靡诗风确是主流。虽然西晋未年已经崇尚玄理,不注重情辞而只在理趣,尤其是东晋诗坛“赏意忘言”已经取代了“缘情绮靡”,但绮靡诗风的余脉,对后世诗歌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对东晋诗歌的影响
东晋初年,士人或无力南渡,或卒于乱世,致使诗坛一时沉寂。“永嘉南渡以来直到东晋玄言诗兴盛前的诗歌,用断层化来称述,当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绮靡之音与“平淡之体”的交替时期。永嘉之后的东晋诗风貌似与绮靡格格不入,但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名士过江,风流未沫
永嘉乱起,北方士族纷纷南渡。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虽然如此,绮靡诗风对东晋诗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东晋前期,桓、庾诸公等中兴名士与依附他们的一些文士,仍然沿袭西晋雅诗风气,但玄言因素也在渐渐增多。温诗虽仅存两句,但我们从郭璞、梅陶给温峤的赠诗中可以想见,温峤也是很乐于创作这类雅诗的,必有答赠之作。
而郭、梅这样地位较低的文士创作雅诗,也正反应了当时诗风的趋尚。东晋士人仍然继承了西晋风流。

2.丽藻繁富,情韵幽深
东晋诗人亦多繁辞丽藻,东晋诗坛绝不仅仅是玄言诗的平淡。东晋初期,干宝、李充、虞预等都曾著文反对浮华虚诞之风,但人们对华辞丽藻的喜爱并未减褪,而且东晋前期一些地位较低的文士,沿着西晋感物缘情、兼尚意理的创作原则,在五言诗上作了一些实绩,这也可看作是绮靡诗风的余衍。
只不过在中期以后,由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理和山水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玄言诗被推为诗坛的主流。

东晋诗歌同样有情韵幽深之作,虽不绮靡却也缘情。玄言诗即是过于追求情韵的幽深而显得玄妙高深。东晋诗歌并非单纯的“道貌岸然”、平典无味,也有不少表现儿女情浓的作品。
杨方也有代表诗作《合欢诗》五首,此选其一:诗中山盟海誓,既有文采,亦显情深,大量运用比喻,加之一连串动人物象,与西晋儿女之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3.神游仙界,心归田园
诗入东晋,面对外族入侵、离乡弃国的际遇,又加一层伤逝之感。但偏安心态让东晋士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发生了变化,“新亭对泣”已成为历史,人们更多的是保持着魏晋时期厚生忧死的心态。
既然厚生,则更注重生活的安适、情趣的高雅。这也体现在士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上:一是清谈,二是养生,三是游山玩水,四是钟情于诗乐书画。这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游仙诗的创作和山水田园诗的形成。

田园生活非是一般诗人能有的体验,因此,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在当时并不突出,只有后世才认识到其价值。总之,西晋绮靡诗风,对陶渊明、谢灵运这样山水田园诗人的产生,对于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作用不容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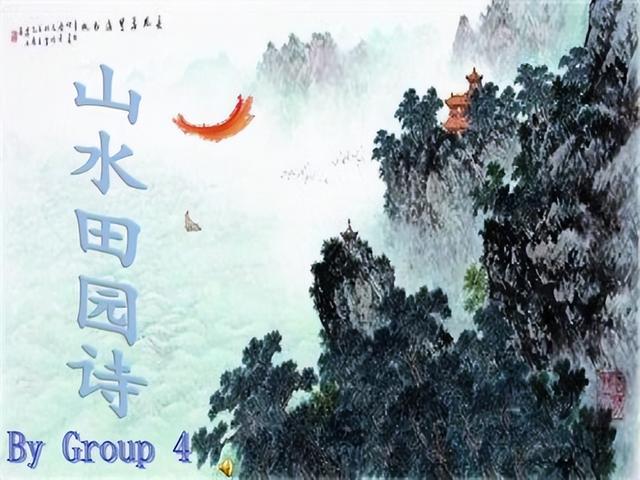
(二)、对南朝宫体诗的影响
西晋绮靡之风的绵软多情,经过了东晋玄言诗的冲刷,山水田园诗的滤化,非但没有减弱,到了南朝,甚至有发扬光大的现象。终其原因,是诗歌已经走进了自觉的审美时代,凡是世人眼中所看到的美、心中所感受的美都成为了诗歌吟唱的对象,不再是一味讲求仁义伦理、玄言精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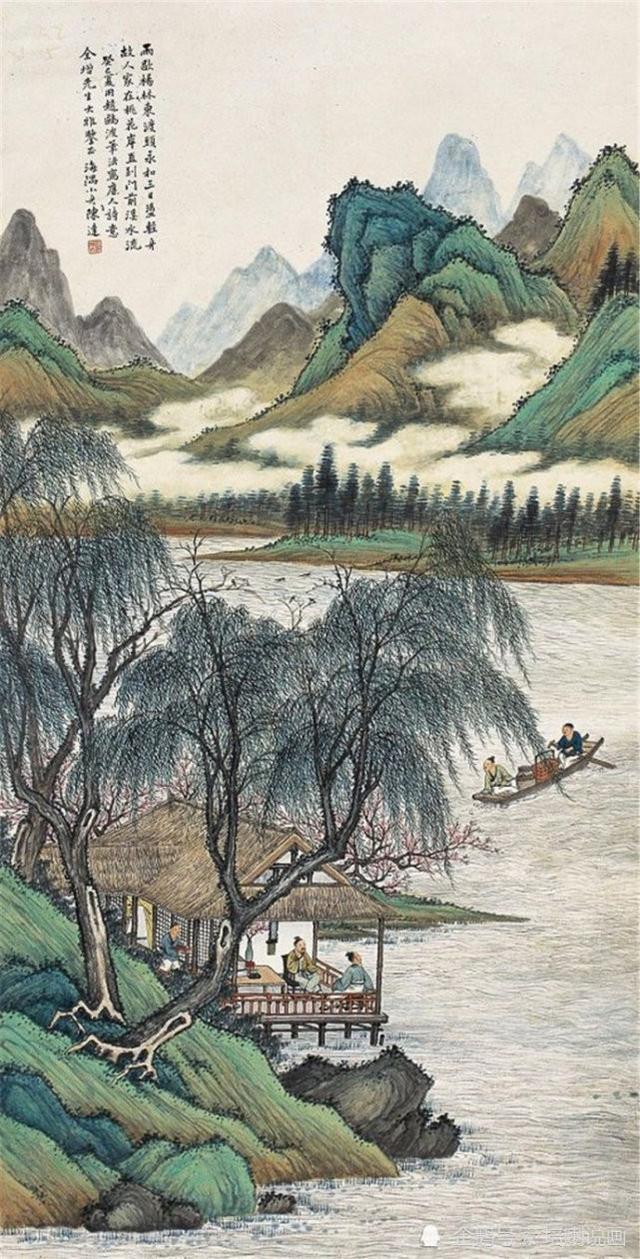
1.容色之美,妇人之姿
宫体诗是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与徐、庾等人在东宫相互唱和,创作的一些思极闺房、辞藻靡丽的作品。西晋时期,中国诗歌真正成就了“美的文学”,社会上的审美风潮也带动了文学的审美风潮。于是纯粹以美貌、美服、美器、美物为歌咏对象的宫体诗产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宫体诗毕竟是文人诗作,文人的学养和高雅对其写美色的“度”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诗中并没有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对性爱的体现也是极隐晦而具有艺术性的,因此,宫体诗并不能与“淫诗”等同。

2.女儿之心,微妙情思
西晋诗人对于闺情怨思的关注颇多,在傅玄、张华等多情诗人的诗歌中更多体现。这一点,也为南朝宫体诗人所继承。西晋诗人关注女性情思,多体现在对妇女命运遭际的同情和品质德操的赞美,如傅玄《苦相篇》、《秦女休行》,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等。

此外,宫体诗人喜好欣赏美女的大量装饰,也能看出西晋士人审美情趣的遗续。宫体诗起源于民间情诗,这与西晋文人诗好言情的原因是一致的。李贽曾评《玉台新咏》所收艳歌“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可谓绮靡之音与宫体诗歌的共同评语。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说,西晋绮靡诗风虽然不是宫体诗歌的直接来源,但至少对宫体诗歌的产生起到过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结语
三、结语西晋绮靡诗风是中国文学史闪亮的一环。它将文学的审美追求大胆付诸实施,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是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的文学发展趋势必然。正谓“善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总之,西晋绮靡诗风所追求的情辞的细腻优美是顺应文学发展规律的,是文学自觉意识的鲜明体现。西晋诗歌所追求的纯粹艺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诗之气、词之秀皆可从绮靡之中追寻根源。西晋绮靡诗风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笔重要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