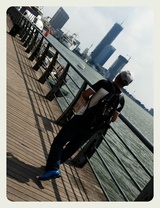车轮碾过无人区的砾石,发出细碎的呻吟。阿里45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得像是被神祇刻意稀释过的琼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刀割般的钝痛。从改则县到尼 玛县的路途上,车辙在荒原上蜿蜒成一道伤痕,远处的地平线被风沙揉皱,几座低矮的土窑突兀地矗立在视线尽头,像被时间遗忘的古老图腾。


土窑的轮廓在烈日下颤抖。一位老妇人佝偻着脊背立于门前,身上原本色彩艳丽的藏袍已褪色,褶皱里嵌满沙尘。她手里握着一只铜质转经筒,筒身斑驳如龟裂的土地,经筒转动的“吱呀”声却异常清亮,仿佛能穿透荒原亘古的寂静。四个孩子蜷缩在她身后,最小的那个吮着手指,脸颊皴裂成高原红,眼神却像雪山上未融的冰湖,澄澈得令人心惊。


当我们走进土窑更是让人震惊,这哪里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居所,可这的的确确就是他们的家。老妇人始终未开口,只是将转经筒贴在胸口或是手举转经筒转动着,面露祥和的笑容,指尖摩挲着刻满经文的筒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在这片连飞鸟都避之不及的荒原,信仰是比氧气更重要的生存介质。


我们没办法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只能给他们留下一些衣物、食品和饮料,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喜悦,在我心里涌动的却只有心酸和心疼。孩子们围住我们留下的矿泉水和食品,像一群发现雪莲的羚羊。最大的女孩用藏袍兜住食物,却将一包糖果悄悄塞回我们手中。她指了指老妇人,又指向远方的雪山,手势笨拙却虔诚——那是献给山神的供奉。我蹲下身,试图用手机播放一段动画,屏幕亮起的瞬间,孩子们惊恐后退,仿佛撞见了某种禁忌的灵物。老妇人却笑了。她布满沟壑的脸庞突然舒展,如同一朵在绝壁上绽放的雪莲。那笑容里没有悲苦,只有一种近乎神性的坦然。


在我们逗留的过程中没有看到一个壮年男女,只有这一老四幼,也许壮年男女都外出去寻找他们生存的需要品去了。但这里的环境并不安全,阿里的无人区常常会有狼和熊出没。因为语言不通,我们无法了解这一老四少的关系,更无从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生存和生活的。看着眼前的这一老四少,我想起城市里那些被玩具和补习班填满的童年,突然意识到:在这里,生存本身即是修行。孩子们吞咽粗粝食物的姿态,与老妇人转动经筒的节奏,构成了荒原上最原始的生命韵律。



离开时,引擎声惊起一群远处的藏野驴。后视镜里,老妇人的身影渐渐缩成荒原上一个颤动的黑点,唯有转经筒的铜光仍在暮色中闪烁,像一颗永不坠落的星。同伴低声问:“你说他们真的相信轮回吗?”我没有回答。当车灯刺破黑暗的瞬间,我仿佛看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面孔,那些与狼群对峙的夜晚,那些用体温融化冰水的清晨——在阿里,信仰不是飘渺的来世契约,而是此生此刻的呼吸方式。



高原的星空倾泻而下,银河如转经筒的经轴般悬于天际。我突然懂得:现代人总将信仰与苦难捆绑,却不知在这片离天堂最近的土地上,信仰是荒原赐予的铠甲。他们向神佛倾尽所有,并非因为恐惧地狱之火,而是要让灵魂与牦牛、风马、格桑花一样,成为荒原永恒史诗中的一个韵脚。当游客带来的可乐瓶和防晒霜逐渐侵蚀这片净土时,老妇人的转经筒依然在转动——那是对抗时间与遗忘最沉默的宣言。


自从阿里回来后,我常常会凝视那张偷拍的土窑照片。像素模糊的影像中,老妇人与孩子们的身影已与荒原的肌理融为一体。某个瞬间,我忽然惊觉:我们携带GPS和氧气罐闯入无人区,自诩为探索者,却不过是浮光掠影的偷窥者;而他们,才是荒原真正的主人。


我一直在参悟,或许,阿里的藏民早已参透生命的奥义:在神山与苍穹的注视下,所有文明的对峙都显得苍白。当我们在城市中为利益得失难以入睡时,他们在暴雪夜围炉诵经;当我们用智能设备测量幸福指数时,他们用掌心温度焐热冰凉的糌粑。这不是落后与先进的较量,而是两种时间维度的对话——一种追逐线性增长,一种在圆形轮回中完成永恒的闭环。
转经筒依然在转。荒原上的每一次日出,都是对守望者的加冕。


感谢诸位朋友莅临狼窝,诚望予以批评指导。欢迎各位留言点评、转发、分享、收藏并关注本号,您的支持乃是老狼创作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