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丽娟教授是一位有造诣、有影响、为笔者所尊敬的红学家。她的《红楼梦》[1]人物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体现在她的《大观红楼》四卷、《红楼梦立体人物论》等系列著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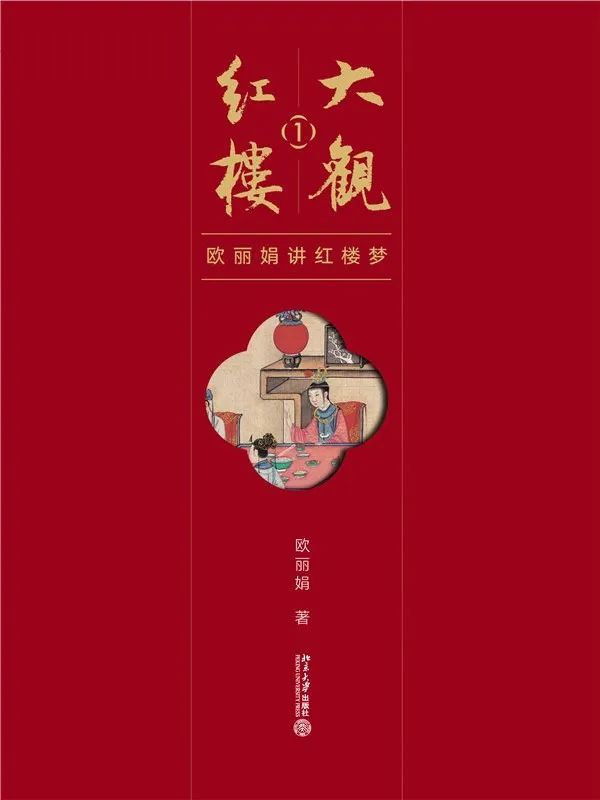
《大观红楼》
她高度肯定《红楼梦》,“在一部作品里竟有这么多的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这实为中外文学史所罕见”(《大观红楼》<4>,002页)[2]她反对把作家创造的圆形人物扁平化解读,并在论著中努力践行,不乏精彩篇章。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她的小说人物论也出现了自己所批评的“既定成见与主观好恶之下的贬抑”,“既有失于伟大作家所理解、所创造的复杂度,错违了小说文本的全面性,也不符合分析批评的客观理性”的问题。(350页)《晴雯论》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晴雯是欧教授很关注的红楼人物。《晴雯论》(以下简称“欧文”)是《大观红楼》(4)中的一篇长篇论文,124页,八万余字。此外,书中其他地方(如论王夫人、袭人等)还有不少涉及晴雯的论述。
欧文一开头,就认定由于“宝玉的主观认知却成为读者的认知主流”,因而“实有必要重新理性地客观分析晴雯这个角色,由此也有助于正确掌握《红楼梦》的人格复杂性与人性价值观。”(225页)。
她认为:“整体而言,晴雯是一个美丽健康、朴直念旧、性急浮躁、火爆易怒、口齿尖刻、争强善妒、骄纵任性的女孩子。”(226页)这话虽有偏颇,尚觉不离“正邪两赋”,然而,越读下去,却越看不到“理性客观”。
相反,从用词酌句,到推理逻辑,都可以感到著者的否定厌恶倾向和深文周纳用意,甚至为了主观好恶屏蔽不利材料。著者已经不但背弃了自己的主张,对作者创造的“圆形人物作扁平化解读”,还进行了有意的贬抑黑化。
这自然引起读者不满,网上已有质疑意见。鉴于晴雯形象的重要性,不可不加辨析。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自己的片段感受,本着“吾更爱真理”的求是精神作一些评论,以与欧教授商榷。

《红楼梦人物立体论》
二
由阅读小说文本引发的黛钗晴袭评价之争,源远流长。在《石头记》稿本时代,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分歧。
尽管曹雪芹明确地把晴雯置于《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但脂批却有“晴卿不及袭卿远矣”,“(袭人)自是又副十二钗中之冠”之语。[3]后一句欧文一再引用,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不过,这也恰好说明,即使是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们也可能“有失于伟大作家所理解所创造的复杂度”,这才有他题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沉重感叹。其实,读者主流对晴雯的认可和同情,并非因为受“贾宝玉的主观认知”的影响,而是“伟大作家所理解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本身感染的结果。
因此,对晴雯的解读,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回归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我们应该对曹雪芹多一份敬畏之心。离开这个认识基点,硬要去“颠覆”、“出新”,或者“回归‘”,都只能归于失败。

戴敦邦绘晴雯
晴雯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女奴艺术形象。不但被设置为“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更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薄命司”展示第一人,表明其在曹雪芹“大旨谈情”和“使闺阁昭传”的整体构思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情”的悲剧和“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女儿悲剧特别是女奴悲剧的核心人物。
晴雯是曹雪芹增删定稿唯一具体描写完成生命过程的艺术形象。她有出众的美丽,出众的人格自尊,直率任性,纯真无邪,寄托着作者的“童心”理想,但也有明显的性格缺点。从判词到诔文,构成一个贯串前八十回的闭环系统,并以“诔晴雯即以诔黛玉”的构思,与宝黛爱情链接。
作者的描写从奴身人格写实到浪漫神格升华,倾注了极为热烈的爱憎情感。晴雯形象具有深广的概括意义。
除了女儿悲剧·和奴婢悲剧,还寄托了作者包衣曹家的被奴役命运和人格追求理想,寄托了作者对美的命运、人才命运和人性善恶的政治历史批判和哲理思考。人们可以对晴雯形象作出自己的解读,但不应背离作家的文本和创作意图,因为晴雯属于曹雪芹。
三

欧丽娟对晴雯的偏见显而易见。同书《香菱论》一开始就指出小说的香菱定位:她是第一位出场的“金钗”,十二钗副册第一人。然而,紧接着的《晴雯论》却没有指出作者给晴雯的更为重要的定位。

连环画《晴雯》
显然欧文很不认同曹雪芹的定位。相反,欧文的结语,还特别强调读者对晴雯的偏爱,“不符合小说家和小说本身的价值定位”,因为“虽然图册的顺序是以晴雯放在首页,后面接着才是袭人,但脂砚斋则认为袭人才是领衔的魁冠。”(344页)
这真是奇怪了,莫非小说家“以晴雯放在首位”的“价值定位”不正确,需要脂砚斋的批语加以纠正?只此一句,就可以看出欧文背弃曹雪芹的论述立场了。
欧文认识到第5回晴雯判词的纲领和预示意义,把解读判词作为论述重点: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嗟念。
然而,他所列出的专节论述,却以“心比天高:特权意识”作标目,显示了其另立章法的曲解用意(259-283页)。
曹雪芹的晴雯判词,首二句即以美丽意象“霁月”“彩云”隐喻晴雯名字内涵(第5回脂批也肯定晴雯“名妙而文”),从而奠定了整首判词的颂扬悲悼基调,使以下数句意义指向清晰明了。”

赵成伟绘晴雯
心比天高“是一个流行俗语,或喻心志高远,或喻心高气傲,在不同语境中呈现不同语义。判词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很明显是通过”心“与”身“的对映肯定晴雯身为奴隶却无奴颜媚骨的风骨人格。[4]
但欧文却有意遮蔽首二句的解释,直取语义可能曲解的“心比天高”,塞进自己的私货,用“特权意识”贬损晴雯。
接着,她用四大段数千字分析胪列,其标目为:(一)虚构的平等思想(260-264页);(二)半主的阶级傲慢(264-274页);(三)准姨娘的自觉(274-278页);(四)不安定因子(278-283页)。最后著者总结道:

判词中所谓的“心比天高”,实质是其主观意识上的“自视甚高”,而非客观价值上的高风亮节,甚至带有目中无人的傲气,无所畏惧的霸气,以致待人处事往往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因而才会发生“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的结果。(283页)
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晴雯的悲剧都由其坏脾气坏意识引起,

必须自负其责,不能归咎于别人。(293页)
这样一来,晴雯形象及其悲剧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由此可见,欧文是处心积虑,把对判词的扭曲解读作为后文贬抑晴雯的纲目。

昆曲《晴雯》戏单
笔者读过一些对晴雯性格弱点进行剖析的文字,但是如此颠覆判词本意,把曹雪芹为晴雯所写的人格赞歌和命运悲歌歪曲为自我罪判,把“他杀”变为“自杀”,也太匪夷所思了。
四

由于欧文冗长,不能对其论据一一分析。仅举数例,以见其观点和方法之谬误。
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作者把晴雯与宝玉的一次(也是书中唯一一次)正面冲突作为晴雯特写的第一笔,突出了晴雯性格和宝晴关系的特点。
事件以“跌扇”引起的晴雯对宝玉的顶撞开始,终以晴雯有意“撕扇”作为对宝玉的回击,宝晴和好结束。
在此之前,第8回的晴雯贴字、宝玉渥手情节,初步展现晴雯任性忠心,宝晴主奴亲密无间的纯净情感,31回的的矛盾爆发有其突然性。

于水绘晴雯
此前一系列事件(金钏儿被逐,端节家宴不欢而散等)宝玉负面情绪的积累,使他不自觉地流露少爷脾气,引起习惯于亲密和睦相处的晴雯的直言顶撞:“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袭人的卷入和不当言辞招致了晴雯的反唇相讥,盛怒的宝玉坚决要撵逐晴雯,矛盾达到高潮。终以袭人及全体丫鬟下跪求情和黛玉的诙谐调笑使事态缓和。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有意气,晴雯的言辞尖刻也是推动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但事件是非还是清晰的。不是晴雯不认错,而是内心积压了对宝玉少爷脾性和对袭人“争荣夸耀”(第31回)及宝袭暧昧关系不满的爆发。晴雯的个性和风骨得到了突出表现。[5]
面对宝玉的盛怒和撵逐威胁,晴雯并不哀求,而是以“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的态度以死相抗。当袭人带怡红院全体丫鬟下跪为晴雯求情时,“晴雯在旁哭着”,却没有下跪。王昆仑评论说:”

晴雯的中心意识是什么?她自始至终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的反抗者的本质——骨气。……晴雯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谄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蔡义江评述说:

晴雯是个直烈性子,有正义感,最少奴颜媚骨。……她是见不得平时像闺友般的宝玉,忽然摆出主子爷儿的架势、脸色来给她看,拿她当奴才训斥、出气,这里包含着某种人格上平等的观念,尽管还是朦胧的。与袭人口角也非出于争宠,而是对她以柔媚式的温顺态度向主子邀宠的不屑和反感。[7]
这些评论都是符合文本实际,精辟到位的。
然而,欧文却指责晴雯对宝玉的顶撞是:
“骄纵成性到一种完全不认错、不受责的程度”,“以自我为中心,在逾越(主奴)分际成为习惯的情况下得寸进尺,终于侵犯到对方的底线,引爆了好好先生的空前震怒。“(244-245页)
很明显,欧文的观点就是肯定宝玉作为贵族主子是无可非议的,而晴雯的问题正是“逾越分际”即破坏了主奴界限。

《宝玉与晴雯》
这样在欧文的贵族礼法观里,是非就颠倒了过来。而晴雯以“撕扇”回击宝玉因“跌扇”口角引发的“震怒”,则更被被解读为“褒姒的叠影”,“褒姒裂绢的同类”,宝玉的纵容取悦有等同于幽王之举,与亡国之君同类,暗示晴雯为“女祸”。(283-287页)
这就很清楚了:欧文“贬抑”晴雯,从根本上说,不是论述方法或角度的错误,而是观念的错误,认识立场的错误。
五

晴雯之死是曹雪芹在小说前八十回怀着极大悲愤最为着力描写的女儿悲剧,奴隶悲剧,人性悲剧和美的悲剧。仅从回目《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第74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第77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78回)就可以看到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
绝大多数读者完全认同曹雪芹及其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爱憎。清代野鹤《读红楼札记》就说:“王夫人撵逐晴姑娘,为《石头记》中第一不平事。”[8]
欧文缺要"为《石头记》中第一不平事”作翻案文章。她为王夫人辩护,说:

既然合情,合理,合法,指控王夫人欺压晴雯就是过分偏颇的成见。(305页)
而王夫人是听信王善保家的谗言才抄检大观园的,于是,欧文就进一步为“谗言”洗白,并且煞费苦心地反复为奸邪小人辩护: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晴雯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脾气,而不是那些小人。王善保家的固然借机谗害,但却没有一句话是扭曲事实的栽赃诬陷。(256页)
王善保家的这段话,目的虽然是谗害晴雯,但却句句属实,没有扭曲捏造。(292页)
撵逐晴雯的导火线是晴雯一手自己造成的,王善保家的虽然趁机加以利用,却并没有捏造事实诬赖她。(300页)
王善保家的固然有意陷害晴雯,但所言却是句句属实,并非构陷罗织,栽赃诬赖,与全书中晴雯的人格表现全然吻合。(303页)
凡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痛恨王善保家的恶毒谗害和为虎作伥,也无不会感受到作者对这类小人的切齿痛恨。

《晴雯之死》戏单
在描写抄检时,作者通过在其外孙女司棋箱中搜出信件等令王善保家的自打嘴巴,给以无情嘲弄鞭挞。更在《芙蓉诔》中以“毁诐奴之口,忿犹未释;剖悍妇之心,讨岂从宽”等语句愤怒声讨。
欧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这种小人开脱。王善保家的是怎样进谗晴雯的,作品有具体描写:

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
作者之所以把这段话定位为“奸谗”,就在于其阴险中伤。所谓“打扮像西施”,所谓“骚眼睛”,所谓“妖妖趫趫”,都是为了“妖化”晴雯,指斥她是品行不端,勾引男人的“妖精”、“祸胎”。
“西施”一词及其形象,在正常健康的审美观里,是绝世美人的符号,其历史传说甚至令人同情。第3回宝玉眼中黛玉“病如西子弱三分”,第64回黛玉《五美吟》首咏“西施”,“一代倾城逐浪花”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在贵族贾府的男权文化语境里,“西施”却是勾引男性的“红颜祸水”符号。王善保家的正是摸准了王夫人的“体统”观谗害晴雯。果然,后来王夫人见了晴雯就骂:“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做这轻狂样儿给谁看?”
欧文一再辩称王善保家的“句句属实”,难道糊涂到连这种恶毒中伤之语都看不出?什么是“骚眼睛”?什么是“妖妖趫趫”?能够从曹雪芹的笔下找出一句“属实”的描写吗?

刘旦宅绘晴雯补裘
人性善恶并不以地位高低区别。王善保家的进谗只是代表,第77回描写,还有老婆子骂晴雯为“祸害妖精“,借机进谗的还有”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者,恶意造谣中伤是他们共同的舆论武器。他们不是针对晴雯的性格脾气缺点,而是在那个时代礼教对女性的“体统”要求上,通过“妖化”“祸水化”给予致命一击。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卑劣的人性恶使他们成为权势者的帮凶,一起结成邪恶之网。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抄检之夜,作者精彩地描写了晴雯的无言愤怒和抗争怒火,当袭人带头打开自己的箱子任王善保家的搜检后:

到了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不开了任搜?”袭人等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过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第74回)

连环画《晴雯》
面对虎狼爪牙,病弱女子晴雯倒箱的“豁啷”一声与后面庶女探春打王善保家的耳光“啪”的一声,是反抄检仅有的英勇行为。
但是,这样的壮举,竟被欧氏《晴雯论》完全屏蔽。
在曹雪芹看来,晴雯的被谗害悲剧,也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才悲剧、正直之士的悲剧乃至所有美好事物被摧残的代表,所以,他不但写晴雯抗争和屈死,还让贾宝玉写出血泪交加悲愤至极的《芙蓉女儿诔》为晴雯冤案控诉辨诬,把旌扬逝者德行的传统诔文变成声讨邪恶势力的檄文:

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疾。故尔樱唇红褪,韵吐呻吟;杏脸香枯,色陈顄頷。诼谣謑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牖。岂招尤则替,实攘垢而终。既忳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
从这个角度看,为王善保家的进谗辩护,实际上也就是在为邪恶辩护,向谴责和反抗邪恶的正义挑战。
其实,以笔者之见,欧文未见得钟情于王善保家的之类奸邪小人,她真正要辩白保护的,是“惑奸谗”的贵族主子王夫人,因为王夫人是她《大观红楼》(2)认定的“母神崇拜”系列的一位“母神”。

《从曹学到红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六
《红楼梦》是否存在“母神崇拜”以及王夫人是否可列为“母”,或许须另行讨论。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看待晴雯悲剧与王夫人的关系。
抄检大观园,撵逐晴雯及一批丫头,从本质上说,是由于绣春囊事件引发贾府加强礼法统治对大观园自由生活和个性理想的整肃,园内外各种矛盾推波助澜,邪恶观念和利益冲突交织其中,但强权与弱势、礼教与个性、害人与被害,在家国一体的专制语境里,其正邪善恶对立的是非界限是很清晰的。

邮票《晴雯撕扇》
不能因为弱者的缺陷过失而否定强者的罪恶邪行。谁能指责李白的狂放导致奸佞进谗;苏轼的讥讽导致乌台诗案?谁能指责刘兰芝的举止导致焦母逼休,陆游唐琬的恩爱导致分钗遗恨?然而,在欧文中人们却看到了是非颠倒:
按照欧文的逻辑,晴雯是因其性格脾气不好而自取其咎。而王夫人不过是履行其管家责任。

王夫人之所以对晴雯大为不满,关键在于晴雯的骄傲、娇纵已经到了非比寻常的程度。(292页)
晴雯之所以被撵逐出府,失去了享福的机会,主要原因就是侵犯了王夫人的底线。……仔细说来,包括过分的装扮(“趫装艳饰”)与轻狂的言行(“语薄言轻”),尤其是涉及男女之间的情色挑逗,构成了王夫人“平生最恨”“一生最嫌”的两道防线,而晴雯两者皆犯,于是注定了不可挽回的下场。“(290页)
欧文完全以王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王夫人的是非观不仅因为全盘接受了王善保家的“奸谗”,更来自其保守的礼教观念。
其实,晴雯究竟怎样“趫装艳饰”,除了王善保家的中伤,书中无一处正面或侧面描写,连王夫人偶然撞见时的第一印象也不过是“削肩膀、水蛇腰”、眉眼像林黛玉,丝毫没有“趫装艳饰”的感觉,这说明即使晴雯爱打扮,也并无出格之处。
至于“语薄言轻”,指的是轻佻色诱,与晴雯的言语直率尖刻,也不是一个范畴。相反,她在“涉及男女之间的情色挑逗”这方面的纯净无邪,远强过袭人之流。
这部小说中丫鬟挑逗主子最轻佻的话,莫过于袭人发现宝玉梦遗后,含羞带笑地问:“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有意挑起宝玉的情欲,遂有“初试云雨情”之事(第6回),而袭人却是王夫人最为信任倚靠者。

电视剧《红楼梦》中袁玫饰演袭人
晴雯和宝玉之间,从来没有过轻佻之话和事,晴雯还义正词严地呵斥宝玉“拉拉扯扯作什么”,拒绝宝玉一起洗澡的要求。(第31回)何以冲撞了王夫人的“底线”?
说明白一点,王夫人“最嫌趫装艳饰语薄言轻者”,就是指女性卖弄风骚勾引男性,这也许包含妻妾关系中对赵姨娘之类女性的反感,也与她神经质的“护子”心态有关。
撵逐金钏时,她骂:“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第30回)搜检怡红院时,她说:“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第77回)
所以,王善保家的之类进谗晴雯,只要用“西施”“骚”“妖趫”之类词语往这个方向引,就能击中王夫人的敏感点,让她欣然接受。于是,晴雯无端受辱,无过被逐,在王夫人心中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客观地看,在贾府贵族中,王夫人不算心狠手辣者。作者含义微妙地评述:“王夫人本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胸臆”,可见她的特点是用权主观任性,不受理性和道德约束。
但欧氏却赞扬“王夫人实践了世家大族的宽厚家风”,因为晴雯死后,赏了十两烧埋银子,“衣履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以贾府的应有权力而言,其实是一种开恩。”(305页)似乎晴雯地下有灵,也应感恩戴德。
欧氏甚至把撵逐说成是“解放奴隶”之举,抱怨读者“反过来对解放奴隶的王夫人施行抨击,展现出以今律古的不公平和双重标准的自我矛盾。”(289页)
是谁既掩盖罪恶又加诬受害者呢?请看被欧氏选择性屏蔽的这一段王夫人逐晴雯的文字:

宝玉及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色,见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才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只许把他贴身衣服撂出去,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第77回)
这哪里有一点慈悲宽厚的影子?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还是“母神”?晴雯的死难道不是这种残害的直接结果吗?欧氏竟然说:“晴雯的死因,合理推测应该是心情郁闷所致,但还很可能包括对贫困生活的严重不适应。”(327页)对晴雯屈死悲剧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说,王夫人撵逐晴雯真正是因为晴雯犯了大过,违反贾府礼法。那么,为什么她在贾母面前又要编造谎言呢?而这一段谎言,又被欧氏选择性屏蔽了: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母剧照

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病不离身,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痨,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78回)
大概这位贾府女管家也觉得加在晴雯身上的“浪”“狂“等罪名难以成立,她那“最嫌趫装艳饰语薄言轻者”的底线难以得到同为正统派的贾母认同,所以要编”女儿痨“欺骗婆婆。说到底,她是心虚了,才会把原来剥夺的晴雯“衣履簪环”发还。
不料,这竟被欧文说成“解放奴隶”的“恩典”。金钏儿之死和晴雯之死是王夫人一手造成的两大悲剧,还有芳官等女伶同样以“狐狸精”的罪名被逐,王夫人心态类似,事件过程类似,都是先盛怒处置,造成悲剧后,心虚不安,用谎言掩饰,用“恩典”弥补。
金钏尚有同宝玉调笑之失,而晴雯与宝玉相处,“各不相扰”。王夫人把重病的晴雯迫害致死,有何“合理合情合法”可言?“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第30回目)“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第77回目),曹雪芹已经把她的罪恶钉在贾府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七
从论述手法看,《晴雯论》最为突出者,除了前面屡次提到的选择性遗漏、遮蔽不利材料外,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
同样一个材料,从不同角度审视,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这是认识的主观性。但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的主观性,就可能并非善意,而是出自恶意。
欧文给晴雯扣了“善妒”的帽子。这个帽子不小,因为“嫉妒”不单是一般的人性之恶,而且是被列为旧时代女性“七出”之条的“恶德”。
《芙蓉诔》云晴雯“高标见嫉”,认为她是人性恶的牺牲品。欧文却说晴雯“善妒”,是有意的颠倒。她把晴雯讥讽红玉、袭人、秋纹、麝月、芳官的不同内容话语,加以主观解读,结论说:

可见其中完全没有任何反抗阶级的意味,反倒充满了同等级之间‘掐尖要强’、不肯屈尊的嫉妒。(262页)
晴雯确实是最善妒、最刻薄的一个,……她那强烈的敌意绝不是出于正义感而全然都是与‘地位高下’有关的情绪性表达。(273页)
嫉妒本是在攀比中对优胜者的负面情感。晴雯讽刺红玉炫耀为“二奶奶取东西”是自以为“爬上高枝儿去了”(第27回),讽刺袭人“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第31回),讽刺秋纹为太太赏赐两件别人挑剩下的衣服而得意(第37回)等等,很明显都是对奴性的鄙视,至于晴雯与麝月、芳官等,更是互相支持,友爱相处。

年画晴雯
欧文中列举了不少具体描写的例子,说明“怡红院大丫鬟之间的温馨的日常互动,有如彼此照顾的姊妹”(309页),“‘宝玉才睡下,晴雯等犹在床边,大家顽笑’,这类情景才是怡红院的主要面貌。”(315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欧文强加晴雯的“善妒”恶名可以休矣。
在怡红院中,晴袭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友善相处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就后一方面说,晴雯对袭人的奴性和心机的不满直率表达;袭人却确实对晴雯的美和宝玉的亲近心存嫉妒。
晴雯被逐后,她对宝玉把晴雯比作海棠花不满,说:“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还说了一句颇带恶意的话:“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第77回)

越剧《宝玉哭晴雯》光盘
欧氏居然以此为依据挖掘晴雯身上的“轻佻”的“不安定因子“。找不到任何实际材料了,欧氏于是从宝晴诀别时晴雯的话里深文罗织:

(晴雯说)“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起。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说毕又哭。
随后,晴雯铰下指甲,脱下贴身绫袄,与宝玉交换,说:
“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里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
人们读到这一段,都会为晴雯受冤屈的悲愤和她的勇敢反抗精神所感动和震撼,而且能明确体会到作者紧接着描写晴雯的嫂子、淫荡的灯姑娘偷听,调戏宝玉并由衷感叹一段的用意:

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两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
曹雪芹为了替晴雯辨诬特地安排一位淫妇作为视事眼睛,手法极为高明,也极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连环画《晴雯》
然而,这一段又被欧文完全屏蔽。却在晴雯身上大挖“不安定因子”。她说,晴雯的话证明晴雯有一种“准姨娘的自觉”(274页)。“晴雯之所以娇惯任性,岂非也带着有恃无恐的潜意识心理?(276页)”“她的性格里其实存在着不稳定的因子,没有勾引宝玉只是没有必要,并非出于‘造次必于是,颠沛比于是’(《论语.里仁》)的真正节操。”(278页)“细思让她悔不当初的‘另有个道理’,便是‘私情密意勾引你。’”(279页) 因为女奴晴雯未达到孔子的要求,于是晴雯与宝玉互换内袄,不是诀别念想,而是“勾引”的行动。连灯姑娘都感动的“委屈”事,被坐实为死前勾引宝玉的罪案。如此深文周纳,罗织罪名,谁能企及!

王叔晖绘《晴雯补裘图》
八
欧文在《晴雯论》的评论失误不是孤立的,它与著者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认识,和所持立场密切相关。
欧丽娟对《红楼梦》有很高评价,不过她是从自己的视角评论的。她重视“《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部真正叙写贵族世家的小说,又是在‘写实逻辑’(非‘写实内容’)下进行书写所反映的阶级特殊性”[9]。
他认定“内三旗”出身的曹雪芹是“没落贵族的落魄王孙”,因而把《红楼梦》写成了“贵族阶级的挽歌”,“《红楼梦》其实是清代贵族世家的阶级反映。”[10]所以,她强调: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回到传统中去理解这部在传统中诞生的作品,并且重新由文本出发,探测到无论是作者曹雪芹或作品《红楼梦》,“清代贵族世家”的习惯、思想、信仰、价值观、心理感受,都是最根本的核心。“封建礼教”则是这一切的先天规定。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都是根植于这样的意识形态而展开。[11]
按照这种观点,书中的人物事件就都需要依据“封建礼教”的“先天规定”重新审视。而评论晴雯“主流意见的形成”,“多数读者多是采个人主义的角度,颂扬为一种高贵的情操以及不屈的反抗精神。”(221页)
所以,她不但排斥“反封建”、“反礼教”观点的解读,也企图“提供与现代个人主义不同的思考”(345页)
这种“回到传统”的结果,并没有为欧氏带来新见,反而使她完全站到了贵族贾府的“封建礼教”一边。

《欧丽娟红楼梦公开课》
她在《大观红楼》(1)用礼教规范解读了宝黛爱情,在《大观红楼》(2)用礼教理想构造了一个“超越少女崇拜”的“母神崇拜”系列:女娲——警幻仙姑——贾母——王夫人——贾元春——刘姥姥(因其救赎贾府),在《大观红楼》(3)(4),她一反曹雪芹展示“薄命司”又副册——副册——正册的顺序,按照等级身份高低的正册——副册——又副册顺序进行人物论述,加上引用扬袭抑晴的脂砚斋批语,这样,被曹雪芹排在首位的晴雯自然在人物论中处于末端。
但欧教授弄错了。如果她稍微认真了解一下曹雪芹的家世文献资料,就不会得出出身于包衣-仕宦之家的曹雪芹是“没落贵族的落魄王孙”的错误结论,更不会把曹雪芹对贵族阶级的批判说成是“贵族阶级的挽歌”;如果她阅读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楝亭集》和曹雪芹的生平资料,了解包衣曹家在世代为奴的屈辱里,始终保持着自由心性和反奴人格追求,就会理解为什么《红楼梦》会那么关注奴婢命运,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反奴文学杰作,会把“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晴雯置于“薄命司”簿册的首位,为她奉献颂歌和悲歌。[12]

曹雪芹邮票
可惜欧教授没有这样做。她站在贵族贾府的立场上诠释文本,站在王夫人代表的礼法势力和观念一边看待晴雯。这样,她就不可避免地要曲解、丑化以至最终黑化晴雯。欧文几乎把有关晴雯的关键性情节都做成了罪案:
她用礼教等级观念的“特权意识”诠释晴雯判词“心比天高”,仅仅是论述所谓“二等主子”或“半主”一项,欧文就给晴雯戴如下帽子:“怡红院中真正当家做主的,是包括晴雯在内的一干大丫鬟,而最常使用这一特权的太上皇,实即为晴雯。”(233页)“无视分际的身份僭越者”,“‘假传圣旨’的权力滥用者”(264页),“晴雯的反仆为主,越俎代庖,确为怡红院中的唯我独尊者。”(265页)
这些可都是破坏贵族之家礼法等级制的罪名。
受等级观念影响,晴雯常骂小丫头,因为坠儿偷窃,她愤怒之下擅自撵逐,并且用簪子狠扎。不能为晴雯的性格缺点和过失辩护,但欧文肆意夸大,用“对下位者极尽行使打骂的权力”(248页)、“打骂小丫头不仅是家常便饭,而且打骂兼具,言语尖刻,方式凶狠,态度凌厉”(258页),“施加不符比例的残忍酷刑”(255页),“动用私刑”(251页)等严厉批判,都是为了强化前面所加的“身份僭越者”种种罪名。(其实除坠儿一事外,书中晴雯无“打骂兼具”之记录。)
她用“逾越分际”的罪名否定了“撕扇”情节中晴雯的反奴风骨,又在“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一节,曹雪芹热烈称颂的“勇”字上大做意识形态文章,说“晴雯的‘勇’其实是‘勇而无礼”:

一无所惧的晴雯乃是出于有恃无恐,无所顾忌而横冲直撞的蛮勇,在若干恃宠而骄的情况下,甚至有如一尊毫无自尊、不加约束的自走炮(aloosecannon),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假平等”,“假民主”。(339页)

《红楼十五钗》
欧文重视的是礼教之“礼”,曹雪芹重视的是人格之尊。抄检大观园的晴雯倒箱,再一次证明她的反抗精神无愧“勇晴雯”之赞。但却为欧文所屏蔽。
如前所叙,为了证明王夫人的“合理合情合法”,欧文紧接着还屏蔽了王夫人残酷撵逐重病晴雯的情节,屏蔽了王夫人向贾母撒谎掩盖罪责的情节,以及灯姑娘偷听宝玉晴雯对话证明他们关系纯洁清白证明晴雯受冤屈的情节;而表现晴雯临死前悲愤反抗的情节,竟被解读为晴雯有“私情密意勾引”宝玉的“不安定因子”……(第77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位名人说过:“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里拷打出洁白。”当人们陷入认识误区的时候,即使并非出于恶意,也会做出错事或蠢事来的。

邮票《晴雯撕扇》
九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思想的差距。二十一世纪有人企图回到“礼教”思维,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却超越他的时代面向未来。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他设计的“情榜”,据脂批,“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已无可疑,而晴雯则可能正是谐音“情文”。可以肯定,他们都是体现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情”的理想的关键人物。
欧文的逆向操作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和文本实际必然南辕北辙。欧文把晴雯“横竖在一起”的童真幻想,作“准姨娘的自觉”的世俗化解读,津津乐道于为贾宝玉设计妻(黛玉)妾(袭人)的婚姻蓝图(385至396页),说明她完全不理解曹雪芹在宝黛宝晴关系上寄托的“情”的理想,乃是追求建立在人格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真诚奉献的精神知[13]己。
其实,在近代以前,这种超越性爱的“蓝颜知己”已经在中国社会如晨星般出现,明清之际的笔记史料和《聊斋》《儒林外史》都留下了印记,《红楼梦》则通过“假语村言”赋予了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的美好人性理想为传统和世俗所不容。

张惠斌绘晴雯补裘
仅从标志性词语看,“爱将笔墨逞风流”(张宜泉《题芹溪居士》)的曹雪芹给“风流袅娜”的黛玉和“风流灵巧”的晴雯以及追求“风流奇异”的宝玉都贴上“风流”的标签,就是一种背弃和超越世俗的反拨“风流”污名化的审美理想的表达。
然而,这种审美理想却为欧氏奉为“母神”的王夫人等礼教势力厌恶不容。)[14] 脂批说:“一篇为晴雯写传,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风流也。”(第77回庚辰本批语)[15]。
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文对晴雯的“出于既定成见和主观好恶下的贬抑”,既有个体因素,也有传统及世俗因素,也就不足为怪了。黛钗晴袭,人们可以各有所好,但对曹雪芹及其创作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实有必要。
2024年12月29日于深圳
注释:
[1] 本文所引《红楼梦》,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欧丽娟《大观红楼》(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凡引自此书,不再注出版信息,只标明页码。
[3] 【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190页,353页。
[4] 参见刘上生《晴雯判词研读札记》,《红楼梦学刊》公众号2022-3-29;3-31.
[5] 参见刘上生《晴雯反奴人格的曲线和底线》,《红楼梦学刊》公众号2021-3-25
[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30页。
[7]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361页。
[8]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285页。
[9] 欧丽娟《大观红楼》(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606页。
[10] 欧丽娟《大观红楼》(1),59页,168页。
[11] 欧丽娟《大观红楼》(1),绪言v。
[12] 参见刘上生《关于包衣曹家社会地位的辨析》,载《曹雪芹研究》2024年第2期。
[13] 参见刘上生《曹雪芹为何偏爱“风流‘“》,光明网202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