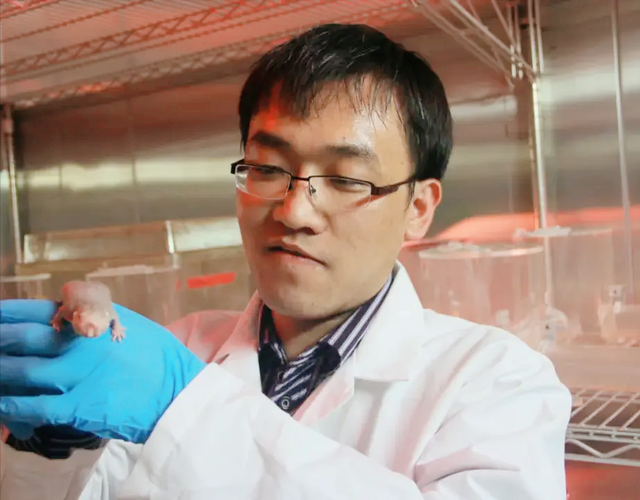当基因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科学界,细胞,古老而神秘的生命单位,这个比基因更基础、比器官更微观的生命载体,正在成为我们理解健康、疾病乃至人类未来的关键密码。
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一位善于将医学科普与文学相结合的作家、医生和学者。他的首部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2010)被誉为现代科学写作的里程碑,荣获普利策奖,并被《时代周刊》评为“过去100年最佳非小说类作品之一”。随后,他在2016年出版的《基因传:众生之源》继续探讨遗传学的深远影响。
如今,他的新作《细胞传》(中译版)面世,这次是什么驱动他将目光投向了细胞?

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第一次以如此迫切的姿态直面细胞的力量与脆弱。病毒如何入侵细胞?细胞如何应对感染?治疗的关键又是什么?正是在这些尖锐的问题面前,他意识到仅仅研究基因是不够的。基因是乐谱,而细胞是乐器;只有深入理解细胞,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运作法则。
“基因虽然是生命的支柱,但它们本身并不具备生命。细胞,才是更核心的生命单位。”这位作者在访谈中如是说。细胞是构建生命的乐章,是所有疾病的舞台,帮助更好地理解健康、疾病及人类命运。从CAR-T细胞疗法到体外受精(IVF),从基因编辑技术到干细胞再生,这些科学突破也指向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在理解生命的单位,也在重新书写生命的可能性。
但科学之路,从未一帆风顺。突破的背后,是挑战与争议并存的现实。CAR-T细胞疗法在癌症治疗中被誉为革命性的技术,但也有患者因疗法本身而罹患新的疾病。而体外受精技术,虽然为无数不孕家庭带来了希望,却也因性别选择等伦理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科学的进步永远伴随着道德的考量,”悉达多·穆克吉说道,“我们不能只谈技术的成功,也必须直面公平性、伦理性与成本的挑战。”
如今AI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令人无法忽视:从预测蛋白质结构到设计新药分子,从解读临床数据到优化实验室工作,AI已成为科学家的有力助手。但悉达多·穆克吉也冷静地指出,AI的真正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新型人类”——在新书中,他提出了这一令人深思的概念。人类曾以为生命的诞生是自然法则的不可逆转,而第一个体外受精婴儿的降生,打破了这一观念。当细胞被重新编辑、器官被再生、基因被精确修复时,人类自己也成为了科学重塑的对象。这并非科幻小说的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未来:通过细胞科技重塑的人类,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
在科学的推动下,细胞研究正在为疾病治疗与生命理解带来全新的可能性。《细胞传》梳理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同时探讨了技术进步与伦理考量之间的平衡。这本书是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深邃对话,它为细胞正名:细胞并非冰冷的生命单元,而是构成生命与未来的微观乐章。
在这场科学与人性的交响曲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聆听者,也是参与者。那么未来的“新人类”将走向何方?科学与伦理能否和谐共鸣?悉达多·穆克吉与“后浪研究所”聊了聊。
以下对话经编辑。

后浪研究所:
你曾写过《众病之王:癌症传》和《基因传:众生之源》两部著作,而这次新书的焦点是“细胞”。
是什么启发你撰写这本书的,它与你之前的作品又有哪些联系?
悉达多·穆克吉:
这本书的诞生源自几个契机。首先,当我写完《基因传》一书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基因”虽然是生命的构成单位,但它们本身并不具备生命;基因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基石,但“细胞”才是真正的生命单元。因此,我想捕捉细胞这一生命基本单元的奥秘,并探讨它如何构建了我们,我们又是如何由它们拼织而成的。
其次,我们不仅在理解细胞,还在操控它,甚至创造全新的细胞形式。比如,CAR-T细胞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以及利用基因工程生产胰岛素的细胞。这引发了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细胞改造”的潜力与后果?
第三,我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新审视疾病的根源——许多病症其实是“细胞功能的失调或调控的紊乱”。长久以来,我们被困在一种“基因中心主义”的框架中,习惯于将疾病归咎于基因、环境、行为、暴露或偶然性。在我的前作中,我曾将这些因素总结为“五边形”的五个维度。但这个“五边形”的每个因素,如果没有“细胞的改变”作为基础,根本没办法引发疾病。因此,要真正理解疾病的本质,必须回归到“细胞”这一生命单位。

此外,这本书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全球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洗礼。疫情让我再次深刻意识到: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剖析病理,最终都绕不开对细胞的理解。细胞是生命的核心,它是疾病发生与治疗的关键。而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撰写一本系统探讨“细胞生物学的历史与未来”的书。
后浪研究所:
我能感受到你在写作上很注重文学上的美感,你常通过精妙的比喻,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些艰涩的医学术语。在这本新作的标题《细胞之歌》(The Song of the Cell)中,就能感受到这种意蕴。是什么促使你将细胞与音乐联系起来的呢?
悉达多·穆克吉:
书名不会在开始时降临,唯有当写得接近完成了,它才会在某个瞬间自然浮现。写完这本书时,我陷入深思:细胞之间的相互依存,构建生命的方式,何其像音符之间的和谐共鸣。单一的音符无法奏出音乐,只有成组的音符汇聚成旋律,而所有音符的交织,才能演绎出一首乐章。

这与细胞何其相似——每一个细胞都是独立的生命单位,宛如画作中的像素,细腻且微小。但孤立的细胞无法塑造器官或构成生命,唯有众多细胞的协奏,才能谱写出生机盎然的生命篇章。因此,将细胞之美比拟为音乐的律动,成为了书名的由来。
后浪研究所:
说到生物学研究的核心理论,细胞理论是最早出现的,大约200年前,德国生物学家将细胞确定为生命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大约70年前,随着DNA分子结构的揭示,基因理论开始兴起,生物学开始向分子层面转变。
悉达多·穆克吉:
很有意思的是,像鲁道夫·维尔肖(Rudolf Virchow)这样的病理学家早就理解到,尽管基因很重要,但细胞的地位同样重要。细胞是可见的,我们需要一系列新技术的发明,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细胞及细胞理论。
如果生物学有“定律”,那应该是:遗传密码的普遍性、进化的普遍性和细胞理论的普遍性。长期以来,这三者中的前两项已经被广泛探索和理解,而细胞理论的理解和普及相对不足。这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细胞和基因之间是一种“阴阳关系”,互相依赖:没有基因,细胞无法形成;但没有细胞,基因也无法发挥作用。
后浪研究所:
这本新书主要围绕三个核心主题:“细胞发现的历史”、“对细胞功能的科学理解”,以及“细胞功能失调引发的后果及我们今天的应对方式”。首先在细胞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发现令你印象深刻?
悉达多·穆克吉:
当我们深入理解细胞及细胞系统如何相互协作时,我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便愈发深刻。例如,免疫学是一个极佳的案例。它代表了我们对细胞之间的相互沟通,以及在疾病状态下这种沟通“崩溃”的理解所达到的高度。

另一个例子是1型糖尿病。我们已经明确,疾病的根源在于胰岛素分泌细胞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主要源于自身免疫系统的错误攻击。这类疾病让我们明白,只有真正理解细胞的生理机能,我们才能掌握疾病的病理,寻找到治疗之道。

后浪研究所:
你在新书中详细探讨了技术这一主题,尤其是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包括干细胞技术、基因编辑与免疫疗法等前沿医疗手段。那么,这些技术目前取得了哪些突破?
悉达多·穆克吉:
毫无疑问,CAR-T细胞疗法是癌症治疗领域的一项革命性突破。我本人也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与合作伙伴共同在印度建立了首批CAR-T疗法中心,这在印度尚属首创。而在中国,CAR-T疗法的推广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令人振奋的。
另一个例子是基因编辑技术(Gene Editing),这种技术被用于修复特定细胞,以治疗罕见疾病,比如通过骨髓移植疗法来应对一些遗传性血液病。这也是我们在癌症治疗研究中关注的方向之一。

此外,体外受精(IVF)同样值得一提。它本质上就是一项依托细胞技术的突破性手段。此外,我们正在探索更多新领域,比如通过基因编辑治疗镰状细胞贫血与地中海贫血等血液疾病。这些技术已获得美国FDA的批准,正在逐步改变患者的生活。此外,科学家们正尝试利用干细胞再生胰腺细胞、重建皮肤细胞,乃至重塑其他功能细胞,这些都标志着细胞疗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后浪研究所:
这些技术仍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悉达多·穆克吉: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挑战。细胞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系统,任何微小的改动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比如,尽管CAR-T细胞疗法在治疗癌症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但极少数患者却因CAR-T细胞引发了其他类型的癌症。这便是我们需要攻克的一道难题。
另一个例子是IVF。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细胞疗法,IVF无疑为无数家庭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引发了伦理层面的争议。例如,IVF技术使性别选择成为可能,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性别选择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后浪研究所:
还有治疗费用高昂的问题。
悉达多·穆克吉:
没错,细胞疗法的复杂性带来了高昂的成本:细胞必须在无菌环境下培养,能够在体外生长并存活,最终成功移植到人体中。

公平性与可及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以CAR-T疗法为例,在美国,治疗费用高达35万-45万美元。然而,通过努力,我们已在印度将治疗成本降低至6万到7万美元,并正在探索如何让成本进一步降低。另外像IVF这样的技术,已经走入寻常家庭,为饱受不孕之苦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后浪研究所:
你一直在致力于关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方面的工作,请分享一下你目前专注的研究方向与治疗方法?
悉达多·穆克吉:
我参与创立了一家名为Vor Bio的公司,我们在这家公司中结合基因编辑技术与CAR-T细胞疗法,同时配合抗体疗法,开创了一种全新的AML治疗策略。今年9月,我们公布了试验的初步结果,数据非常积极,而在12月,我们会发布进一步的成果。
后浪研究所:
你提到了“新人类(New Human)”这个概念。在书中,你提到这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命题,甚至比科幻小说里的角色更加令人震撼。那么,这种“新型人类”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
悉达多·穆克吉:
我认为,通过细胞科技的重塑,人类自身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这种“新人类”与你我截然不同,他们是通过细胞的改造与再造而诞生的。但我们或许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将细胞疗法视作一种日常的医学手段。
然而,当第一个体外受精(IVF)婴儿降生时,这一切曾是多么不可思议。那是人类第一次在培养皿中创造生命,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便是这场医学奇迹的象征——世界上第一位通过IVF技术出生的婴儿,她的诞生颠覆了人类对于生命起源的传统认知。

我希望通过“新人类”这种说法,向人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今天,我们通过细胞技术改造器官,重塑骨髓,甚至创造新的生命单元。这些改变所塑造的人类,将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新人类”。

后浪研究所:
回首作为医学研究者的职业生涯,最让你振奋和最挫败的时刻分别是什么?
悉达多·穆克吉:
对我而言,最令人激动的时刻,莫过于为人类创造新的药物。研究的最终目标便是让科学的火花照亮现实,开发出能够拯救生命的疗法。当看到自己的努力化作希望与疗愈,这种成就感无与伦比。

然而,最令人沮丧的是,这一过程之缓慢,往往超乎想象。尤其药物的研发,我们必须经过繁复的试验与验证,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这条漫长的道路,充满了等待与反复,有时会让人深感挫折,步履维艰。
后浪研究所:
有一种说法,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有“双十定律”,也就是需要“十年时间和十亿美元”。
悉达多·穆克吉:
我认为,现在所需的时间大概缩短至五年,成本也降至约五亿美元。这虽然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后浪研究所:
创造新药的旅程,有时是否也包含“运气”的成分?
悉达多·穆克吉:
确实,人们常说“运气”,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垂青,而是需要深思熟虑的谋划与精准的战略。科学的突破并非偶然的馈赠,而是智慧、努力与耐心共同铺就的结果。
后浪研究所: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来自Google DeepMind的科学家,他们在AI技术对于蛋白质结构的预测与设计领域的成果,令人惊叹。你是否认同,AI已经对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悉达多·穆克吉:
我对此深表认同,我很早便意识到了AI的巨大潜力。大约五年前,我为《纽约客》撰写了关于医学AI的第一篇文章,文中聚焦于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的开创性工作。
他后来因在物理学领域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能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我倍感荣幸。如今,我本人也在积极参与AI领域的研究,探索它在医学中的广泛应用。
后浪研究所:
AI已经成为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了吗?目前它的主要应用是否依然集中在结构预测等方面?
悉达多·穆克吉:
AI的应用早已超越了结构预测的范畴。它的影响深入到医学的各个领域,比如:更加精准地解读临床试验数据,提高试验效率;对分子结构进行预测,辅助药物设计;发现与开发全新药物,拓展治疗的边界。

AI的应用横跨从基础实验室工作到复杂的临床数据管理,涵盖了医学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它让科学家能更加专注于创新与发现,而繁琐、重复的工作则交由AI来完成。
事实上,AI几乎渗透了医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它也为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与视角。
后浪研究所:
AI目前主要依赖已有数据进行预测对吗?
悉达多·穆克吉:
确实如此,但现在我们正在迈向一种新的AI形态——生成式AI。这种AI不仅依赖大规模数据集,更具备创造力。在化学领域,生成式AI已能凭借算法设计出全新的分子结构。尽管它仍需人类的训练与引导,但它已开始具备某种启发性的创造潜力。这或许正是医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后浪研究所:
在你写的第一本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离治愈癌症如此接近,只缺少登月计划般的意志力、资金和全面规划。”十几年过去了,你还笃信这句话吗?或者有了什么新的感受?
悉达多·穆克吉:
是的,尽管前路漫长,但我们的进步毋庸置疑。让我举个例子:当我完成那本书时,约有10%-15%的复发性白血病儿童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彼时,80%的白血病患儿能够被治愈,但对于那20%复发且治疗无效的孩子而言,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如今,这一局面已大大改观。在这20%的孩子中,约80%的人如今也能获得治愈。这意味着,超过90%的白血病患儿都能看到康复的希望。

这只是冰山一角,另一个例子是乳腺癌。过去,许多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复发,存活率极低。而如今,许多患者不仅存活了5年,甚至能迎来10年的健康生活。对于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等疾病,我们也找到了新的治疗途径。但一些癌症依旧是我们尚未攻克的堡垒,比如胰腺癌。尽管挑战重重,但我们正在一步步攻坚克难,每一小步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科学的曙光终将穿透这片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