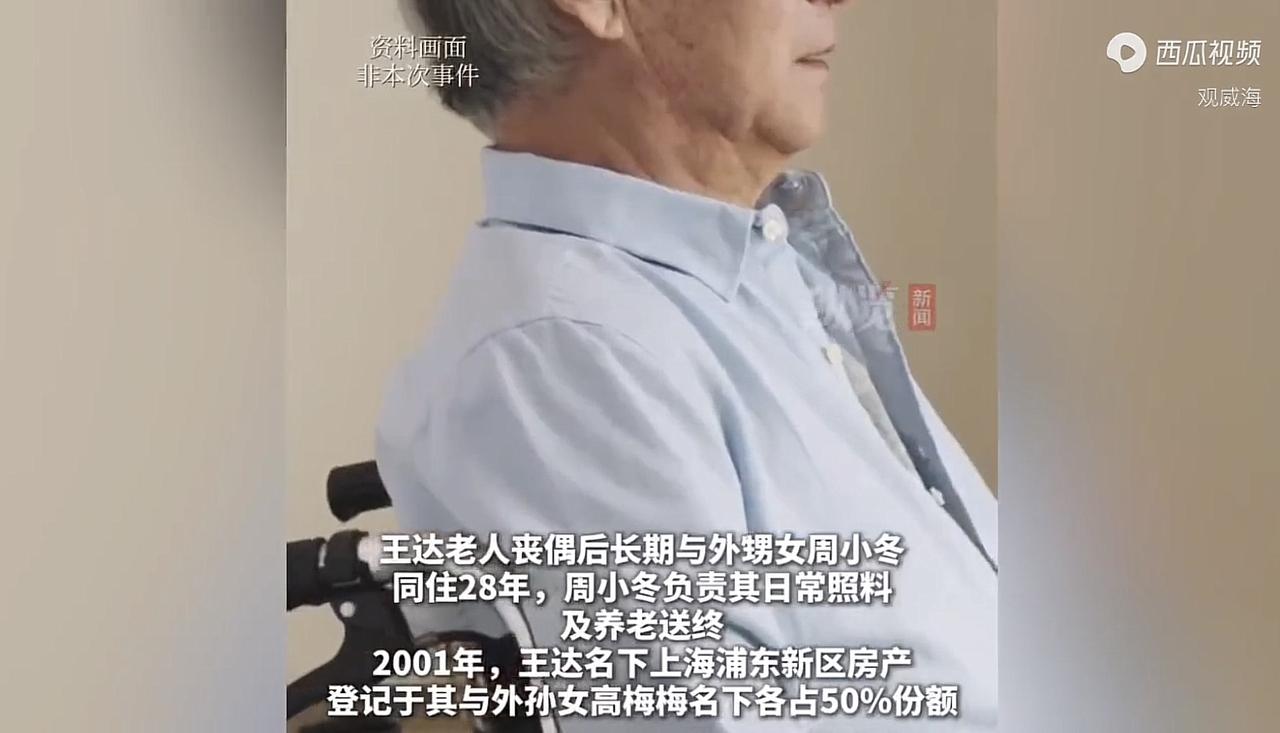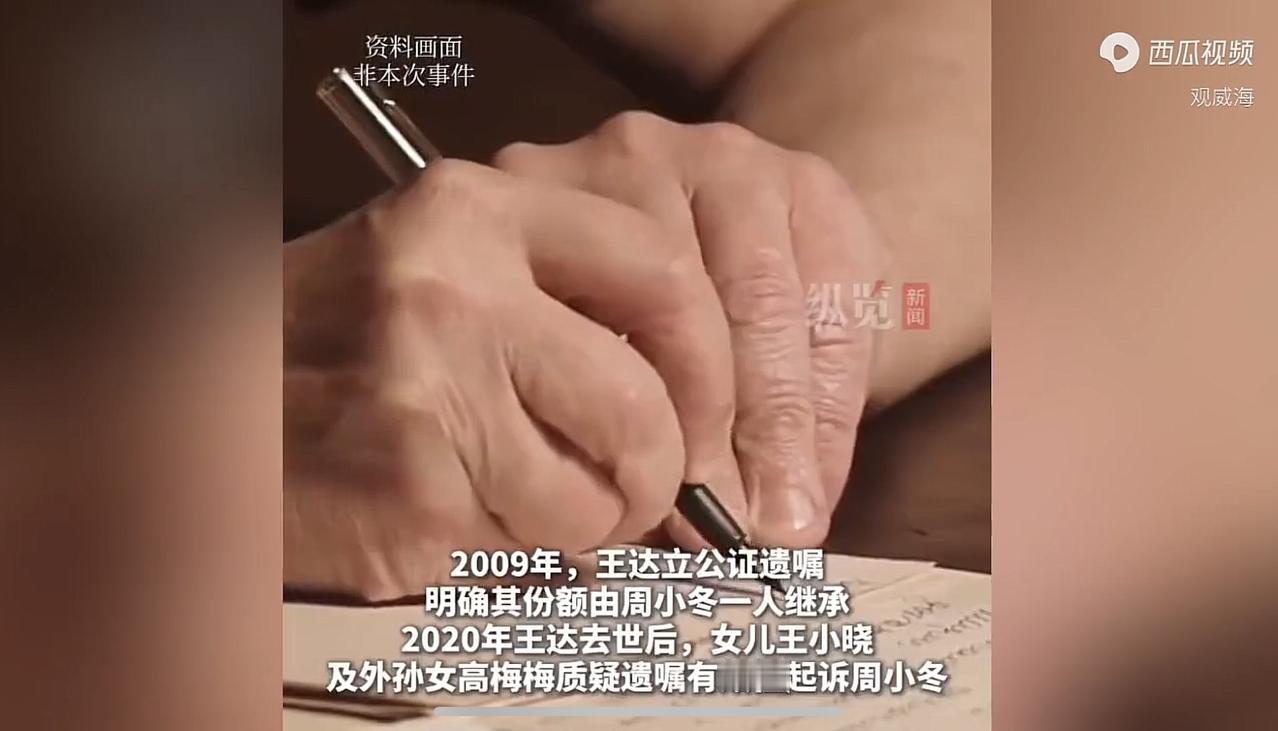上海,女子数年前从外地过来帮舅舅做生意,并照顾舅舅28年,还给他养老送终,期间舅舅亲女儿却不管不问,把抚养责任全推到女子头上。舅舅念着外甥女的好,去世前立下遗嘱,要把自己房产其中50%的份额给女子,谁知舅舅去世后,亲生女儿诉至法院,说女子无权继承,一审法院判女子和亲女儿各继承25%的份额,双方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出乎意料。 8月4号,观威海报道,1992年,34岁的周小冬揣着500块钱从江苏农村来到上海。 那时舅舅王达刚丧偶,在浦东开了间小杂货铺。 舅舅说对周小冬说:你帮我看店,我供你吃住。 周小冬起初只是帮工,后来她看舅舅独居寂寞,便把丈夫和2个孩子接来同住,一住就是28年。 邻居们都知道,周小冬对舅舅王达照顾得有多体贴,虽不是亲女儿,但胜似亲女儿。 相比之下,王达的亲生女儿王小晓却对父亲格外疏远。 王小晓2003年结婚后搬去松江,每月只来看父亲2次,还总说工作忙,每次来坐一会就走。 到了2001年,王达突然把外孙女高梅梅,也就是王小晓女儿的名字,加进了他在浦东那套68平老房子的房产证里,两人各占50%。 当时高梅梅刚上大学,王达说外孙女也是孙,加进来没什么不妥。 可这话让周小冬的丈夫老陈听着却不是滋味,毕竟房子实际是他们夫妻俩装修的,水电费也一直从他们账户扣。 直到2009年冬天,王达把周小冬叫到床前,他掏出公证处开的遗嘱,说我那份房子,以后都给你。 这份遗嘱显示,王达明确将名下50%产权指定由周小冬继承。 到了2020年3月,91岁的王达在睡梦中去世。 当周小冬还沉浸在悲痛中时,4月15号,王小晓带着女儿高梅梅闯进老宅,说我们是法定继承人,你一个外甥女,有什么资格继承? 到了5月,双方矛盾彻底爆发。 周小冬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和外孙女起诉她"伪造遗嘱",并强调根据《民法典》,受遗赠人应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表示接受,"你5月20日才在居委会声明接受,早就过期了!" 一审法庭上,周小冬哭得说不出话,说我天天守着舅舅,哪知道还要写什么声明? 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判决房产由王小晓继承,但考虑到周小冬28年扶养,从王达份额中划出25%给她。 周小冬却不服,她的律师拿出关键证据:2019年王达住院时,周小冬曾把房产证放在病房抽屉,护士作证"老爷子说'这房子以后是小冬的'";2020年1月,周小冬在家庭微信群发消息:"舅舅的房子我接着住,大家没意见吧?"12个亲属无人反对。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周小冬究竟有没有权利继承? 《民法典》第1124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传统理解中,“表示”通常需以书面形式或明确行为作出。 周小冬虽未在60日内提交书面接受声明,但通过以下行为间接表达了接受意愿: 王达生前将房产证交由周小冬保管,且邻居、护士证实王达曾表示“房子以后是小冬的”,可视为周小冬以实际占有行为表明接受。 2020年1月,周小冬在家庭微信群中明确表示“舅舅的房子我接着住”,12名亲属无人反对,构成对继承权的公开主张; 28年扶养事实与遗嘱内容相互印证,证明周小冬早已以行动履行继承预期。 二审法院未机械适用“60日书面表示”规则,而是结合周小冬的实际行为、家庭关系及社会常理,认定其已通过“默示+明示”的复合方式完成接受表示。 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表示”形式可多样化,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行为效力,避免教条化适用法律。 《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该条款旨在保护两类非法定继承人:一是长期依赖被继承人扶养的人,如无生活来源的亲属,二是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如无血缘关系的照料者。 周小冬属于后者。 周小冬从1992年起与王达共同生活,负责其饮食起居、医疗陪护,符合“扶养较多”的条件。 邻居、居委会的证言及王达生前多次表示“女儿不管自己”,进一步证明周小冬的扶养行为具有唯一性和必要性。 王达2009年立遗嘱将房产指定给周小冬,正是对其扶养行为的认可,二者形成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呼应。 一审法院虽认定遗嘱效力存疑,但依据本条从王达遗产中划出25%给周小冬,体现了对扶养贡献的补偿。 二审法院在确认遗嘱有效的基础上,未再单独适用本条,但隐含了“扶养事实强化遗嘱真实性”的逻辑,也就是周小冬如果未长期扶养,王达不太可能将房产遗赠给她。 二审法院认为,周小冬长期保管房产证、向亲属明示继承意愿等行为,已构成"以行为表示接受遗赠"。 2022年3月,法院改判:王达名下50%房产由周小冬全额继承。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猫眼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