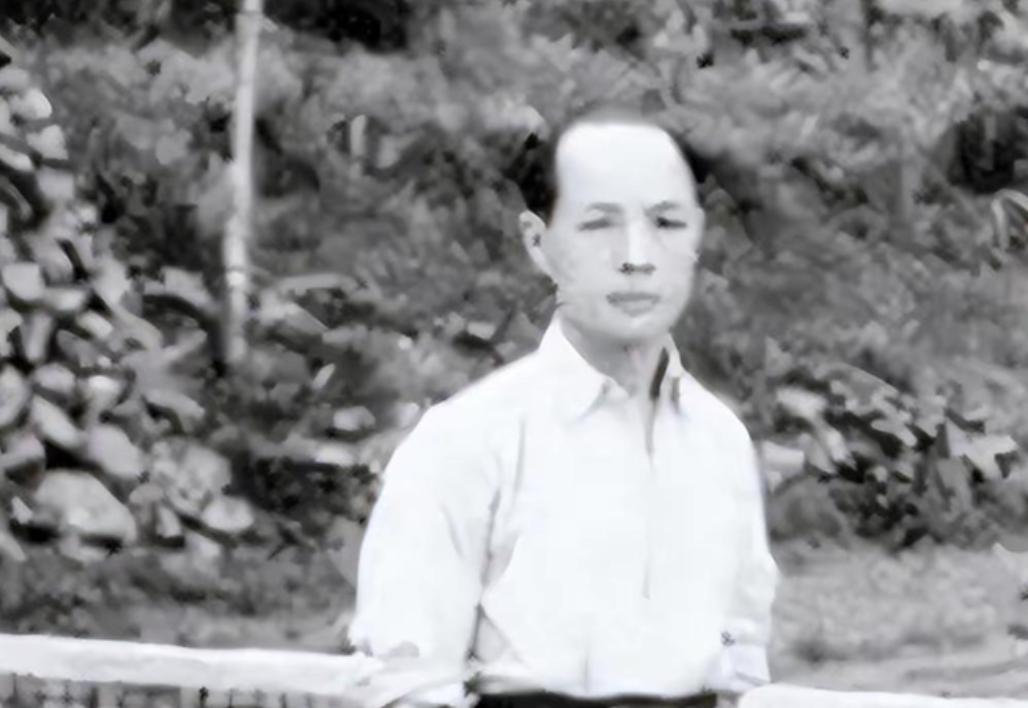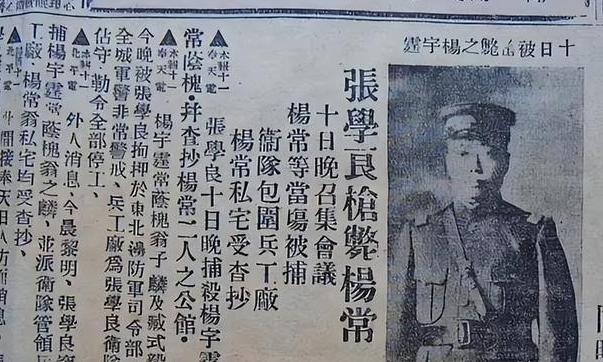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刘乙光这个人,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恶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 这件事,他做得近乎完美,也正是这份完美,才让赵一荻恨到了骨子里。 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西安城一声枪响,改变了历史,也彻底锁住了“少帅”张学良的后半生,蒋介石没要他的命,却给了他比死更难受的惩罚——无限期的软禁。 最初的看守人员换了几拨,都不太让上面满意,直到戴笠选中了他的黄埔同学刘乙光,这个局面才算定了下来。 戴笠看中他什么?忠诚、严谨、话少,像一部精准的机器,执行命令绝不打折扣。 于是,刘乙光便成了张学良夫妇身边一个甩不掉的影子,从浙江奉化到贵州桐梓,再到台湾新竹,张学良的囚禁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唯独这个看守者始终如一。 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有网友形容得特别到位:“这不是坐牢,这是精神上的凌迟。” 张学良夫妇住的院子,风景再好,也只是一个大点的牢房,院墙外,明哨暗哨24小时不间断,一公里内都是禁区,张学良想在院子里散散步,可以,但必须在刘乙光的注视下,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而且总有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 赵一荻想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没问题,写好了先交给刘乙光,他会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查,任何可能泄露信息或者带有抱怨情绪的词句,都会被他用红笔圈出,然后整封信被退回。 有一次,赵一荻实在忍不住,在信里夹了一张小纸条,想托来访的友人带出去。她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就在递出的那一瞬间,刘乙光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她身后,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张小纸条拿走,撕得粉碎。 那一刻,赵一荻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无力,在刘乙光的严密监控下,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无数个碎片,每一个碎片都贴着“报告”和“批准”的标签。 吃饭前,有人要检查饭菜,晚上睡觉,房门会被从外面锁上,就连白天在房间里说话,都得压低声音,因为他们总觉得,刘乙光的耳朵就贴在门外。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有时候气得摔杯子砸东西,刘乙光也从不进来制止,他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记上一笔:“今日,张将军情绪不稳。” 这种压抑,对赵一荻的折磨尤为深重,她是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甘愿陪伴张学良共度囹圄,她不怕物质的匮乏,却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囚禁。 她恨的,不是刘乙光这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冰冷、刻板、毫无人性的制度,刘乙光就像一堵会移动、会呼吸的墙,日复一日地提醒她:你是不自由的。 其实,换个角度看,刘乙光自己又何尝是自由的呢?他的那些黄埔同学,戴笠、张灵甫,一个个都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一个黄埔四期的精英,却把一生中最宝贵的25年光阴,耗费在看守一个“政治犯”身上。 他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没有朋友交际,他的世界里只有张学良和那份“死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囚徒,一个被“忠诚”二字困住的可怜人,张学良晚年也曾感叹,说刘乙光其实也不比他自由多少。 可道理是道理,情感是情感,对于每天都活在这种窒息氛围中的赵一荻来说,她无法原谅这个剥夺了她丈夫尊严、耗尽了她青春的直接执行者。 所以,当1962年刘乙光终于要被调走时,张学良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而赵一荻却把积压了25年的恨意,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 那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控诉。 刘乙光走后,看守张学良的政策明显宽松了许多,房门不再上锁,信件可以直接送到手上,亲友来访也变得容易。 院子里重新有了笑声,阳光似乎也变得明媚了,而离开张学良的刘乙光,人生则迅速走向了黯淡,他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彻底被边缘化。 1982年,他在家中失足摔伤,不久后因心肺衰竭去世,终年79岁,他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 出人意料的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也来了,他们在刘乙光的灵前默默伫立,献上花圈,没有说一句话。 这一刻的沉默,或许比任何语言都复杂,恨,是真的,但当那个让你恨了一辈子的人最终化为尘土时,剩下的,可能只有对那段荒唐岁月共同的叹息。 人生如戏,他们三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历史旋涡里,各自扮演着身不由己的角色,耗尽了一生。 信源:东南网 2016-12-12——探访张学良台湾故居:“少帅”的幽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