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败了,未来一百年将再无可能,如果赢了,未来一百年,甚至更长,我们的发展将不会再有国家敢打压我们,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日可待。 这样的输赢,难道只是冰冷的战略术语? 看看实验室里那台被禁令卡住的光刻机吧——镜头里本该流转的晶圆光芒,此刻凝固成墙上日历被划掉的红圈。 七十年前的西伯利亚荒原,几百个德国战俘蜷缩在漏风的木屋。零下四十度的寒风里,手指冻僵得连煤镐都握不住,监工的皮靴踩碎雪壳的声音,比肚子的咕噜声更刺耳。 同一时刻的北海道煤矿,朝鲜少年金哲的镐头每落下一次,矿灯就晃一下。十八个小时的井下劳作后,他盯着送饭桶里漂着冰碴的稀粥,忽然想起母亲教的韩语童谣,嘴唇动了动,又赶紧咬住——昨天隔壁矿道的大叔就是因为哼母语,被鞭子抽得昏死过去。 征服者最阴狠的武器,从来不是枪炮。 当汉城的学校开始教“日之丸”的画法,当景福宫的青瓦被拆下铺在日本神社的屋顶,当“李”姓被强制改成“佐藤”,民族的记忆就像被泡在福尔马林里,看似完整,实则早已失去呼吸。 你以为这只是过去? 今天的芯片禁令里,藏着同样的逻辑——不让你造最先进的光刻机,不让你用最核心的算法,甚至不让你看一眼顶尖实验室的论文。他们就是要让你永远停在产业链的下游,像当年的战俘挖煤一样,重复着低附加值的劳作。 柏林墙倒塌时,守墙士兵汉斯的日记里写:“三十年了,妹妹的婚礼我只能在望远镜里看。” 板门店的界碑旁,白发苍苍的金奶奶每年都带着泡菜来,她说:“弟弟当年跨过这条线时,兜里揣着我织的围巾。” 领土的裂痕里,流的从来不是地缘政治的墨水,而是无数家庭的眼泪。 现在的博弈场没有铁丝网,却有更密的网——贸易清单上的红叉,金融市场里的暗礁,舆论场上真假掺半的抹黑。 他们说这是“规则”,可当年日本逼着朝鲜人改名字时,不也说这是“文明进步”? 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只能在二手市场淘旧芯片,当科学家因为设备禁运而推迟研究,当普通人在超市看着进口商品涨价时——这不是“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劳累,是精神的绝望。就像当年朝鲜孩子在课堂上必须用日语回答“你是谁”,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只能用别人的技术、读别人的历史、说别人的语言,复兴从何谈起? 这不是遥远的故事——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里,自主研发的晶体正在生长;工厂的流水线上,国产芯片的测试数据在屏幕上跳动;高校的图书馆里,年轻人啃着外文文献,笔尖却在笔记本上写满“突破”的计划。 当年景福宫的琉璃瓦碎了,可朝鲜民族用百年抗争捡起来,重新拼出了自己的屋顶。 今天,我们的屋顶正在自己搭建,瓦是科技的瓦,梁是团结的梁。 你觉得,这一次,我们会让历史重演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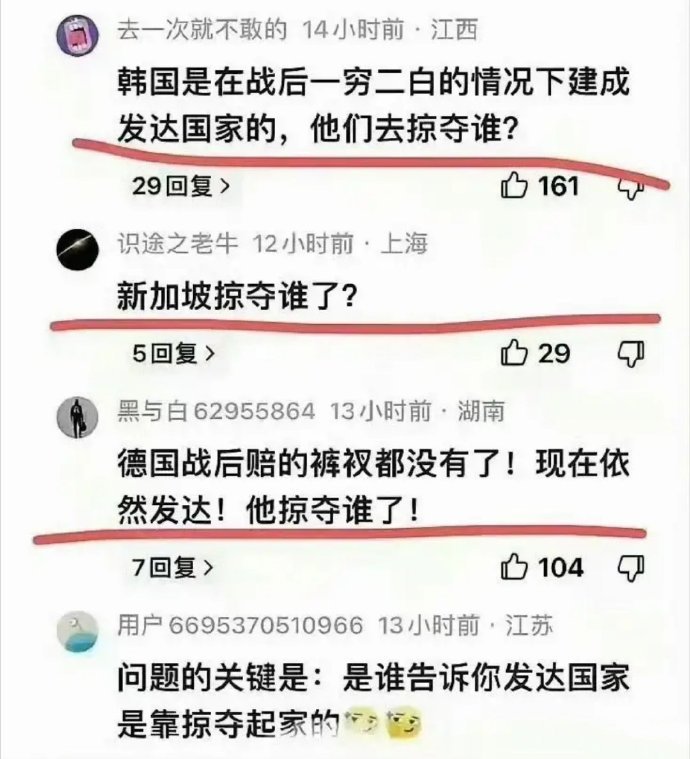






![垂死病中惊坐起,列强不是我自己!太少了,继续造[doge]](http://image.uczzd.cn/80312481742046818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