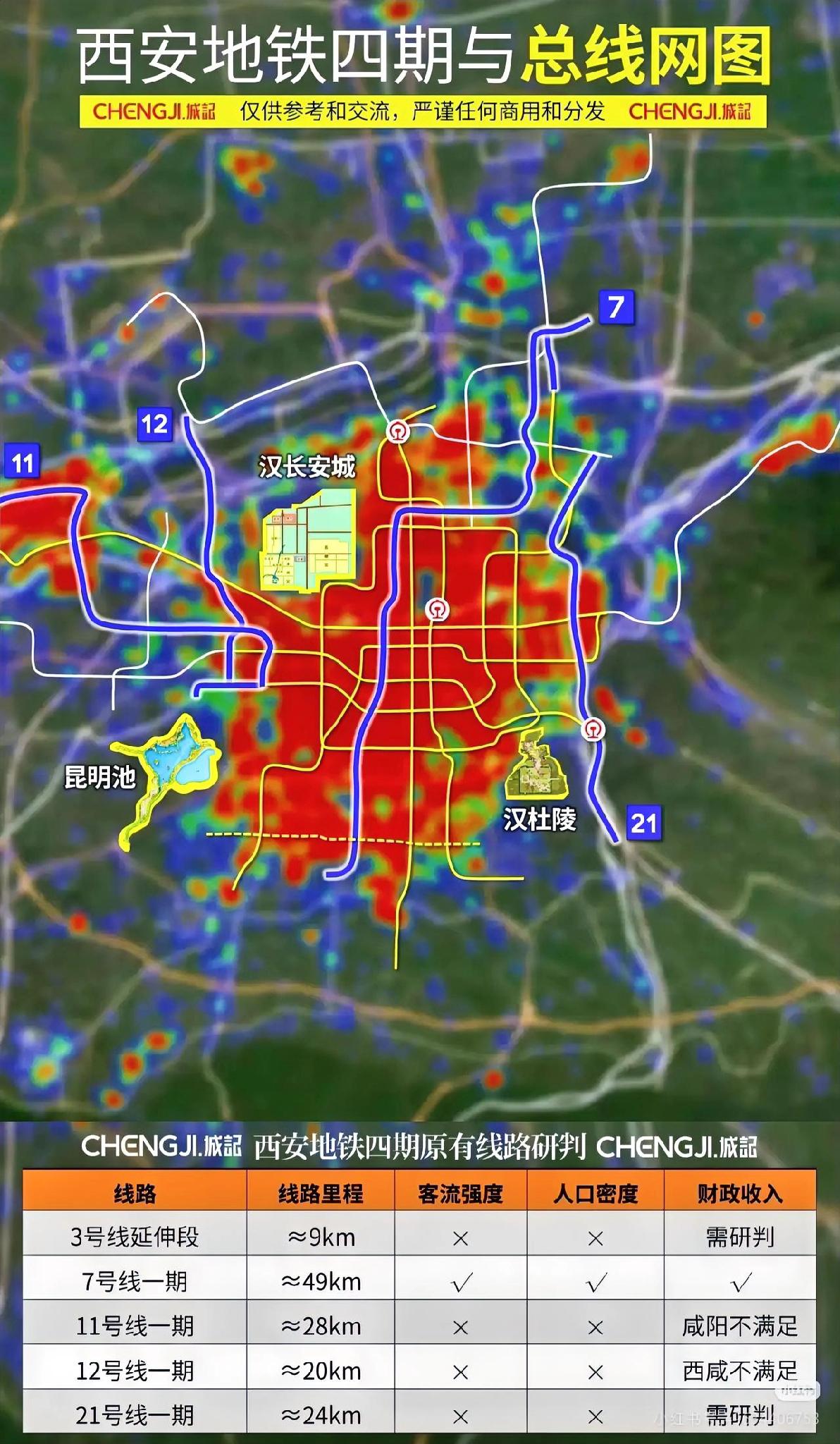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 高德隆第一次和命运“较劲”,是在1981年的西安。那一年,计划生育抓得紧,街头巷尾都在宣传“只生一个好”。他和妻子却在无数张红头文件和宣传画中,悄悄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为了有个儿子,冒着顶风的风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孩子抱回家,代价也很快清算下来。他在国营大厂的职务被撤,工资从八十多元一下掉到不到五十元,每个月还要再掏出近十元作为超生罚款。对原本靠双职工工资过日子的家庭来说,这等于把生活硬生生勒紧了一圈。 可每当他夜里起床,看见小儿子在被窝里睡得香甜,伸出一只小手抓住他的手指,他心里那点委屈和不甘又都软了。这个男孩,是他逆着大势要来的“心头肉”。 低谷并没有一直拖住他。九十年代风向渐变,市场经济的风吹进厂区,他凭着当爆破兵时练出的胆量和摸索出的物资调配经验,开始在钢材生意上闯荡,把低价货源调往急需的地方,为厂里赚来了真金白银。 业绩上去,人也被重新启用,当上小额站劳动服务公司的分管经理,家里日子又见起色。 有了钱,他更舍得往儿子身上砸。儿子集邮,他出差时就一口气买回当年发行的一整套邮票,花了三百多块,还顺带买了块手表;儿子考进四十四中,他又咬牙掏出两千多元,给孩子买了辆当时刚流行的山地车。 在多数人月薪三五百的年代,这几乎是把几个工资叠在了一起。妻子心疼,他却只盯着儿子脸上的笑,觉得只要孩子高兴,一切都值。 没想到,真正的祸根就从这份“体面”里冒出来。儿子骑着山地车去学校,马上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许多同学还为几块钱生活费发愁的时候,他骑着一辆价值两千多的车子,实在太扎眼。 王星提出要“借”车一骑,被儿子拒绝后,第二天就带着六个小混混堵在校门口,把人从车上拽下来拳打脚踢。等儿子鼻青脸肿、嘴角眼角流着血,一瘸一拐回到家时,高德隆只觉得眼前一黑,连忙把他送去医院。 医生见惯这种学生打架的伤,只是简单清洗包扎,就让他们回家。夜深后,儿子开始剧烈头痛,还不断呕吐,他这才意识到事情远不止皮外伤那么简单,又火急火燎把孩子往医院送,一边排队挂号走流程,一边托人请来脑科老专家。 专家看过片子,只说了一句“晚了,赶紧开颅”,可这“赶紧”前面,已经被种种拖延耗掉了太久。等到晚上手术做完,儿子却一直没能醒来,五天之后,医院冷冰冰地给出“脑死亡”的结论:就算勉强救回来,也只会是植物人。 儿子的死像一颗重磅炸弹,把这个原本为超生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家,彻底炸成碎片。妻子接受不了现实,精神失常,从此连车也开不了,原先那个被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转眼成了被命运连番碾压的废墟。 法律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支撑。带头行凶的小混混被判了十四年,其余五人各判五到十年,真正挑事的王星因为没亲自动手,只赔了三千块钱。 他想着儿子不过是多骑了一辆好车,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心里始终过不去。想告医院延误抢救,可在当时几乎没有类似先例,连立案都难,无力感和愤怒在心里越积越厚。 终于,他第二次和命运“较劲”,这一次用的是自己最熟悉的爆破技术。夜深时,他悄悄把自制炸弹安进那家医院的门诊楼,剧烈的爆炸掀翻了玻璃,震坏了墙体,三百多块玻璃碎裂,七人受伤,所幸无人死亡。 案子一度成了悬而未破的大案,他则悄然离开,跑去卧龙寺想剃度出家,被方丈一眼看出“执念未除”,只准做居士。后来又辗转运梁寺、莲花庙,换了地方,却始终放不下那股怨气。 2002年,他在街头碰见了当年参与殴打儿子的其中一人,那人早已提前出狱,躲在父母身后不敢抬头,母亲反倒冲着他嚷:“我儿子都坐过牢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一嗓子像火星一样,点燃了他心底最后的理智。 2004年大年初五,他做出了更极端的决定。十一枚延时炸弹被他装进新年礼盒,悄悄放在当年那些参与殴打者家门口。 幸运的是,有人在凌晨发现异常报警,警方全面排查,最终只炸了两枚,因疏散及时没人受伤,其余全被拆弹专家处理掉。 两天后,他在自杀未遂后落网,因爆炸罪和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判处死刑,2005年执行,“西安高德隆复仇案”至此画上句号。 当制度的冷硬、少年的恶意、医疗的疏忽和一个父亲的执念缠在一起时,一个普通人要被逼到多远的角落,才会一步步走到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