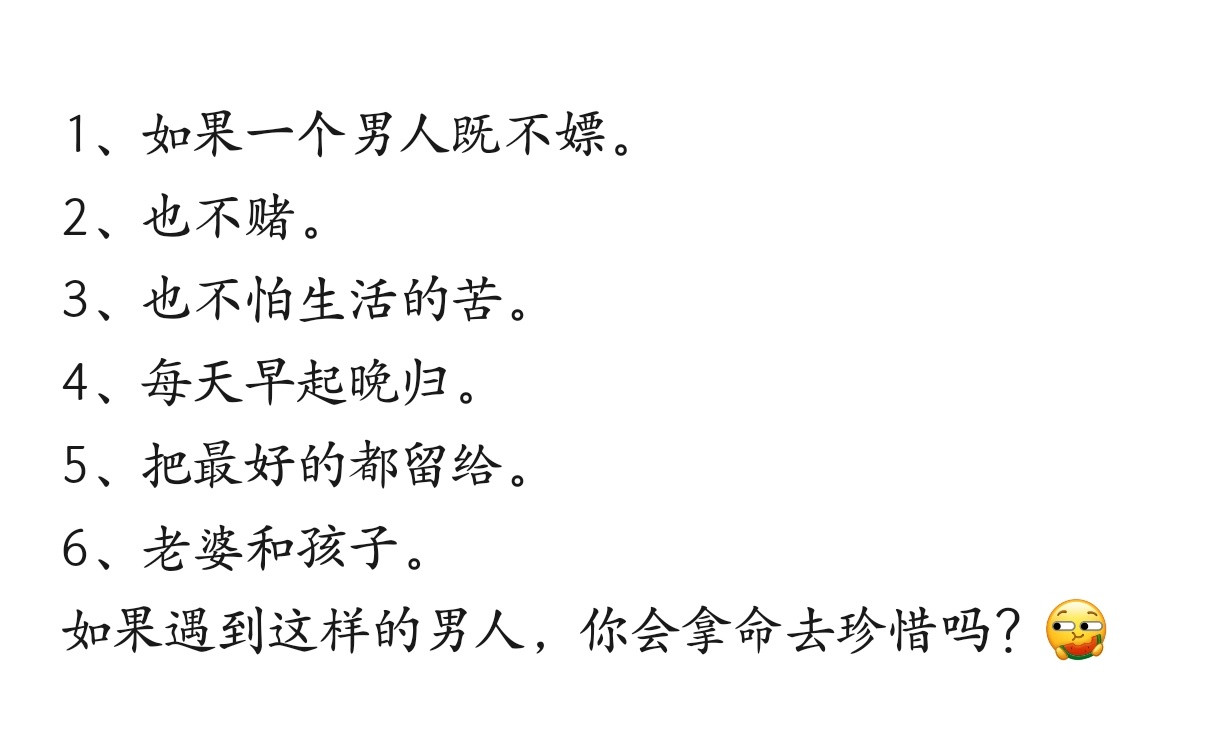有一个地主,七十岁上死了老婆。一过年,在他七十一岁时娶了一个一十七岁的女子为妻。成婚后,妙龄之妻想生个孩子,可是那个地主不愿意。 春桃不再提孩子的事了。她依旧每天早早起来,给王老爷熬粥、煎药。王老爷的屋子大,却空旷得很,只有一只老猫偶尔从门槛上溜过。春桃就坐在廊下,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一坐就是半晌。 一天,她在收拾库房时,碰落了一个积灰的木匣子。里头不是金银,是几本旧书,还有一叠泛黄的纸,上面画满了各种花草,边上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名字和用途。王老爷年轻时跑过码头,看来是那时记下的。春桃不识字,但那些画儿好看。她掸去灰,把匣子抱回了自己屋里。 那天晚上,王老爷咳得厉害。春桃照例端去冰糖梨水,却看见老人借着油灯,正眯眼瞅着一张药材铺子的旧单据,手指颤巍巍地顺着字行移动。春桃心里一动,把木匣子拿了出来。“老爷,”她声音轻轻的,“这上头画的,是药材不?” 王老爷有些吃惊,拿过看了,点点头。“都是些寻常草药,路边野地里有。” “您……能教我吗?”春桃指着画上的字,“这个念什么?” 王老爷看了她好久,油灯的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跳动。他最终指了指第一个字:“紫,紫苏。” 从此,廊下多了点别的动静。王老爷慢悠悠地念,春桃跟着学。认了字,就对着画认草药。后来,她不再只是坐着看槐树了,她挎着小篮,按图索骥,去田埂、河滩找那些画上的草。采回来,学着书上的法子,晾晒、收拾。 村里人起初笑她,地主婆倒像个采野菜的。春桃只当没听见。她发现自己认得越来越准,晒干的薄荷、艾草、车前草,竟也被村里偶尔来的货郎收去,虽换不了几个钱,却让她手心发烫。 王老爷的身子还是那样,时好时坏。但春桃端去的,渐渐不止是梨水,有时是一碗淡淡的、有清香的草茶。王老爷接过,什么也没说,只是喝得比往常慢些。 一个秋后的傍晚,凉意很重。春桃刚把晒干的最后一簸箕菊花收进来,王老爷忽然在里屋叫她。她擦着手进去,看见老人从枕边摸出一个小布包,推到她面前。 “这是……”春桃解开,里面是几块碎银,和那个她已无比熟悉的木匣子。 “匣子,给你了。”王老爷的声音有些哑,“银子不多,你收着。往后……这认草药的事,你自己也能接着弄了。” 春桃捏着布包,看着老人又闭上眼,像是累了。窗外传来秋虫声,很长,很细。 她把布包小心揣进怀里,走出去,轻轻带上了门。院子里,月光清清白白地洒了一地,像层薄霜。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平日晾晒的架子前,把空簸箕重新摆正。明天,她想,该去更远的山坡那边看看,记得那里好像有几株柴胡。
有一个地主,七十岁上死了老婆。一过年,在他七十一岁时娶了一个一十七岁的女子为妻。
正能量松鼠
2026-01-19 19:44:34
0
阅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