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社编辑阎长贵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哲理短文。
平心而论,这是一篇语言质朴,没有多少复杂构思和深刻理论探讨的文章。
阎长贵在文章里更多流露的是个人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批判了“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表达了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和人生价值观。

令阎长贵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篇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却让他此后的人生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
因为这篇文章,4年后,他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工作,5年后,他成为江的第一任机要秘书。

不过,对于阎长贵而言,命运并不是始终眷顾于他,因为,升任江青第一机要秘书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被投入秦城监狱,开启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监狱生活。
追溯阎长贵大起大落的一生,戏剧性的命运转折,全因为那一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
因为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
1、文章天下知阎长贵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阎长贵是阎家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且考上了著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
1961年,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就被《红旗》杂志社选中,如愿进入杂志社工作,并师从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
因为工作的关系,一年后的1962年9月22日,阎长贵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短文。

初出茅庐的阎长贵,在这篇短文里写下的是自己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笔端流露出的都是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大胆无畏以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被毛主席读到了。9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上方写下“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的批示。
有了毛主席的批示,阎长贵的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瞩目,自然,阎长贵也因为这篇文章,一跃成为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
不过,对于阎长贵而言,更大的改变还在后面等着他。
2、进入钓鱼台1966年6月底,阎长贵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戚本禹看中,调往钓鱼台,专门负责处理信件。
钓鱼台作为国家的高级接待场所,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安排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知名政治人物。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进入这样神圣的地方工作,对于阎长贵而言,简直就是无上的荣耀。

这年7月,阎长贵正式进入钓鱼台上班。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如同雪花一般飞来,每天都是应接不暇,有时候,一天收到的信件,就能够装下三四麻袋。
为了能够及时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戚本禹组织成立了“办信组”,由阎长贵牵头负责,专门负责处理来访信件。
因为每天收到的信件太多,“办信组”的工作人员日日都是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夜里工作到十二点,是家常便饭,每天只能睡上个五六小时。

1966年冬日的一天,晚饭过后,一个难得的短暂休息时光,戚本禹约了阎长贵一起散步,一边散步,一边闲闲说着工作和生活。
在两人闲聊的过程中,聊着聊着,戚本禹忽然停下脚步,同时看向阎长贵,郑重严肃地说道,自己已经婉拒了到11号楼担任秘书的职务,同时将阎长贵推荐了上去,让他担任11号楼秘书。
阎长贵一听此话,大吃一惊,既而连连摆手,说自己从没有给人当过秘书,恐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阎长贵的直接摆手拒绝,让戚本禹颇为不快,他再一次将严肃且不悦的目光定定看向阎长贵,明显加重了语气,对阎长贵近乎质问一般说道,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推荐你了。
说完这话,戚本禹头也不回地走远了,留下阎长贵一个人愣在原地。一阵凛冽的冷风吹过,阎长贵打了一个寒战,不禁裹紧了厚厚的棉衣,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件事怕是无可更改了。
不过,阎长贵又安慰自己道,光靠戚本禹的推荐,还是不能完全作数的。

此时的阎长贵哪里知道,11号楼的主人早已相中了他。
原来,阎长贵在钓鱼台16号楼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专门负责牵头处理从全国各地寄往11号楼的信件,就这样,阎长贵那段时间,频繁出入11号楼。

因为工作的关系,李讷其时也与阎长贵有过接触,常常在提起阎长贵,说他为人热情友善,学习刻苦,工作认真。
还有一点就是,在11号楼工作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高中毕业,像阎长贵这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可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就更加深了江青对于阎长贵的良好印象。

因此,当戚本禹一推荐阎长贵,在阎长贵想来,并不一定会一推荐就成;戚本禹这一推荐,正中其下怀。
这一切,阎长贵哪里知道?

1967年1月9日,这天晚上,戚本禹忽然兴奋地来找阎长贵,一进门便看到阎长贵正在埋头伏案工作。戚本禹走上前,对阎长贵打了一个招呼,而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阎长贵一个好消息:已经定下来了,调你去给江当秘书,现在就搬去11号楼住。

戚本禹的这一消息,再次让阎长贵吃一大惊,他没有想到戚本禹竟然真的一推荐就成,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这里,搬往11号楼。
然而,事已至此,不论阎长贵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他都必须立刻搬到11号楼。
此时的阎长贵还不知道,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大幕,已经开启。

正式成为江的秘书后,阎长贵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收发和管理送往11号楼的文件,将其按照必看件、参阅件、浏览件三种不同类别整理装袋,登记送达存档。在11号楼工作,阎长贵居住的地方也在这里,等于是每时每刻都在办公室,因为不知道领导何时会按铃叫你。

20多天后,江才第一次正式找阎长贵谈话,告诉他,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要你做事都不要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要严守纪律。
阎长贵认真聆听,感觉很受教育,也很感动。
1967年国庆节,一个名叫杨银禄的人被带到了11号楼,阎长贵非常开心,以为自己繁重的工作终于可以有人分担了。

此时的阎长贵哪里知道,杨银禄并不是来分担他的工作,而是来取代他的工作。
不久后,阎长贵就被告知,要给他“换换工作”。
“我换到了警卫连的连部,还有两个警卫看着,不久又被换到了秦城监狱接受审查。”

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被投入秦城监狱,换上了黑色囚服,从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
这一天距离阎长贵1967年1月9日进入11号楼,正好一年。一年里,阎长贵就从很多人羡慕的大人物身边的大秘书,沦落为阶下囚,命运的戏剧性转折,打了阎长贵一个措手不及。

在秦城监狱,阎长贵被关押在一个14平方米的牢房,生活用品配置齐全。冬天是一套黑色棉衣棉裤,夏天时一条黑色短裤一件粗布短袖衬衫,每天的生活是吃饭休息,等待接受审查和审问。
在这里,阎长贵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他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政治犯。
这一等待,就是两年,直到1970年,阎长贵才迎来看第一次提审,他的罪名是,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此后,阎长贵面对的仍然是漫长孤独的牢狱生活。
在秦城监狱,阎长贵将手边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反反复复看来很多遍,有的文章他读了不下于一百遍,以至于到了晚年,仍对这些文字记忆犹新,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清楚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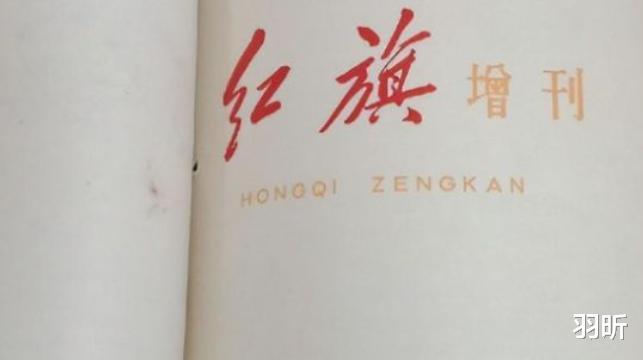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秦城监狱,告诉阎长贵,他将被送往湖南洞庭湖某国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在国营农场,阎长贵学会了喂猪放牛、整田插秧、种菜种地、洗衣做饭等所有活计,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那一刻,阎长贵觉得自己又活出了农家孩子的本色。

1979年9月,阎长贵终于苦尽甘来。这一年,他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结束了长达十二年失去自由的生活。
这一年,阎长贵42岁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
1980年3月,阎长贵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命运似乎跟阎长贵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的人生之路,从起点回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