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梓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是讲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在世德堂本成书之前,取经故事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在发展演变之中。

世德堂本《西游记》
有学者指出,《西游记》“每一个名号之下都潜隐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其自足的叙事逻辑”[1],只是在取经故事的生成与演化历程中,在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删改及写定过程中,旧故事所蕴含的部分文化信息与叙事逻辑,可能会被不断生成的新故事所磨损、遮蔽,而新的文本形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故事的种种印迹。
因此,以跨文类的多元视角观照小说文本的情节缺失与逻辑断层,有助于探寻出潜藏在文本背后的叙事逻辑与演化轨辙。
从《大唐西域记》到世德堂本《西游记》,“女国”故事都凭借其神秘而独特的魅力,成为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王子今梳理传说与史籍中的“女国”,认为其是“保留明显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文化存在”[2]。韦强则将“女国”故事分为才人系统与文人系统。[3]胡胜勾勒取经故事中“女国”故事的变迁,揭橥“百回本写定者独特的美学贡献”[4]。以上研究也为深入探讨“女国”故事奠定了基础。
然而细读世德堂本《西游记》,小说竟两次提及西梁女国的妇女有“割人肉做香袋”这一习俗,而且这个尚处于传闻状态的“人肉香袋”,竟然直接影响了唐僧师徒在西梁女国的行动计划。
小说虽然没有透露“人肉香袋”的来历,但毫无疑问的是,“人肉香袋”的出现,给原本温柔、香艳的西梁女国涂抹上了一层血腥、野蛮的色彩。语焉不详的“人肉香袋”从何而来?它与西梁女国又有什么文化渊源?
沿着世德堂本的西梁女国故事溯源而上,在丰富多元的取经故事文本中找到“女国”的历史原型,解开“人肉香袋”之谜,揭示隐藏在小说文本背后的秘辛,有助于还原西梁女国故事从历史书写到文学想象的生成、传播及演化过程。

《彩绘西游记》之“假亲脱网”
一、取经故事中的“女国”
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师徒过子母河,唐僧、八戒饮水成胎,腹痛难忍,借宿在路旁村舍的一个老婆婆家:
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事尽皆休了,故此不肯伤你。若还到第二家,老小众大,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八戒道:“若这等,我决无伤。他们都是香喷喷的,好做香袋;我是个臊猪,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无伤。”[5]

婆婆此时没有对“人肉香袋”作更多解释。猪八戒则趁机插科打诨,似乎认可了女国之人“割肉做香袋”的事实,而生性机敏好胜,专以降妖除魔为乐的孙悟空,对“人肉香袋”一事,竟然也没有任何质疑。
次日,唐僧师徒到西梁女国,女王派太师做媒,驿丞主婚,要招赘唐僧,孙悟空竟然一口应允,等太师、驿丞走后才向唐僧解释原因:

邮票《情阻女儿国》
行者道:“师父放心,老孙岂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三藏道:“怎么叫做将计就计?”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儿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换关文,不放我们走路。倘或意恶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么香袋呵,我等岂有善报?”[6]

可见此时的孙悟空对所谓的“人肉香袋”也是信以为真的,故而“将计就计”。
如此谨小慎微、谋定后动的行为,与原本“胆包身”的性格简直判若两人,在百回之中亦仅此一见。
后文师徒见到的女王,却是一副“秋波湛湛妖娆态”的娇娘模样。直到孙悟空的“假亲脱网之计”成功,唐僧师徒顺利离开西梁女国,也未见女王露出“意恶心毒”的一面。小说此后再未提及香袋,西梁女国“割人肉做香袋”一事也就抛过不提了。
回顾西梁女国故事,由于悟空听信了“人肉香袋”传闻,预先安排了“假亲脱网之计”,唐僧也假意应允了女王的求亲。随后的面见女王、倒换关文等环节才能顺利进行,小说叙事也由此减省了女王与唐僧师徒可能发生的正面冲突。
可见“人肉香袋”本是影响唐僧师徒人物行动、影响西梁女国故事发展进程的重要物象,不应草草了结。
再看早期的取经故事,唐僧师徒的“女国”之行确实没有如此顺利。
明代有一本《续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取经归来的故事。《续西游记》所续的应是世德堂本之前的某种佚本《西游记》,因此也保留了部分佚本《西游记》的故事情节。[7]

《续西游记》(岳麓书社版)
《续西游记》的第五十八、五十九回,叙述唐僧师徒取得真经,回程路经西梁女国。师徒为避免生事,决定绕开西梁女国转走山路,半途却又遇到了几个“女古怪”。小说在这两回六次提及“女古怪”要“割肉做香袋(囊)”[8],“人肉香袋”出现次数是世德堂本的三倍。
可见在世德堂本之前的小说故事中,“割肉做香袋”的确是西梁女国故事的重要情节。
在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中,师徒过女人国,女王直接在殿上求亲,唐僧不允,此时孙悟空、猪八戒诸徒已被众女缠住,无暇顾及唐僧。女王就威逼道:“不从咱除是飞在天上,箭射下来也待成双!你若不肯呵,锁你在冷房子里,枉熬煎得你镜中白发三千丈!”幸有韦驮尊天及时出现,救出唐僧,而女王却依旧不死心:“你如今去,我这里收拾下画堂,埋伏下兵将,等回来拿住再商量。”[9]
可见在《西游记杂剧》所载的女人国故事中,虽然没有“割肉做香袋”这类血腥情节,但在求亲不允的正面冲突之下,女王已经充分展露出了她强硬、霸道的一面。

陈均《〈西游记杂剧〉评注本》
由此亦可推知,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的取经故事中,女王求亲不成,唐僧师徒就不得不面对一场正面冲突。小说提及的“人肉香袋”,或许是在原有的正面冲突情节中展开的,至少“假亲脱网之计”原本不是孙悟空的预先规划,而是被逼无奈后的临场发挥。
从《西游记杂剧》中女王的威胁逼迫,到《续西游记》六次提及“割肉做香袋”,再到世德堂本《西游记》中婆婆的善意提醒、悟空的预先防备,我们可以大致确认:
“女国”的“人肉香袋”故事确实完整存在过,只是在取经故事的发展演化中,在《西游记》的版本流变中,原有的故事情节不断演化变形,世德堂本的写定者出于某种考虑,改写了“女国”故事的发展进程,删略了“人肉香袋”这一血腥情节,原本完整的故事方才出现脱落。
再追溯到流传于唐宋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取经诗话》也有“女人之国”的故事。法师一行进到内宫,女王设斋款待,僧行“盖为砂多”,都不吃斋。女王解释“此国之中,全无五谷。只是东土佛寺人家及国内设斋之时出生,尽于地上等处收得,所以砂多”。
此处设斋一节,看似荒诞,女王特设斋供,为何砂多,女王所作回答却又似通非通。对此情节,始终未有研究者作出合理解释。
随后女王也有意求亲,挽留法师:
女王曰:“和尚师兄岂不闻古人说:‘人过一生,不过两世。’便只住此中,为我作个国主,也甚好一段风流事!”
和尚再三不肯,遂乃辞行。两伴女人,泪珠流脸,眉黛愁生,乃相谓言:“此去何时再睹丈夫之面?”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颗、白马一匹,赠与和尚前去使用。[10]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在法师拒绝女王的求亲之后,《取经诗话》只是突出了“两伴女人”的反应,并没有正面描摹女王本人的情态,而法师一行亦未受阻。故事的结尾处有一诗赞:“此中别是一家仙,送汝前程往竺天。要识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及普贤。”
该诗赞的最后一句却让“女人之国”的故事显得更加模糊了。女王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人间的女帝,还是佛界的菩萨?这些疑问都笼罩在《取经诗话》朦胧而神秘的薄雾中。
要想解开“人肉香袋”之谜,回答“女人之国”的诸多疑问,必须从小说回到历史,探讨取经故事中诸多“女国”的历史原型。
二、史籍与笔记中的东女国

“女国”传说似源出印度,中世纪波斯、阿拉伯的作家乃至马可·波罗均有关于“女国”的记载。

槐荫草堂刊本《山海经》
汉籍之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11]《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之国。”郭璞注:“王颀至沃沮国,尽东界,问其耆老,云:‘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一国,在大海中,纯女无男。’即此国也。”[12]
自东汉之后,“女国”开始出现在官方史籍中,《后汉书·东夷列传》甚至有了“窥井生子”的传说:“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13]唐传奇《梁四公记》更记载有六七个不同的“女国”。
王子今认为诸多“女国”故事中的生育传说,“其实源自于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女子不交合而孕的神话,体现了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的群婚时代的社会现实”[14]。
隋唐时期的笔记、史籍,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以及《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也有关于各类“女国”的记载,可见进入取经故事序列的“女国”故事,不仅取材自渊源久远的传说,更有确凿可证的史实依据。
回到《西游记》的成书史,玄奘等僧人的西行求法是后世取经故事萌蘖的起点。翻检《大唐西域记》,玄奘在路过婆罗吸摩补罗国时,记载有一个“东女国”: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15]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
一般认为,东女国是隋唐时期藏族地区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尚处于母系氏族部落阶段。其地理位置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于阗以南,拉达克以东。
唐代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又一月过程,雪山,东有一小国,名苏跋那具怛罗,属吐蕃国所管,衣著与北天相似,言音即别,土地极寒也。”[16]
慧超的西行时间在公元723年至727年之间,比玄奘晚了近一百年,两人对女国的记载基本相同,可证明东女国的真实性。
《大唐西域记》称其为“东女国”,是因为玄奘在波斯国之后还记载了一个“西女国”:
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17]

已有研究者指出,“女国要么是纯是女人,要么是以女人为统治者,与中原地区迥然相异。所以,和中原地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别构成都完全不同的女国,对于中原地区的人讲,本身就蒙着一层神秘、异幻的面纱”[18]。

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
显然,玄奘本人并未亲自到过东女国和西女国,《大唐西域记》对东、西女国的描述应取材自当地人的记载与传闻,而玄奘对相关资料的选择与写定也包含着他本人的判断乃至偏见。
例如,玄奘对东女国“人性躁暴”的粗略概括,便不免隐含着一种时人对西域女国的“刻板偏见”。但恰恰是这种对不同文化的刻板偏见,容易成为故事的生发点。
其实隋唐时期仅在青藏高原范围内,就存在东、西两个女国。一个在青藏高原西部、葱岭之南,即《大唐西域记》《隋书·女国传》等记载的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另一个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高原,《旧唐书·西南蛮传》对此有记载。因为传说中已有西女国存在,青藏高原范围内的两个女国都被称作东女国。
从《唐会要》《旧唐书·东女国传》开始,史籍对川西高原女国风俗与政体的描述,便已明显地混入了《隋书·女国传》所记载的葱岭之南女国的文字;到《新唐书·东女国传》则进一步将两国混同为一国。[19]
笔者后文专论青藏高原西部、葱岭之南的东女国,因此选用《隋书·女国传》《大唐西域记》等资料。
对于这个神秘的东女国,《隋书·女国传》有如下记载:

《隋书》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
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
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
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20]

将《隋书·女国传》的女国与《大唐西域记》的东女国对读,我们发现两国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与风俗习惯都高度吻合,极有可能是同一国度。而且东女国并不是没有男人,只是男人“不知政事”“唯以征伐为务”。

胡胜《〈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知,在东女国参与的数次战争中,上战场的主要是男人,如有战亡,也多是男人。随后《隋书·女国传》对其丧葬、祭祀习俗的介绍,也丰富了我们对“女国”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女国传》所载的“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其实质是母系氏族部落实行的一种“双王政体”。
而《取经诗话》中“要识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及普贤”的诗赞,也隐约指出了“女人之国”的女王似有两位。这是否就是东女国“双王政体”留下的痕迹呢?
三、作为历史原型的东女国

从《大唐西域记》到《取经诗话》,从《西游记杂剧》《续西游记》到世德堂本《西游记》,我们发现史料、笔记对东女国“人性躁暴”、丈夫“唯以征伐为务”的记载,与取经故事对“女国”残暴习俗的描述,存在时隐时现的关联。
要证实东女国的“双王政体”与《取经诗话》“女人之国”的两位女王存在客观联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资料。
遗憾的是,由宋至明,有关《西游记》的成书资料大都佚失。《朴通事谚解》《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以及《佛门取经道场》载录的部分取经故事片段,仅能勾勒出流行于明代前期的平话系统《西游记》的概貌,却无法呈现更为细致的故事情节。
以《朴通事谚解》《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以及《佛门取经道场》为代表的资料,载录了一种西行历时六年的取经故事,统称平话系统《西游记》。它的故事情节与西行历时十四年的小说《西游记》存在较大差异,处于《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早期阶段。[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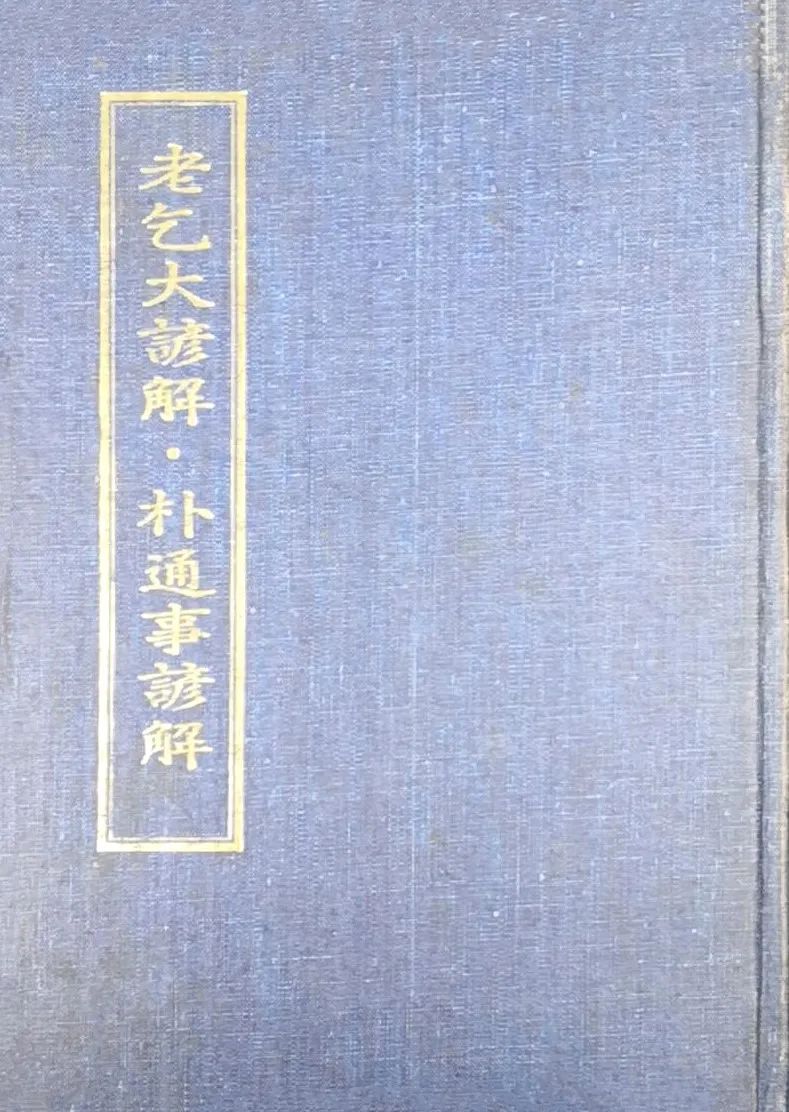
《朴通事谚解》
平话系统中也有“女人国”故事,可惜大都只留下一个简单的国名,如《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对此只有一句记载。在平话系统《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与女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现在似乎无从探考。
2019年春夏,笔者在北京大学古籍馆读到了两册《真经宝卷》。该宝卷细致讲述了唐僧师徒五众历时六年途经番邦十八国,到灵山拜佛求经最终修成正果的西天取经故事。该故事上承《大唐西域记》《取经诗话》之遗绪,下启世德堂本《西游记》之规模,还比已知的平话系统《西游记》更为完整丰富,是取经故事发展演化历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真经宝卷》所载的“番邦十八国”版取经故事中,唐僧师徒过“西凉国”,遭遇女王殿上求亲。其过程就比《西游记杂剧》、小说《西游记》所载内容更为惊险:

北大图书馆藏《真经宝卷》之西凉国
一程赶到西凉国,国中尽是女佳人。
养儿泉水成胎孕,尽养花娇美貌人。
女皇二人登龙位,聚集文官共武臣。
唐僧殿前来经过,女皇传旨召唐僧。
唐僧请上金銮殿,分宾坐定献茶津。
女皇请问何名姓,三藏开言说事因。
出身原是中华国,敕封三藏号唐僧。
君皇荐度孤魂众,命我西天去取经。
望皇早换通关牒,借条大路往西行。
女皇见说呼呼笑,唐僧休想到雷音。
我国祖传行旧例,来时有路去无门。
你今登殿为天子,我掌朝阳正宫身。
百年偕老同享福,度子度孙坐龙庭。
若道半声言不肯,刚刀杀你作泥尘。
晒干肉放香炉内,喷香扑鼻无价珍。
三藏回言忙便说,我是修行办道人。
三世九转真童体,再不将身染色尘。
女皇见说龙颜怒,说与唐僧你且听。
你若不来是由你,既来这里走无门。
要到西天参见佛,除非足下会腾云。
唐僧正在烦恼处,齐天大圣告唐僧。
我师在此成亲事,徒弟西天去取经。
取得经来归本国,复来参见我师尊。[22]

在《真经宝卷》中,面对女王的“死亡威胁”,师徒被逼无奈,用假亲脱网之计方得离开。结合“若道半声言不肯,刚刀杀你作泥尘。晒干肉放香炉内,喷香扑鼻无价珍”,世德堂本中西梁女国的“人肉香袋”果然是有来历的。

龚学渊绘《唐僧路过女儿国》
世德堂本《西游记》的“香袋”与《真经宝卷》的“香炉”如出一辙,只是《真经宝卷》细致解释了人肉的“制作流程”。
再结合《续西游记》的六处“割肉做香袋(囊)”,我们可以推知,世德堂本的写定者为了抹去西梁女国血腥、野蛮的一面,突出女王的娇艳袅娜,有意将“假亲脱网之计”提前。唐僧师徒由此就避免了与女王发生正面冲突,“人肉香袋”情节也由此刊落;但为了促使唐僧师徒提前用计,写定者又不得不借婆婆之口提前透露出“人肉香袋”一事。因此,小说涉及“人肉香袋”的文字失去了前后照应,原本完整的故事情节也由此出现脱落。
已有研究者指出,西梁女国故事之后的蝎子精,在本质上与女王是二而一的。她是《西游记杂剧》女王性格的横暴、色情部分的外化。写定者为净化女王,将杂剧中的同一形象一分为二了。[23]
现在看来,女王的横暴不仅保留在杂剧故事中,也保留在世德堂本写定前的小说故事中。写定者的净化对象主要是小说中的女王,而非杂剧中的女王。
另外,我们发现《真经宝卷》所载的西凉国故事,竟然有“女皇二人登龙位”的细节,明确指出西凉国的女王有两位。这不仅与《隋书·女国传》中东女国的“双王政体”相吻合,同时也为《取经诗话》中女人之国的诗赞“要识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及普贤”,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女人之国的女王也是两位,只是《取经诗话》言之不详,附会成文殊与普贤。
可见《大唐西域记》《隋书·女国传》所载的东女国,应是取经故事中诸多“女国”的历史原型。而世德堂本《西游记》的西梁女国故事则凝聚了从历史书写到文学想象的生成与演化过程。
最后,结合前引《隋书·女国传》所记载的东女国的“鸟卜”史料:
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

可知《取经诗话》“女王设斋”情节,其创作灵感应是源自东女国的“鸟卜”习俗。女王所言“尽于地上等处收得,所以砂多”等语,实质是代鸟而言的人物化自述。斋供之后,法师
留诗:“女王专意朱(设)清斋,盖为砂多不纳怀。竺国取经归到日,教令东土置生台。”[24]

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747号鸟卜文书
“生台”是禅林用以置生饭而施于鬼神或供禽兽啄食之台案。禽兽啄食正与“鸟卜”吻合,可见法师是听懂了女王代鸟而言的自述的。
《取经诗话》的编纂者,正是利用了类似《隋书·女国传》中东女国的“两王政体”及“鸟卜”等史料,编出了神秘的“女人之国”故事。太田辰夫注意到了生台的施食供养功能,可惜未能与“鸟卜”史料结合,便认为生台与女人国或其女王没有直接关系。[25]
由于《取经诗话》在当时可能是配图演说,缺失了人物图像与“鸟卜”知识,“女人之国”的设斋故事方才显得荒诞不经。
四、“女国”故事的生成与传播

在世德堂本《西游记》写定前后,仍有丰富的取经故事在民间说唱、流传。这些未经整理写定的取经故事,并未因小说的写定与出版而彻底瓦解消失,反而是与仪式文献结合,通过传抄与演述在民间流传,因此在历代的传播中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概貌。

《众喜粗言宝卷》之《取经因由》
前文提及的《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佛门取经道场》及《真经宝卷》即是如此。清代长生教经卷《众喜粗言宝卷》记载有一篇《取经因由》,这篇一千余字的《取经因由》概述了一种独特而完整的取经故事。其中也提到了西梁女国:
又到元会县,过八百里通天河,此河鹅毛难浮,芦花亦沉。又到子母河,若吃此河水,男女俱要成孕。行过西梁女国,此国有女无男,吃城中双井水为孕,若见男人,众割肉为香袋。[26]

《取经因由》所记载的取经故事在关目上与世德堂本相近,但在故事细节上又有较大差异,保留有部分世德堂本写定前的取经故事。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考论,兹不赘述。[27]
但《取经因由》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仍然点出了西梁女国“众割肉为香袋”的故事细节。可见在小说写定前的取经故事中,“割肉为香袋”的确是西梁女国故事的情节高潮。
那么西梁女国的“人肉香袋”究竟是否属实?该故事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辛?细读《隋书·女国传》所载相关史料,无论是《真经宝卷》的“晒干肉放香炉内”,还是《续西游记》、世德堂本《西游记》及《取经因由》的“割肉做香袋”,其实质都是对东女国的特殊物产——麝香,以及东女国的特殊葬式——翁棺葬的一种文学想象。

瓮棺葬
公元7—10世纪,吐蕃与中亚之间的商贸往来非常密切,这条商路被称为“麝香之路”。麝香作为吐蕃的主要商品,对于大量使用香料的中亚及西方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通过海路与陆路分别运往西方,这条“麝香之路”成为吐蕃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渠道。[28]
也有研究者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指出,在唐代至少八个道有向朝廷进贡麝香的记载,但是,最集中、普遍地向朝廷贡麝香的则是陇右道、剑南道、山南道西部三地。其所在位置大都在环青藏高原周围地段,或者本身就处在高原区富产麝香的地带上。待元朝统一藏族地区,在青藏高原上设立驿站后,麝香主要就通过驿道进入中原。[29]
前文已引,地处青藏高原、临近吐蕃的东女国就出产麝香。麝香是鹿科动物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是一种较名贵的药材及香料。
麝香的传统采集方式是杀麝取香,即切取带毛香囊,直接干燥化处理而成毛壳麝香。除去毛壳后的净香称为麝香仁,野生麝香仁呈紫黑色大颗粒状及棕褐色或黄棕色的粉末状。灼烧麝香仁粉末,初则迸裂,随即熔化膨胀起泡沫似珠,香气浓烈四溢。[30]

麝香仁与毛壳麝香
麝香仁的制作和使用方式就与《真经宝卷》中女王所说的“刚刀杀你作泥尘”,“晒干肉放香炉内,喷香扑鼻无价珍”高度吻合。实际上,女王应是在用麝香仁的制作及使用方式,来威胁拒不招赘的唐僧。
这种联系麝香的推论,是否有文献依据呢?幸运的是,笔者在如不来室主人所藏的《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钞本中,找到了用男子肉做麝香的西凉国故事:
师徒来上路,同至西凉国。此国无男子,尽是女人列。大国男子肉,女国做香麝。女王闻师至,拱手相迎接。接至金銮殿,待为王家客。长老求玉笔,女王换文牒。尊师为帝王,女王愿为妾。长老心不喜,要吾用计策。吾用脱身计,才把女王别。[31]

《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所记载的西凉国故事,正与《真经宝卷》所载相同,都是女王殿上求亲、孙悟空用计脱身。所谓“大国男子肉,女国做香麝”,叙述更直白:西凉国的女人竟然把男子的肉做成类似麝香一样的香料!

如不来室主人藏《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
室主人藏《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 8b3ce2ca-0623-0626"="">室主人藏《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 399dcdda-0612-0615"="">室主人藏《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 uploaded="1" data-infoed="1" data-width="1080" data-height="1006" data-format="png" data-size="1670951" data-phash="A232AB398E6AEB98" data-source="outsite" outid="undefined">但是,男人毕竟不是雄麝,男人的皮肉及腺体也无法做成香料。那么人肉和麝香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其实,东女国这种将人肉放置在容器内的做法,除了受麝香制作及使用方法的影响,还与东女国的独特葬式——二次葬有关。二次葬,又称洗骨葬、迁葬、再葬等。其形式复杂多样,但核心是对死者的尸骨进行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安葬。前引《隋书·女国传》对东女国的二次葬有简单描述:
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

东女国的二次葬先后经历了瓮棺葬和土葬两个阶段。“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是明显的瓮棺葬,它在形式上与“刚刀杀你作泥尘”“晒干肉放香炉内”正好相似。这本是东女国对死者尸体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是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

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概而言之,女国国王之所以用“刚刀杀你作泥尘”“晒干肉放香炉内”这种独特方式来威胁唐僧,主要是因为东女国既有“杀麝取香、去壳烧粉”这种制作麝香的物质文化,又有瓮棺葬这种“剥皮削骨,置于瓶内”的独特丧葬习俗。
这些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与风俗习惯,才是使麝香与人肉发生关联的现实基础。女王的思维与言说方式既在普通读者的意料之外,又在原型国度东女国的情理之中。
结合前文考论,我们大致探清了“人肉香袋”故事的生成过程。在以女性为主导的东女国,男人“不知政事”“唯以征伐为务”,因此在战争、打猎等活动中,死亡的仍以男性为主。在丧葬习俗上,东女国实行的是二次葬,其中瓮棺葬这种“剥皮削骨,置于瓶内”的特殊葬式,恰与东女国“杀麝取香,去壳烧粉”的麝香制作及使用方法存在相似之处。

暗花罗绣香囊(南京北宋大报恩寺塔地宫出土)
而东女国又刚好出产麝香,误解或便由此生成。在漫长的“麝香之路”上,渐渐传出了西凉国女人割男子肉做麝香的恐怖故事。该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其一一对应且真实存在的物质文化与风俗习惯,这应是该故事长盛不衰的奥秘之一。
厘清“人肉香袋”与西梁女国的关系后,再回头看世德堂本《西游记》第四十八回。灵感大王作法冻住通天河,引诱唐僧踏冰过河,此时唐僧与陈老有一番对话:
三藏问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陈老道:“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数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32]

与西梁女国的贸易往来竟有百倍之利,买卖人“不顾生死而去”的那条路,正是“麝香之路”在小说中的投影。至此,我们将“女国”故事的产生及传播与“麝香之路”联系起来,这为学界关于取经故事与“麝香之路”的关系推论,增添了一组新的证据。[33]
结 语

隋唐时期真实存在的东女国是取经故事中诸多“女国”的历史原型。史籍与笔记对东女国“人性躁暴”的刻板偏见,对东女国男子“唯务征伐”的片面认知,以及对“瓮棺葬”这一特殊葬式的文化隔膜,使得东女国成为故事的生发点。

侯冲、王见川主编《〈西游记〉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
东女国出产麝香的物产状况、“杀麝取香,去壳烧粉”的香料制作及使用方式,又使东女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这些文化要素在漫长的“麝香之路”上聚合成人们猎奇的谈资,并在生成与传播中逐渐变形,最终演化成取经故事中西凉国女人割男子肉做麝香的恐怖故事。再经世德堂本写定者的删改与调整,这才留下了西梁女国那似不可解的“人肉香袋”之谜。
由东女国真实存在的麝香制作方式及瓮棺葬习俗,到《真经宝卷》《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中西凉国那令人悚然的“刚刀杀你作泥尘”,“大国男子肉,女国做香麝”,再到《续西游记》《取经因由》中西梁女国那血腥、残暴的“割肉做香袋”,最后到世德堂本《西游记》删改后残存的两处“人肉香袋”,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探知“女国”故事从历史书写到文学想象的生成、传播及演化过程。

《西梁女国故事的生成与演化考述》
从这个角度看,《西游记》不仅堆叠着十分复杂的故事层次,也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意蕴,至今仍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富矿。我们在文本的断层背后探寻故事演化轨辙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古典小说历久弥新的魅力。
附记:本文前后幸得侯冲教授、王见川教授、胡胜教授、许蔚副教授、黄仕忠教授、李小龙教授以及《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老师的指点;许蔚副教授还向笔者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注释:
[1] 胡胜:《叠加的影像——从宾头卢看玄奘在“西游”世界的变身》,《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
[2] 王子今:《“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3] 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王萍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1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9-133页。
[4] 胡胜:《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
[5] 吴承恩:《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654页。
[6] 同上书,第662页。
[7] 关于《续西游记》,刘荫柏先生认为,《续西游记》所续的不是吴承恩写定的百回本的《西游记》,而是元人的平话《西游记》。参见刘荫柏《〈续西游记〉作者推考》,《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张颖、陈速认为:“元明或元明之前,在现存片段的古本《西游记平话》以外,必定另有一部今尚未见的古本《西游记》章回说部存在。现存之一百回本《续西游记》,正是那部比《西游记平话》更罕见之古本《西游》或《西游》前记的一种续书。”参见张颖、陈速《古本〈西游〉的一部罕见续书——〈续西游记〉初探》,张颖、陈速校点《续西游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96—797页。笔者认为《续西游记》所复述的取经故事,在取经团队、西行时间以及西行诸难上均已向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情节结构靠拢,仅部分故事略有差异,所以《续西游记》所续的并不是平话系统的《西游记》,而是略早于世德堂本的某个佚本《西游记》,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
[8] 张颖、陈速校点《续西游记》,第444—451页。
[9] 蔡铁鹰编著《西游记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06—407页。
[10] 同上书,第84—85页。
[11]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65页。
[12] 同上书,第458页。
[13]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7页。
[14] 王子今:《“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15]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409页。
[16] 同上书,第409页。
[17] 同上书,第943页。
[18] 韦强:《论“女儿国”故事的传承衍变和两个系统》,王萍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14辑,第127页。
[19] 参见石硕《〈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篡乱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20] 魏徵等:《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0—1851页。
[21] 参见左怡兵《斋供科仪所载取经故事与平话系统〈西游记〉关系考》,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08—127页。
[22] 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册)·真经宝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259—260页。本文所引字句,参校了《中国常熟宝卷·长生卷》以及苏州戏曲博物馆藏的《西藏宝卷》,特此说明。
[23] 参见胡胜《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
[24] 蔡铁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84页。
[25] 参见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王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
[26] 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6册)·众喜粗言宝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606页。
[27] 参见左怡兵《转录、钞撮与重述:〈众喜宝卷〉所载〈取经因由〉的文本生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28] 参见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
[29] 参见尹伟先《青藏高原的麝香与麝香贸易》,《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30] 参见姚荣林、刘耀武主编《中药鉴定技术》(第3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31] 经卷引文的影印件详见侯冲、王见川主编《〈西游记〉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第573-574页。从整体上看,《南无齐天大圣新降真经》文字简省,故事情节与世德堂本《西游记》基本趋同,但仍有部分故事细节与世德堂本有所出入,并非直接改编自世德堂本,而是保留有部分早于世德堂本的取经故事内容。相关研究可参看许蔚《〈西游记〉研究二题》,《华人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
[32] 吴承恩:《西游记》,第594页。
[33] 蔡铁鹰在探讨猴行者的文化来源时,认为“(麝香之路)这条通道为《取经记》的密宗色彩提供了一个解释,也为《摩罗衍那》从藏区进入敦煌并影响《大唐三藏取经记》提供了一种解释”。参见蔡铁鹰、王毅《〈西游记〉成书的田野考察报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