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蒲润洲 赤城文史一角
2024年岁末应贺宝贵老师之约,我写了《赤城莜麦、莜面与文化》,供《张家口莜麦莜面文化简史》选用。完成了贺老师交给的任务之后,我感到稿子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就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查资料、访专家,果然又有不少新的发现与收获。现将其整理为《续赤城莜麦、莜面与文化》,发布于公众号“赤城文史一角”,希望朋友们予以批评指正为盼。
一首嵌有"麦"字的古诗
我在《古镇独石口》查到这样一首诗,叫做《登独石城楼》:“高危楼堞塞云横,有客褰裳极望情。旧卫当年弛锁钥,荒陵何处识簪缨。烟迷上谷东庄柳,日下居庸北路城。今古销沈无限事,山青麦秀鸟啼声。”
诗的作者是张曾炳。张曾炳,字于丙,安徽含山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乾隆《赤城县志》主纂。随后我又查了《赤城县志译注》和《赤城历代诗词歌赋选》,也都载有这首诗。

独石口城楼(赵望云)
诗的尾句“山青麦秀鸟啼声”,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这个“麦”字是指莜麦,还是指小麦呢?我知道独石口种莜麦,却不知道独石口种小麦。我母亲是独石口人,上世纪30年代出生,她见过独石口种小麦。然而,母亲与张曾炳的年代相距遥远,不能证明乾隆年间也种过小麦。我又去书上找这句诗的注释,《赤城县志译注》译作“古往今来多少事情都消沉了,只有大自然还是那样,山青麦秀飞鸟啼鸣。”《赤城历代诗词歌赋选》译作“古往今来多少事情都消逝了,只有山青麦秀飞鸟啼鸣。”后书是不是从前书演化来的,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它们都没说明“莜麦”还是“小麦”。我窃想:如果张曾炳诗中写的就是莜麦的话,那独石口种莜麦至少有二三百年了。
两个莜面莜麦革命故事
在《赤城莜麦、莜面与文化》中,我引用过两个群众用莜面招待八路军的故事。今天我又引用了两个与莜面莜麦有关的革命故事。因故事发生在赤城周边县份,我建议贺老师补充到这些县份去。而贺老师却不假思索地说:就在你文章里体现,是你挖掘出来的,不用往其他县里边儿搁。于是我根据原著将这两个故事简写如下:
故事一:1944年4月10日早7点左右,在龙崇宣联合县境内的猴儿山上,八路军与日伪军展开一场激战。霍家洼村的群众听着山上激烈的枪炮声,心中非常惦念与敌鏖战的子弟兵:战斗已经持续4个多小时了,不能让子弟兵们饿着肚子作战呀!他们做了20多斤莜面饼子、焖了80斤山药蛋(土豆),因猴儿山东坡有日伪军严密封锁,就绕西沟攀崖将食物送到亲人们手上。(见《回忆猴儿山战斗》,作者段苏权)
故事二: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军队到清水河一带抢粮,我们的民兵将地雷埋在了莜麦码子底下。第二天敌人赶着10多辆大车,直奔莜麦地的莜麦码子而来,在搬莜麦码子时地雷爆炸了,几个敌兵被炸死,其他的吓得掉头就跑。敌军官认为没有地雷了,喝令敌兵继续搬莜麦码子,谁知又有几颗地雷爆炸了,敌人只好丢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了。(见《清水河风雷》,编者张清亮)
于哥谈麻地沟莜面
据1992年版《赤城县志》记载,麻地沟莜面窝窝:白、细、薄、筯。我通过微信问过赵富智老兄:赵哥,麻地沟莜面窝窝为什么出名,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他回答说:土壤适合,黄土板地。稍后,县文旅局原局长温广智告诉我:独石口麻地沟莜面品质最好,比坝上的好多了。于风云局长曾在那里当过民办教师,说是用凉水一拌就能吃,且好吃易消化、不烧心。
他说的于风云局长,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并一直称呼其于哥。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和于哥都在县文化馆,他专职搞摄影,我埋头搞创作,闲暇时我就钻进暗室看他洗相。有一年,他带我到北京出差,我买西服时上了当,他帮我一起狂追骗子。在京城狭小的胡同内,我俩与骗子PK马拉松,结果骗子输给了我俩。那时真是年轻啊!我二十出头,于哥三十出头。这件事儿让我对于哥一直心存感激。后来他调县报社当记者,又和我父亲一起工作。他曾担任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体局局长。扯远了,打住!之前我知道于哥是独石口人,但不知道他在麻地沟教过书。恰好我有他微信,随时可以采访。

八十年代与于哥合影
我问:于哥,听说麻地沟的莜麦莜面好,特别是莜面窝窝还上了县志。你在麻地沟教过书,知道这里的莜麦莜面为什么好吗?
他回:麻地沟土壤好,土壤肥沃,气候半高山,适宜种植莜麦、山药。产出的莜麦粒满粒大,干净。磨出面粉,面质好色质也好。独石口一带数麻地沟莜面好,同时莜麦产量高。
我问:麻地沟有什么关于莜面的故事与传说没有?或者你经历过什么与莜面有关的故事没有?
他回:每年秋收完后,大队派专人给我精工细做,专门为我磨300多斤莜面,用大口袋装好放到凉屋里,够我吃一年的。一天三顿莜面,百吃不厌。礼拜天同学们经常到我校聚会吃莜面,山药酸菜汤。所以到现在我也离不了莜面,这几年来海口也是离不了,好这一口,从网上买个上百斤。
我又问:于哥,我也特爱吃莜面。赤城人实在、厚道、耿直,我看跟吃莜面有很大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
他又回:大队给我近一亩地,每年派人给我种上山药,剩下点点儿豆角,下午放学锄锄。秋天和学生起1000多斤山药,放到窖里够我一年吃了,吃不了还卖一部分。顿顿尽莜面也不行,所以和山药一起做山药窝窝、山药丸子,等等。
有关山药莜面的话题
我还就山药莜面的话题,向“赤城历史文化研究群”的专家请教过,参与讨论的有沙志强、张桂亮、孙登海、温广智等老师。
有关山药挠子的叫法。我说:我80年代去镇宁堡下乡,听人把山药挠子叫作山药秧子、扒搂柴。沙老师说:红河叫山药丝子;黑河叫山药窝窝,团成四喜丸子那么大,里面加上盐、花椒粉和葱花,可当干粮吃,也可蘸汤吃;丰宁叫山药丸子。孙老师说:也有叫喜鹊窝的,沙老师说:对,沽源小厂一带就这个叫法。
有关山药莜面的做法。沙老师是《赤城民俗》执笔人之一,该书收录了莜面系列主食10类,莜面山药系列主食7类。他说:山药莜面饭的分类与叫法,所依据的就是形状、擦床类型以及制做(蒸制)过程。擦床分三种:倒马蹄口、圆孔翻花口、斜切翻菱口。斜切翻菱口是擦山药丝的。圆孔翻花口在黑河又叫磨床子,山药去皮用磨床细细擦出,拌入莜面搅匀,摊在铺有屉布的篦子上蒸熟,用铲子切成块蘸汤吃,这就是红河叫的山药羊板。因为山药沫子和擦床铁制品起化学反应,这羊板很黑,极像羊圈起出的羊粪块,就叫羊板吧!黑河和丰宁一个名字,叫山药糕。山药挠子就是用倒马蹄口擦床擦出的丝,过水去掉部分淀粉,拌上莜面抓成自然形状(约大山里红大小),平铺在屉上蒸熟蘸汤吃。掺上磨床擦出的山药丝子,不过水和入莜面,叫毛毛饸饹。

莜面山药鱼(泉君老师提供)
有关山药莜面的分布。桂亮老师担任基层领导多年,对各乡镇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龙关人说的山药擦擦和山药洋板是一回事儿。莜面与山药组合,除了后城、东卯几个乡镇吃的少点,可以说是遍布全县。大的分类:就是生山药和莜面组合与熟山药和莜面组合。小的分类:就是因生山药的形状不同与莜面组合。莜面和山药坝上是主产区,不过山药莜面饭是坝头的崇礼、赤城发扬光大的。坝上吃的花样差点儿。
有关山药莜面的种类:温局对龙关的情况较为熟悉。他说:赤城县的莜面特色是与土豆(山药)做混合饭,尤其龙关做法最丰富,有一个师傅(名字忘了)能变着花样儿做近30种,有山药鱼子、山药暄饼、山药擦擦、山药洋板、毛毛饸饹等。其实是过去家里人口多,粮食少,而山药产量较大,与净米、净面搭配着吃,以便充饥。这也是粮食困难,逼着人们发明各种吃法。人家坝上莜面多,多吃净面傀儡、搅拿糕,好吃但费面。
……
我从小就喜欢吃莜面,知道它非常有吸引力,但没想到写莜面也这么有吸引力,让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今后我将继续关注莜面、发掘莜面,争取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尊重原创 是人之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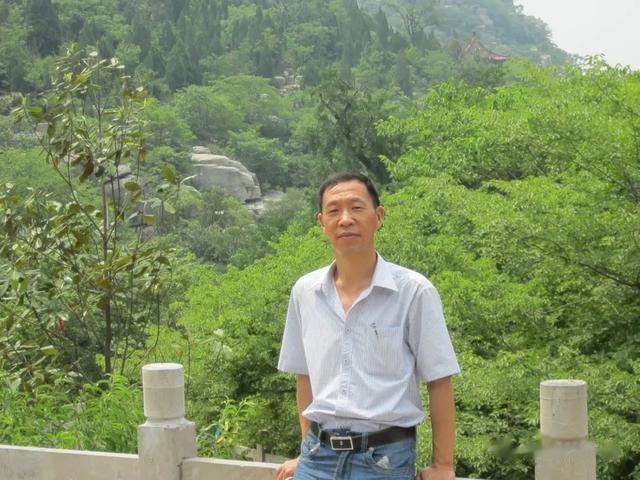
蒲润洲,60后,祖籍怀来,生于赤城。喜欢文学与文史,偶有小文见诸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