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对原文的白话翻译及创作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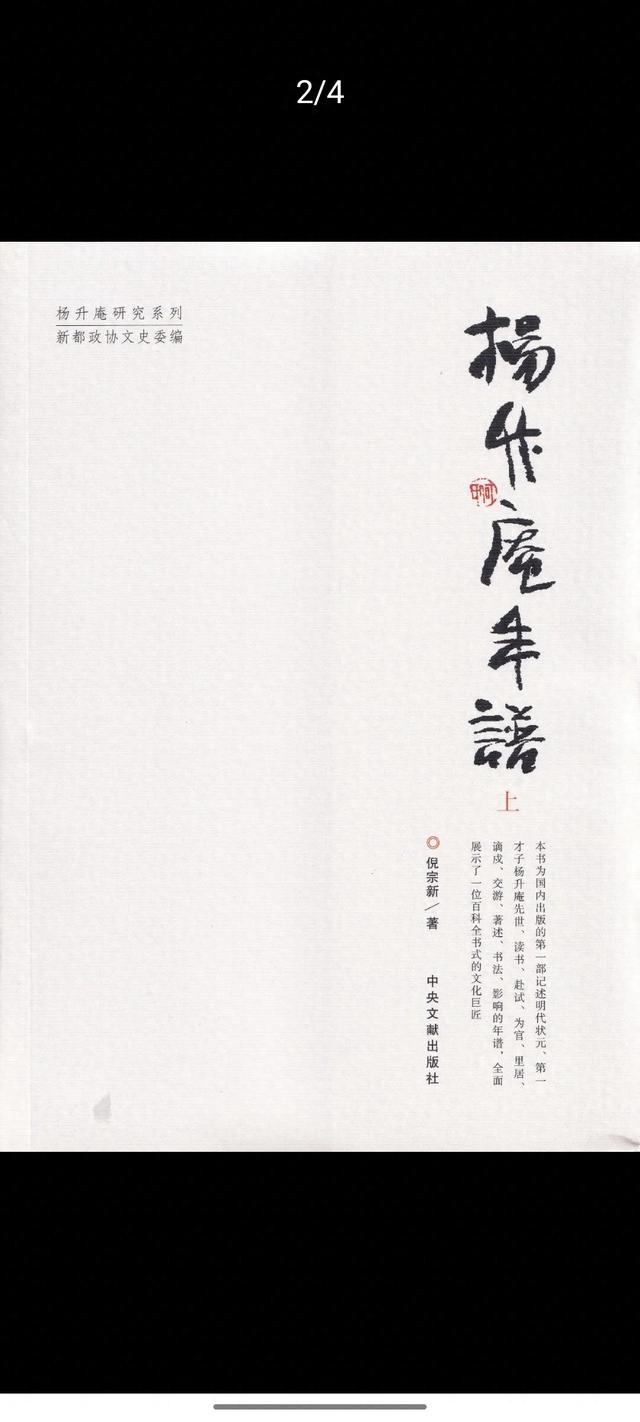
白话翻译
《全蜀艺文志》在明朝有嘉靖、万历两个刻本,均与《四川总志》一同刊印,从未单独发行。嘉靖二十四年的版本是最早的刻本,卷首收录了嘉靖二十年巡抚刘大谟的《重修四川总志序》。序中提到:“我与合川的王侍御,趁着杨慎(升庵)因公事之便、杨名(方洲)赋闲之际,再次征召他们,共同编纂此书。恰逢侍御谢狷斋到来,他也乐于支持,于是不到两个月,便完成了编纂。随后,又委托周宪副木泾、崔佥宪楼谿重新整理编集。”接着是巡按御史谢瑜的《重修四川总志》序,其中写道:“巡抚刘大谟(东阜公)倡议修志,前巡按王元正(合川王子)响应,于是礼聘杨慎(升庵)、王舜卿(玉垒)、杨名(方洲)分工撰写,仅用两个月便完成初稿。”(此序也见于嘉靖《四川总志》卷末,但标题为《重修四川总志后序》)之后是杨慎的《全蜀艺文志序》,他写道:
我的父亲在翰林院时,曾收集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李光的《固陵文类》,以及成都丙、丁两《记》和《舆地纪胜》等书,广泛搜罗,计划编纂《蜀文献志》,但未能完成。如今我看着父亲的遗稿如新,感慨他的遗愿未竟,而自己已被贬南方十八年。嘉靖辛丑年(1541年)春,我因军务暂回故乡。巡抚刘大谟(东阜公)礼聘旧史官王舜卿(玉垒)、杨名(方洲)编修《四川总志》,并让我负责“艺文”部分。于是我翻检旧书箱,查阅随身文稿,参考近期地方志,又采集各家文献。筛选精华,删减冗余,拾遗补缺,剔除糟粕……最终博采约取,编成七十余卷。编纂工作在静居寺的宋、方二公祠进行,始于八月乙卯日,终于九月甲申日,历时二十八天完成。虽然速成令人惭愧不如汉代刘安的捷才,也缺乏《吕氏春秋》悬赏求改的严谨,但我仍委托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交付刻印。……嘉靖辛丑年九月十五日,贬居博南山的成都人杨慎作序。
综合以上三篇序言可知,嘉靖《四川总志》由王元正、杨名、杨慎共同编纂,其中杨慎负责“艺文”部分,仅用二十八天便完成七十余卷的《全蜀艺文志》,其编者身份毋庸置疑。其后王元正的《全蜀人物志序》详细记载了修志过程:“于是派遣使者,以礼聘请杨名(方洲)从遂宁先至,杨慎(升庵)从新都继至,我(王元正)从茂林最后抵达,借住宋公祠,分部门工作。杨名约一个月完成任务离开,杨慎约两个月完成后离开,我则用了三个月才告成。……此志由巡抚刘大谟与巡按王元正发起,不久王元正北上,谢狷斋接任巡按,协助完成。最终缮写编订为二十六卷,立论十三篇,希望借助高明之士,启发我们的愚钝。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日,玉垒山人盩厔王元正撰。”
王元正提到“杨名约一个月完成,杨慎约两个月完成”,与杨慎自述的“二十八天告成”略有出入,可能是王元正记错了时间,实际应为“杨慎约一个月完成”。此序所述为嘉靖二十年的初稿,未提刊刻。明代何宇度在《太平清话》中称:“《全蜀艺文志》为杨慎所编,搜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近于尽,可谓广博。可惜过于繁复,原刻本存于藩司,现已不存。”但何宇度作为明神宗时期的人,所谓“刻在藩司,已不存”应指嘉靖二十四年本。实际上,嘉靖版《全蜀艺文志》是《四川总志》的一部分,何来“二书”之说?嘉靖二十年的初稿未经刊刻便转入重编,这一点刘大谟的序已说明。王元正序提到初稿“总二十六卷,立论十三篇”,而《太平清话》称“仅《艺文》一卷为杨慎所选”,说明作者见过王元正的初稿,反而是何宇度可能未见过这两部书。何宇度提到“刻本不存”,推测他所见的《全蜀艺文志》可能是抄本,因此脱离《四川总志》单独流传也属正常。
嘉靖《四川总志》卷末的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进一步补充了编纂细节……
文章创作:《杨慎:贬谪岁月里的文化守灯人》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西南边陲,一位被贬谪的才子用一支笔点燃了巴蜀文化的火种。他叫杨慎,因“大礼议”之争被流放云南,却在逆境中扛起了编纂《全蜀艺文志》的重任,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闪耀着文明之光的典籍。
嘉靖二十年,巡抚刘大谟决心重修《四川总志》,他深知,要完成这部巨著,离不开杨慎的才学。此时的杨慎已在贬谪中度过了十八年,但他的文名与学识依然为世人敬仰。刘大谟派人礼聘杨慎,邀请他参与修志,而杨慎欣然应允。他带着父亲未竟的遗愿——编纂《蜀文献志》的手稿,从流放地匆匆赶回四川,投身于这项文化工程。
在静居寺的宋、方二公祠里,杨慎与其他学者开始了紧张的编纂工作。他负责“艺文”部分,任务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筛选精华,梳理巴蜀大地的文学脉络。白天,他翻阅历代文集、地方志和金石铭文;夜晚,烛光映照着他伏案疾书的身影。二十八天,他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七十余卷的《全蜀艺文志》,将秦汉以来的巴蜀文章、诗词、金石铭刻熔于一炉,仿佛在蛮荒之地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这部著作的编纂过程充满艰辛。杨慎不仅要面对资料的匮乏,还要在贬谪的屈辱中保持心境的澄明。但他以“择其菁华,褫其繁重,拾其遗逸,翦彼稂稗”的严谨态度,将巴蜀文化的瑰宝一一打捞,让那些险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字重见天日。他在序中写道:“悼手泽之如新,怅往志之未绍。”这不仅是对父亲遗愿的追思,更是对巴蜀文化的深情守望。
《全蜀艺文志》的诞生,不仅是一部地方志的修成,更是一个文化奇迹。它如同暗夜中的明灯,照亮了西南边陲的文明之路。杨慎以一人之力,在贬谪的岁月里为四川留下了一部“文化史记”,让后世得以窥见巴蜀文学的璀璨星河。正如他在峨眉山题下的“与造物游”,他用文字与时光对话,将个人的苦难化作了文化的永恒。
如今,当我们翻开这部典籍,仿佛还能看见杨慎在烛光下挥毫的身影。他用生命的坚韧与学识的渊博,证明了真正的文人从不被命运击垮——他们的文字,终将穿越时空,成为文明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