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中的“书法”是指史家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书法”也称为史笔,例如朱熹(紫阳先生)撰《通鉴纲目》,其笔法被称为“紫阳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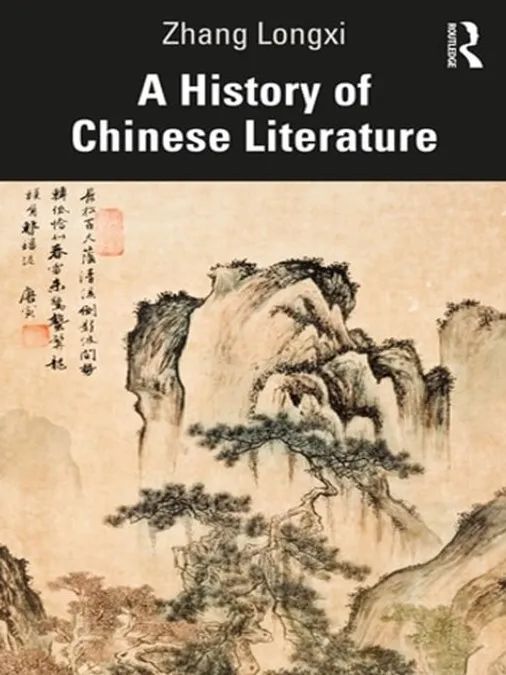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在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南宋部分,我们看到patriotic (爱国) 这样的字眼被多次使用。笔者粗略点算了一下:patriotic至少出现了八次。
爱国,是文学史书写中比较特殊的话题,例如,屈原一般被视为“爱国诗人”,不少文学史书强调:屈原深爱楚国,他抗拒秦国﹔“爱国”诗篇弥足珍视。
秦楚相争,却是秦国结束战国时期大分裂诸国互相攻杀的局面,所以,若论统一的历史意义,秦国开创大一统的崭新局面也有正面意义,例如: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南宋人面对北方金人入侵,他们的仇金之作获得一般文学史家的表彰,例如:陈与义、陆游、辛弃疾、范成大、文天祥等人在文学史书中都以“爱国”见称。“爱国”似乎成为一种衡量和评价标准。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Tetsumi MURAKAMI)指出: “忧国之词”在南宋出现大量佳作(村上哲见撰;杨铁婴、金育理、邵毅平译《宋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页371)。

村上哲见《宋词研究》

文学史常为一国之史(国别史),伴随西式教育的兴起而在中国出现(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当时中国正受外国外族侵凌,因此,重视文学史的“爱国”意义正符合时代所需。
然而,文学史如果涉及民族矛盾,情况往往变得复杂,例如,南宋人仇视金国人(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金人的后裔是满族人,而满族人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那么,当今的文学史书有必要再推衍“灭金、排满”之论吗?历史的问题应当如何对待?
此外,中国文学史如果被写成“汉族文学史”,妥当吗?
民初,周作人(1885–1967)将文学现象置于“言志”“载道”的图式之中,而胡适(1891–1962)书写文学史选择以“白话”为主轴,那么,如果文学通史以“爱国”为中心,也是不足为奇的吧?然而,“爱国”就是爱汉族人之国而排斥外族吗?
鲁迅(周树人)写过一本《汉文学史纲要》。“汉文学”三字令人猛省:中国不是只有汉族、汉字、汉语。那么,撰写中国文学史,如果只关注“汉文学”,周全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图书馆藏)
本文从细致的文本分析(practical criticism)出发,尝试检视一些唐、宋作家的仇外心态,然后尝试讨论文学史书怎么对待“仇外・爱国”。“爱国”的篇章,为文学之最上乘?

宋朝陈与义被视为爱国诗人。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一书第十二章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Northern to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论及陈与义,并引录以下诗篇(英译本):
The imperial court had no plan to defeat the enemies,
So the beacon fires shone on the royal palace at night.
First surprised to hear war horses running in the capital,
Then the flying dragon ran in distant sea to hide!
The lonely servant has frosty hair three thousand feet long,
Flowers are blocked by ten thousand mountains and more.
It’s lucky we have Magistrate Xiang in Changsha,
Though tired, his soldiers still confront the dogs of war. (p.242).
原诗是陈与义《伤春》(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713录有此诗),内容如下:

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平戎”意思是平定戎族,就是大金国人。诗末“疲兵敢犯犬羊锋”,张教授译成:Though tired, his soldiers still confront the dogs of war. (p.242)
对照原诗和译文,我们发现: the dogs of war相当于原诗中的“犬羊”。The dogs of war可解为“佣兵”。
此外,在莎士比亚戏剧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 ) 有这样的说法: Cry ‘Havoc!’ and let slip the dogs of war, … 。意思是:让战争之犬四出蹂躏!
可是,陈与义原诗中的“犬羊”是旧时对外敌的蔑称,而不是佣兵或者普通的“战争之犬”。换言之,“犬羊”是个文化负载词 (culturally-loaded item),有特定的文化意蕴。
陈与义《伤春》诗所写“犬羊”,是用来蔑称入侵中土的金国兵。下文,笔者举实例说明唐人、南宋人怎样以“犬羊”入诗。

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犬羊”,视乎语境,可以指不同的对象,例如,唐朝李峤(644-713)《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全唐诗》卷五十七)开首四句是:
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
可见李峤笔下的“犬羊族”和华夏民族(居于“夏疆”内)对峙。此外,杜甫(712-770)《寄董卿嘉荣十韵》也写“犬羊”:
海内久戎服,京师今晏朝。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黄图遭污辱,月窟可焚烧。
会取干戈利,无令斥候骄。
居然双捕虏,自是一嫖姚。
落日思轻骑,高天忆射雕。
云台画形像,皆为扫氛妖。
“犬羊曾烂漫”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杜诗详注》
清人仇兆鳌(1638-1717)《杜诗详注》卷十四引黄鹤注,谓:“当是广德二年秋作。”(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1167)。
广德这年号(763年7月至764年),在唐朝历史上只使用了一年多。当时,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西域与中原隔绝。由于西域的士兵不知道唐朝中枢已经改元“永泰”,他们仍然使用广德年号,有文物显示他们使用该年号到“广德四年”(《中国考古集成: 魏晋至隋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939)。

广德年间,杜甫在阆州(今四川省),他大概听闻了吐蕃入侵河西走廊之事。公元763年,吐蕃军队趁唐朝内乱之际又攻入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版,页450)。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版。
在“犬羊曾烂漫”句下,清人浦起龙(1679—1762)的解说提到“犬羊”,他说:“谓吐蕃。”(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页745)。
另一位注杜名家仇兆鳌的意见如何?
仇兆鳌解说杜甫《伤春》:“中叙吐蕃之乱,勉其敌忾也。乱后事冗,故日晏退朝。尝胆腰剑,欲报污辱。月窟在西,吐蕃巢穴也。”(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页1168)。
杜甫很可能知悉“月窟”为吐蕃盘踞之地。杜甫这首《寄董卿嘉荣十韵》的“犬羊”当指吐蕃。
“犬羊曾烂漫”, 美国学者Stephen Owen 翻译为Those dogs and sheep ran amok。然后在注释中说明句义是the Tibetan occupation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De Gruyter Mouton, 2015。书中编号:14.1)。
所谓the Tibetan occupation, 是指: 吐蕃人的势力范围。吐蕃当年常居于今日的西藏(Tibetan)之地,包括四川西部和甘肃、陕西、新疆部分地区。
总之,Owen用的是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直译后再用译注辅助说明:译文的语义甚是含糊,而译注标明了专指对象。
唐朝末期,吐蕃的势力开始衰落,但是,直到北宋时期,吐蕃各部落仍然与北宋发生冲突。

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2010 年版。

“犬羊”未必专指吐蕃。在其他历史语境中,“犬羊”也泛指西方的戎人。
杜甫和哥舒翰(?-757年)的作品中,都以“犬羊”指称“西戎”。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全唐诗》卷230。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编号:21.31)之一:
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To Xiao Pass and Long’s waters the imperial army enters,at Kokonor and the Yellow River frontier clouds roll away.The Pole Star increasingly worries about the aura of dragon and tiger,the Western Rong cease to unleash their dog and sheep war-bands.(Stephen Owen, p.386 )

《唐声诗》,任中敏著,张之为、戴伟华校理,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版。
此外,哥舒翰《破阵乐》写攻破“西戎”:
西戎最沐恩深,犬羊违背生心。神将驱兵出塞,横行海畔生擒。石堡岩高万丈,雕窠霞外千寻。一喝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
哥舒翰这作品见于任中敏 《唐声诗》下编第十附录,又见于任中敏《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编号: ○○八六。
先秦诗歌总集《诗经》有“西戎”一词,例如《小雅・出车》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之句。
战国晚期,西戎诸部的居地主要在现在的甘肃省一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4年)。
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西戎”当指西戎所居之地。
后来,“西戎”可以泛指西面的外族,例如《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西戎之地,吐蕃是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涉及:泥婆罗、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唐朝诗人继承了“西戎”这个称谓语。

清同治十一年浙江书局刊《旧唐书》
上引杜甫、哥舒翰篇章中的“西戎”搭配“犬羊”,可见杜甫和哥舒翰视西戎为畜牲。“犬羊”这词饱含蔑视外族之意。
陈与义写“庙堂无策可平戎”,此“戎”应是“戎狄”之义,不专指西面的外族。
总之,唐宋诗中的“犬羊”可以指外族,视乎语境,又可以专指某族。这个语言现实是宋朝之前已经确立的,不是陈与义自创的说法。由此可见,江西诗派诗人未必做到字字有来历,但是,他们肯定承袭一些唐人旧词(参看洪涛《文学史上的“换骨”诗——谈师法古人又保有自家面目的实例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六)》)。
陈与义写“犬羊”如何如何,其实就是金国人如何如何。然而,张教授笔下的the dogs of war (译文), 不专指外族。

杭勇《陈与义诗研究》

“犬羊”这个词,又出现在陈与义的《雷雨行》之中(参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页141):
忆昨炎正中不融,元帅仗钺临山东。万方嗷嗷叫上帝,黄屋已照睢阳宫。呜呼吾君天所立,岂料四载犹服戎。禹巡会稽不到海,未省驾舶观民风。
定知谏诤有张猛,不可危急无高共。
自古美恶周必复,犬羊汝莫穷妖凶。
吉语四奏元气通,德音夜发春改容。
雷雨一日遍天下,父老感泣沾其胸。
臣少忧国今成翁,欲起荷戟伤疲癃。
小游太一未移次,大树将军莫振功。
刘琨祖逖未足雄,晏球一战腥臊空。
诸君努力光竹素,天子可使尘常蒙?
君不见——
夷门山头虎复龙,向来佳气元葱葱。
这首诗作於建炎四年(1130年)。当时,陈与义已经逃到南方。在诗中,陈与义呵斥“(北方)犬羊”呈“妖凶”,又勉励大宋将士努力抵抗金国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腥臊空”。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陈与义《雷雨行》“犬羊汝莫穷妖凶”和杜甫诗句“西戎休纵犬羊群”(《喜闻盗贼蕃寇总退》)之意,如出一辙,两句的句义也相近:喝止猖狂的外族。
杜诗题中的“蕃寇”,指吐蕃。陈与义的“犬羊”,指金国人(女真族)。
过了大约一百年,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陈与义诗中的“犬羊”)终于在蒙古和南宋夹击之下灭亡。当时是1234年2月。
陈与义的《雷雨行》以“犬羊”搭配“腥臊”,指禽兽肉身都是腥臭味。这是不把外族当成人类看。如果以二十一世纪的“文明观”衡量,陈与义这种“羊犬观念”,似乎有歧视外族之嫌。
不过,在金人入侵大宋的语境中,宋人陈与义的抗金意志被视为“爱国主义”(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页142、页143)。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美国学者Victor Mair 主编的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描述:Ch’en Yu-yi, with Tu Fu as his model, wrote of the warfare and has been honored as an important patriotic poet. (p.357) 所谓 patriotic poet, 就是爱国诗人。

笔者这里谈论诗篇中的“犬羊”,并不是无端对“犬羊”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这个词是南宋忠义之士的“共同话语”。所谓“共同话语”在这里是指是作家们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词语。
下文我们看几个实例。
李纲(1083-1140)属于北宋末南宋初的主战派、抗金名臣,他有一首《渊圣皇帝赐宝剑生铁花感而赋诗》(傅璇琮《全宋诗》,北大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卷) 写到“犬羊”, 这诗的后半是这样的:
东南卑湿相蒸熏,坐使三尺光铓昏。安得砺砥来峨岷,淬锋敛锷硎发新。霜寒冰滑无皵皲,指麾尚可清妖氛。愿提此剑平戎獯,犬羊虽众气可吞。
手斩可汗羁可敦,天旋日转还两君。
书铭却勒燕然勋,摅愤刷耻志乃伸。
壮怀聊可垂乾坤,缇绣什袭传仍昆。
卫绾之赐何足云。

《全宋诗》
诗题中的“渊圣皇帝”就是宋钦宗赵桓(1100-1156),他被金人掳走。“犬羊虽众”,但是李纲要持剑斩杀敌首。“还两君”指打败“犬羊”金人,迎回被金人掳走的徽、钦二帝。
李纲之外,陆游的《书愤‧清汴逶迤贯旧京》(《陆游诗全集》卷三)描写:
清汴逶迤贯旧京,宫墙春草几番生。剖心莫写孤臣愤,抉眼终看此虏平。天地固将容小丑,犬羊自惯渎齐盟。蓬窗老抱横行路,未敢随人说弭兵。
“犬羊自惯渎齐盟”是斥责金国人(“犬羊”)违背盟约。大宋和大金国在1125年签订盟约(海上之盟),目的是联合攻打辽国。

《陆游全集校注》
此外,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也有“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之句(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82)。“辛幼安”就是辛弃疾。绍熙四年(1193年)秋,辛弃疾获授集英殿修撰,因此陆游称辛弃疾“殿撰”。
再如,范成大(1126-1193)在《宣德楼》一诗将侵占大宋天子宫殿的金人称为“犬羊”(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页298﹔《范石湖集》第1卷):
嶢阙丛霄旧玉京,御牀忽有犬羊鸣。他年若作清宫使,不挽天河洗不清。
“御牀忽有犬羊鸣”是指金国人占据了大宋的皇宫,污了大宋天子的御牀。
再如,张元幹(1091-约1161)《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戎马来何速,春壕绿自深。要知龙虎踞,不受犬羊侵。九庙安全日,三军死守心。傥为襄汉幸,按堵见于今。”此诗的语境不清楚,没写清楚是何方军队来犯,但是,从诗题有“京城围解”四字可知“犬羊”曾经包围了京城。
金国女真人,南宋时为患于汉人政权。女真人的后裔是满族人,然而满族是现今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之一(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黄兴涛指出,五四运动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


文学史如果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出发,那么,仇外抗金排满的话语可以等同“爱国主义”吗?爱国的话,应该怎样对待民族问题(例如:是否排斥外族)?主张各族间以和为贵、和平解决争端,就是不爱国吗?
无论如何,“爱国”常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
刘大杰(1904-1977)《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用了“爱国思想”、“爱国主义”等语形容陆游、辛弃疾(《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页322)。
游国恩(1899-1978)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六章题为“爱国诗人陆游”,第七章题为“爱国词人辛弃疾”。读者不必细读书本的内容,只看题目已经可以了解编撰者的论断。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南宋前期文学”之下的第一节是“女真族的入侵和爱国主义的文学”(第二册,页720),其后,“爱国作者”(页730)、“爱国主义”(页751)见于书中的小标题。
以上两部《中国文学史》(六十年代出版)都很重视文学作品要“爱国”,不言而喻。
到了本世纪(二十一世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也略为沿用“爱国”话语(第3册,页152论陆游;页160,论范成大……)。
有趣的是,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第四编第七章“两宋诗词的衍化”部分(页260-321),并非如此。
《中国文学史新著》谈陆游,不言“爱国”,而是着重谈陆游在“崇道抑情”的宋代显得感情充沛;谈辛弃疾,论及辛弃疾“恢复中原”之志,“激情涌动”(页294),但也不说辛弃疾“爱国”。
《中国文学史新著》南宋部分的撰稿者是不是刻意避用“爱国”二字?也许,这“從缺现象”只是因为此书有新的“书法”,立意要变更旧史书惯用的评论用语?撰稿者明显推崇“重情感”的作品。
在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南宋部分,我们看到patriotic (爱国) 这样的字眼多次出现(p.251, p.257, p.258, p.261, p.269, p.279, p.280, p.344)。
因此,在使用“爱国”话语方面,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和《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有差别的。

《中国文学史新著》
张教授说过:“……上述的两部文学史(袁行霈主编本、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本)是文革以后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也许,张教授没有察觉《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南宋部分已经罕见“爱国”二字?

本文着重讨论南宋诗人陈与义的《伤春》和《雷雨行》,兼论文学史书上的“爱国诗人”如杜甫、陈与义、李纲、陆游、范成大、张元幹的诗篇。
从陈与义《伤春》我们可以看到:陈诗中的“犬羊”,早见于杜甫诗(《寄董卿嘉荣十韵》)。杜、陈笔下的“犬羊”特指外族敌人,例如吐蕃、女真人。
张隆溪教授笔下的the dogs of war却不专指外族。
陈与义诗《伤春》、《雷雨行》之中的“犬羊”,是承袭前人(包括杜甫等人)遗留的传统诗语。
陈与义、李纲、陆游、范成大、张元幹等人都用“犬羊”,他们仇视金国人,但是,他们在世时,还没有“patriotism / 爱国主义”这个词。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获文学史家赠予“爱国”或“爱国主义”之名。

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世人不妨称南宋仇视金人的诗人为“爱国者”,可是,对于“怎样爱国”或“爱国者应该怎样做”,主战派的主张却未必和南宋朝廷的立场保持一致。因此,他们也可能怨恨南宋朝廷不积极恢复中原(按:宋孝宗、宁宗時期一度北伐)。
时移世易,唐朝吐蕃人(多居于西藏)、东北的满族人(女真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是中华民族之外敌。
到了二十一世纪,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南宋部分,“爱国”用语消声匿迹。相反,“patriotic”多次见于张隆溪所叙的南宋文学史。
“爱国”在政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情感。有趣的是,张教授其实一再强调他抗拒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诠释”。
也许评定某作家某作品为patriotic,在张教授心目中是和政治无关的?其实,patriotic的作品,是否价值较高?中国文学史的“爱国”是否专指爱汉族人建立的国家?像《三国演义》所写那般各为其主(魏、蜀、吳)、各自称帝,是否魏、蜀、吳三国的人都不忠于大汉王朝,没资格谈patriotic/“爱国”?这些问题,有待张隆溪教授分解。
本文没有讨论南宋词。在结束本文之前不妨补上一笔:南宋“爱国词人”的“能见度(visibility)”在近世得到提升。这一点,前贤(例如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已经论及。
“爱国词人”的代表辛弃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日战争爆发后很受重视。村上哲见指出,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1956年)选录辛词44首,辛词是名家词之中获选录最多的(村上哲见《宋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页425)。

村上哲见《宋词研究・南宋篇》,创文社2006年版。
这是文学接受史(reception-oriented literary history)的典型案例:作家的文学地位受时代精神(反侵略)推升。
附记一:“犬羊”和“文身地”
本文讨论的“犬羊”是中土之人蔑称外族的用语。旧时,中土之人视外敌为牛羊猪狗之类的畜牲。
蔑称词“文身地”也是相对于“华夏文明之邦”而言的,见于唐代柳宗元诗。请参阅《洪涛:试问岭南应不好? ——谈文化差异、“文身地”和tattooed bodies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八))》,载2024年6月25日“古代小说网”。

关于“仇外话语”,读者还可以参看洪涛《金瓶梅的文化本位观念与仇外话语的英译》一文,载《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年)。
附记二:国史、爱国和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一书指出:十九世纪,欧洲国别文学史的生成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页5)。
H.A.Taine(泰纳)在其名著《英国文学史》中以民族、环境、时代三大要素论文学的发展。泰纳模式对民初的中国学术界影响不小(参看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泰纳模式传到中国后,第一要素民族似乎强化成“爱国、保种”,早期的林传甲、黄人的著作中已经有这种痕迹,例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批判有些人“知有君不知有国,更不知有民。”(第四篇第八章)林传甲的意思是“爱国”应取代古时的“忠君”。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再举一例。黄人(字摩西,1866-1913)说:“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参看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铅印本1911年,第一册,第一编“总论”。另参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45)。
黄人所说的“种”就是种族。他的意思是:文学史和国史的功能没有差别。
专研文学史书写的戴燕说:“以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为目的的文学史……”(《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页247)。这句话,大概不是纯粹的个人意见。然而,域外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书恐怕就没有此“激发”的目的,读者可以参看:翟理斯(H. A. Giles)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和葛禄博(Wilhelm Grube)的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190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爱国”这个文学史课题关注的是:文学表现了什么价值(相对于“文学如何表现”)。在重视功利方面,“爱国主义”和“文以载道论”实是同气连枝。
推广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是民初以来不少文学史家乐意承担的任务,于是,文学史也是一种“国民精神史”,文学史书脱离不了对“工具性价值”的追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撰写文学史却以推广白话为己任。1928年其《白话文学史》在上海出版。)
实际上,二十世纪初,不少文学史书是由学校讲义发展而来的,例如: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授课,黄人在东吴大学授课,编有文学史的讲稿。也就是说,起初,中国文学史的成立是和教育目的息息相关的。
戴燕说:“……爱国主义,恰好又是近代国家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核心观念,……”(《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页88)。《文学史的权力》第三章是“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值得读者参看。戴燕指出,建国后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课“保持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页95。)

《白话文学史》
以上所述的一切,无碍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停用“爱国”“爱国主义”来冠名述评。
附记三:华裔作者撰写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
笔者最近刚接触到两种华裔作者撰写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
(1) Shou-yi Ch'en (陈受頤), Chinese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1. 此书的封面,有中文书名:《中国文学史略》。

Shou-yi Ch'en (陈受颐)的著作
(2) Lai M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此书有林语堂写的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