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皇命与当朝大将军成婚,他却在新婚夜弃我而去,追随自己的心上人北上塞外。
一别三年,在我对他死心后,他带着对我的亏欠回到了我身边。
--------

我是被父皇赐婚给狄少頫的。
狄少頫征战东南有功,返京后得父皇厚赏,其中有一赏赐便是御赐婚事。
阖宫庆宴上他欣然上前领命,却被父皇告知他该娶的人是我。许是他喝了不少酒已然醉了,他在众目之下愕然抬头,不顾规矩地看向了坐在我身旁的人。
我身边坐着我的姐姐。她年纪正好、温柔娴淑,理应与狄少頫正当相配。
我亦看向姐姐,只见她的始终低着头不说话,藏在桌下的手指攥紧了衣袖,骨节泛白,用尽了力气似的。
父皇身边的管事公公赵祺提醒狄少頫谢恩,狄少頫少见地没有听从父皇的旨意,而是深深叩头求道:“臣谢陛下信任,将映欢公主许配于臣。然此番恩德与信赖臣受之惶恐,心有不安。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恩典。”
一语出,众座哗然。
父皇微有不悦:“狄卿拒此婚事,是有顾虑?”
钟乐暂停,狄少頫的声音在大殿里格外清晰:“臣确有顾虑。”
“说来听听。”
“臣常年在外,对家中照顾甚微,宅内之事顾及不了多少。映欢公主为嫡公主,自小在宫中受万人宠爱,金枝玉叶,嫁于我这等行伍粗人委实委屈。”
“行了,不必在此言不由衷。”父皇轻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狄寅安心里想的是什么,朕能不知道?”
“寅安”是狄少頫的乳名。狄少頫生于寅时,生他时他的母亲侯夫人险遭难产,故取名“寅安”。
侯夫人和我母亲相交甚好,为闺中密友。儿时他常随侯夫人进宫,“寅安”这个名也常被父皇和母亲提及。后来他从军,慢慢地,宫里没人这么叫他了。
而今父皇在阖宫宴上再度叫狄少頫的乳名,无非是想告知对方,他是念及我母亲和侯夫人的姐妹情深,才愿将他最心爱的女儿赐嫁给狄少頫。若狄少頫再不领情,恐真会龙颜大怒。
狄少頫乖顺:“陛下圣明洞察,臣子心之所想必瞒不过陛下。”
“朕不用圣明,你的心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父皇朝我和姐姐看过来,“映微淑庄,映欢烂漫,朕的女儿个个不差。论年龄,寅安的确与映微相称,然朕允不了你的心意。”
只要提及姐姐,狄少頫顾不得规矩:“为何?”
“西北金庭大帐动乱,穆和单于为稳局势,为其嫡长子求娶我大齐公主,以确保嫡长子顺利登位。我已允了。不日金庭便来迎娶映微。”
我始终看着姐姐。父皇言罢,我清清楚楚看到一滴泪从姐姐的眼睛里掉了出来,砸落在纤瘦的手背上,然后滑进了指缝间消失不见。
狄少頫抬头,又问了一句:“为何?”
这一次是问为何应允和亲。
“金庭位于我朝和敕鞑部落中间,扼守西北咽喉命脉。金庭帐安稳,西北就安稳。”
“臣恳请陛下三思。建朝初仁肃皇帝远嫁亲妹妹于金庭,朝阳公主终生不得还乡。后来正平皇帝嫁婉陵公主再往金庭,公主经不住关外苦寒,三年后郁郁而终。陛下,金庭帐远在玉门关外,那儿不该是我大齐女子,尤其不该是我大齐公主屈尊去的地方。”
“今日不同往昔,当年是和亲,而今是对方求娶。你父亲年轻时攻略西北,使得金庭帐归顺于我朝。一经三十年,此番联姻与当年屈辱和亲早不可同日而语。”
“陛下,臣冒死直言,纵与当年不同,但到底是以女子换得边关暂稳。和亲拙计,恐有污史册!”
他的这番话说得大逆不道,我陡然紧张起来,生怕父皇震怒,赐婚不成,反倒销了他的军功。
父皇闻言果然冷了语气:“狄少頫!”
狄少頫跪定在殿里:“臣在。”
“朕告诫于你,你休仗着功勋在身,做出不合规矩之事。”
“若陛下担心金庭会生二心,臣愿带兵前往玉门关。家父年少时可攻略西北,臣亦可。遑论三十年,便是四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终臣之一生,臣也愿意固守在那儿,只求得陛下收回和亲圣令。”
字字句句铿锵落地,话音在大殿里回荡。
他不是在说大话,一身虎胆,飒沓如他,他做得到。
我把目光从姐姐身上收回来,也像她一样低下头去。
从狄少頫拒婚开始我一直难过,直到他说出这番话来,我忽而想放弃他。
他是姐姐的。
从小到大,他喜爱的人一直是姐姐。
“狄少頫,你狂妄至极。”父皇不怒而威,“你愿带兵前往玉门关?你与你的父亲作比?”
狄少頫默然。
“你刚问朕为何允诺穆和的求娶,朕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酒泉一役虽大获全胜,逼得金庭降服。但鏖战五年,所付粮草资饷不论,单人马折损八万。八万人马,狄少頫,你久在沙场,用兵数年,你该知晓其为何意义。”
父皇轻叹:“以泽量尸,一将功成万骨枯。你狄少頫自问,你这一路是踩了多少白骨残骸才获得今日殊荣?朕也自问,朕能在此笙歌盈耳,又是辜负了多少百姓苍生?”
父皇兴致寥寥,拂袖而起。
“朕的女儿尊贵不可去往金庭,那其他父母的子女便不尊贵,便可马革裹尸魂留他乡?”
赵祺上前扶着父皇,父皇摆手:“散了吧。”
父皇走后,各宫娘娘和亲王也陆续退去。
母亲临走时唤我:“映欢。”
我起身随母亲而去,走出大殿后回头,看到狄少頫还跪在中央,不远处站着姐姐。
咫尺殊途,两两沉默。若从皇命,他们便是此生缘尽,从此天涯路迢迢。
我瞬时潸然,觉得自己做了天大的错事。我低声问母亲:“母后,姐姐非得和亲吗?”
“对。”
“如果非得有人去,那我去吧?”
母亲又惊又怒:“你说什么混账话?”
“我不要嫁给寅安哥哥了。”我哭得哽咽,“自刘娘娘去世,姐姐没了生身母亲后,这么些年她一直不开心。她不像我有母后庇护,有父皇疼惜。她什么也没有……”
我的声音低下去:“她只有寅安哥哥。”
“李映欢你闭嘴。”母亲直呼我的名字,“你父皇问你是否心悦狄少頫时,你应他说是,你父皇这才将你的婚事当国事而论。”
前几日父皇是问了我此事,可是我不知道他在为我筹备婚事。
我执拗地问母亲:“若我当日应答父皇我不中意寅安哥哥,是不是该去和亲的人是我,而留下来嫁给寅安哥哥的人是姐姐?”
“不会。”母亲发声音在夜色里很轻,“只要我还活着,就没人能把你送往关外。”

父皇金口圣言,说出去的话不会收回。狄少頫不能左右,我和姐姐也不能左右。
皇帝最宠的女儿嫁予风头正盛的少年将军,自是京城的佳话。父皇节俭,我和狄少頫的婚事没有大办,却也喧闹了整个洛阳城。
所有人无不羡佳偶天成,只有我明白,狄少頫并非我的良人。
新婚夜他喝得酩酊,被下人送到屋里时人已迷离,横卧在榻上一身酒气。
他的贴身仆从我见过,人平日里寡言少语,把狄少頫送到我身边后恭顺谦卑地传侯夫人的话:“公主,侯夫人说今日大喜日,将军多喝了几杯,还望公主莫要见怪。有劳公主照顾。”
我微一点头。
仆从甫一离开,狄少頫翻身而起,喊道:“阿禾。”
刚出门的人被叫住,隔着门应道:“属下在。”
狄少頫醉得不轻,扶着雕花床柱想站起来:“阿禾,去我书房收拾一下……随本将回营。”
“将军早些安歇。”
阿禾不给狄少頫再说话的机会,说完步下台阶。夜晚寂静,我听得清楚,院中再连个声丝儿也没有了。
我始终坐着,给狄少頫挪了挪地方,道:“睡吧。”
狄少頫这才回头过来。他一袭喜衣,玉冠束发,红灯罗帐前格外俊秀,不似盔甲在身时的凌厉。
他愣愣地看着我,许久后,攒眉苦涩道:“你要是映微,该多好。”
灯芯跃动,他在说话的瞬间落下两行泪来。
我良久失语,最终讷讷:“我不是姐姐。”
他回过头去:“你怎能是她?”
“她淑雅和善,最懂人心意,从不会扭拧他人。她不似你。”
剩下的话他没说,我却懂。他是想说姐姐不似我这般任性。
我摇头,也哭了:“寅安哥哥,我是倾慕你,可是姻缘并非我定,不是我做的主。”
狄少頫抗拒斥道:“别叫我寅安。”
他踉跄站起,拎起桌上的壶给自己倒了杯水,饮尽后叹气:“我对不住她。十八年间她无一日不过得谨小慎微,我答应了她,要带她走出高墙宫苑。我食言了。”
狄少頫人虽醉了,话却是清晰的:“金庭形式复杂,她往后的日子依旧如履薄冰。”
我竭力安慰:“父皇会派很多人陪姐姐去往金庭。她有父皇撑腰,会过得好。”
“撑腰?”狄少頫大逆不道,“若真能撑得起这腰,为何去的不是你这位掌上明珠?”
他的目光和他的话像利剑一样刺向我,我控制不住地发抖发冷,脑中轰然。
“荣嘉公主,你说呢?”
“荣嘉”是我出嫁前父皇赐给我的名号。狄少頫这么叫我,显得格外生疏冷漠。
我哭道:“今夜是我们的新婚夜,我们可不可以不提姐姐?”
狄少頫再倒水时水杯倒地,滑落在地上后散成了一地碎片。
他烦躁地骂了一声,沉沉叹息后对我道:“你睡吧。我回营中。”
我站起来走向他,不敢喊他的乳名,只谨慎道:“你别走。只陪我过了今夜吧?安稳过了今夜,往后你宿在何处都行。”
我长在母亲身边十六年,确实如狄少頫所言,我是掌上明珠。因是掌上明珠,我从没有受过任何委屈,遇到了难处也只会哭。
我懦弱无能,比不过姐姐。
我哭得喉头发疼,轻轻揪住狄少頫的衣袖:“求你。若你今夜丢下我走了,一旦被旁人知晓,我会成为全京城的笑话。”
狄少頫自始至终没有答应我。
“你倘若走了,我会恨你的。”
他从我手中抽袖挥手,径直走过去打开了房门,一步踏出门外。隔着泪雾,我看到他头也不回地离我而去了。
清凉的夜风从大开的门里吹进来,我周身生寒,瑟瑟不止,扶着桌子站也站不稳。
陪嫁女官碧儿连忙掩门扶我,半搀着我坐在榻上,抱紧了我:“公主,不哭了。”
碧儿年纪比我大一点儿,我向来依赖她。我止了哭声,喃声委屈道:“我想回宫。”
“公主乖,再等等。等怀宁公主婚事落定,我们便可以回去看皇上和皇后娘娘了。”
我把脸埋在碧儿的怀中:“你怎么也提姐姐?”
我又哭起来:“是我对不起姐姐。”
“公主,不怨你。”
碧儿老成,叹道:“人各有命,是天定的。公主切莫乱想。”
新婚夜是怎么睡去的我不记得了。苦累了趴在枕上,翌日醒来哭肿了双眼。
狄少頫自那夜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他忤逆到底,连新妇对公婆的晨昏问安他亦没陪我去。侯府的人各个不敢言,待我更为谨慎。从侯夫人到下人,他们都怕我为此而闹。
若我真拿此事做文章,父皇必然不会放过狄少頫。
我没闹。
因为闹了也没用。
他已经够厌烦我得父皇的宠爱比姐姐得到的要多,此事我再仰仗父皇替我博公道,他会更加厌我。
况且,他的心不在我这儿,即便我闹得整个京城不宁,他也不会对我有半分好感。
姐姐的婚事与我的婚事相隔三日。
因是嫁往金庭,她的婚事大礼无比盛大。我作为新妇不能出门,独坐在院中静听锣鼓喧鸣声。
论起姊妹情谊,我和姐姐看起来的确不似寻常人家的姐妹那般亲密无间。姐姐内敛秀慧,不爱多言,从前在宫里我好几次想和她一道儿玩耍,都被她礼貌地拒了。
次数多了,我渐渐不怎么去招惹她了。
我儿时总以为我和她相处的日子还长,总有一日我能亲近她,也能像普罗人家的姊妹一样凑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然白云苍狗,似乎只是一须臾间,我和她各成孽缘,在喧腾的锣鼓声里无声作别。
午后的时候碧儿从府外回来,带来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金雀钗,另一样是姐姐亲笔写的书信。
姐姐写了寥寥几行字,只问我安,不问狄少頫。她在信中说金雀钗是她给我备着的新婚贺礼,因婚前繁忙,她一直无法得空见我,没有送出。
她让我好好儿在侯府生活,让我不要因为世事变迁而打磨了自己的率真性子。
她说:“映欢,我最爱你的脾性,也最羡慕你的脾性。”
从始至终,她没有提起狄少頫。
我疲惫不堪,把信压在枕下昏沉沉地想睡觉,朦胧间我后悔自己没有给姐姐备一份新婚礼。
傍晚狄少頫终于回来了。
他一步踏进院中,没想到我坐在桂花树下下棋,当即顿步在院中央。离开时穿的那身喜衣红袍早被他换了,酒醒后的他目光清明,比起新婚夜时,眼里少了违逆,多了疏离。
他风尘仆仆,应当是走了很远的路。
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缓缓移回来,对和我博弈的碧儿道:“该你落子了。”
狄少頫站了片刻后迈开步子往前,错过我,径自去了厢房换衣衫。
阿禾站在台阶下静候狄少頫,我随性问道:“你们将军是去送亲了,对吗?”
阿禾难堪,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我。
我再落下一颗子,托着腮看碧儿:“笨碧儿,你输了。”碧儿嘀咕每次赢不了我,月钱都快要被我赢光了。
厢房门轻开,狄少頫换了件居家干净的衣裳出门,站在檐下遥遥看着我和碧儿。
我权当看不见,仔细地有条不紊地收拾棋子。
晚间轻风细语,吹得头顶的树叶飒飒作响,快到中秋时节,桂花味甚浓。
他站到无趣的时候忍不住开口:“母亲嘱托明日省亲,我已向军中告假,陪荣嘉公主进宫。”
我问道:“我姐姐的轿辇到何处了?”
狄少頫惊愕,全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
我昂头看他:“你不是去送亲了吗?若未时一刻出发,此时应当到了书桥驿。我算得对吗?”
狄少頫冷眼:“荣嘉公主这是何意?”
我收拾完了棋局起身,道:“并无他意,只是我也挂念姐姐,担心她一路山高路远,劳顿不堪。”
我步上台阶站定在正屋门前,回应他刚刚说的话:“明日晌午动身吧。我母后差人来传了话,想留我们在她那里用午膳。”
狄少頫沉默。
“礼数手信我都备着了,将军不必费心思。只是我有一事告知你。”
狄少頫毕恭毕敬:“公主请讲。”
我傲然道:“你说得没错,我确实为掌上明珠。自不必说我母后,单说父皇,他也极度宠溺我,从小到大不叫我吃半点儿苦,受半点儿委屈。”
“将军应该知道明日该当如何。”我看进狄少頫的眼睛,“你若是想保住侯府的安宁,明日切记做个良婿。”
狄少頫黑而沉的双眸里满是不悦,依旧沉默着没有说话。
翌日省亲,宫里因姐姐大婚刚过,一派喜气。我和狄少頫先去了皇祖母那儿。
皇祖母年事已高,身体一直抱恙,但她喜爱儿孙,我的回来让她精神好了不少,穿了锦衣华服特意等我。
我和狄少頫拜过祖母后,祖母唤我:“欢儿,过来。”
我提裙欣然上前,还跟闺中时一样依偎在她身边。她半混半明的眼光慈爱地打量着我,笑着:“欢儿的发髻梳得极好,这雀钗也巧,越发俊了。”
她言罢又朝狄少頫招手:“你也来。”
狄少頫跪在祖母身边,比任何时候都要乖顺:“祖母安康。”
“你儿时常随着树蕙进宫,后来从了军,甚少来了。”皇祖母问,“树蕙可安?”
“托皇祖母的福,母亲一切安好。”
皇祖母始终紧握着我的手,转而叮嘱我:“欢儿,你侯夫人是这世上顶好的人,你既嫁过去了,定要尊她敬她,多听她教诲,多守规矩,不可跟以前在宫里一样,调皮淘气惹她烦心。”
“是是是,孙女知道了。”
皇祖母话音宠溺,朝狄少頫道:“听听,这就不耐烦了。寅安也多管管她。她这只皮猴子谁都不怕,只怕你。她要是闹起脾气来,她父皇都得让她三分。唯独提起你,她能听得进去几句话。”
祖母如絮家常:“映欢孩提时犯懒不读书,但若是皇后说三日后寅安进宫,她便勤奋了。她背了文章想给你显摆,但是次次又胆小,不敢去见你。”
我尬色难掩,低头:“祖母,你别说了嘛。”
“不叫说了?从前提起寅安你不知羞,成日里把他挂在嘴边,怎么成婚了反而娇羞知臊了?”
“祖母,别说了。”
“好,不说了。”
我不想让狄少頫看到我的难堪,请求皇祖母:“祖母,你快给少頫赐个座呀。他跪了甚久。”
皇祖母这才想起来:“哎呀我这老糊涂。”
狄少頫道:“皇祖母,无妨。”
狄少頫坐定后祖母给我们二人赐了茶,忽然问道:“欢儿,你以前都是寅安哥哥长,寅安哥哥短,怎么忽得改口了?”
我端着茶杯的手不稳,垂着头轻嘬了口茶,咽下后平静道:“祖母,孩儿想着既已成婚,自要守夫妻礼节,还是叫大名为好。”
祖母探究:“怕是寅安不让你叫吧?”
我心下一惊,看向祖母。
与我一道看向祖母的还有狄少頫。
祖母只猜对了一半:“互道乳名这等事,是夫妻二人间的秘事雅趣,他怎可让你在外叫出口?”
我点头:“是。”
我低头的瞬间无意看到狄少頫在看我。他双眸沉沉,瞧不出里头的情绪。
从祖母处出来我心口沉闷,虽已回家,但一点儿也不开心。
长街秋凉,我踩着熟悉的砖,数着熟悉的瓦,一步一步走向曾经看似无忧的闺阁。
一路默然向前,狄少頫蓦地出言:“谢公主的担待,在太后那儿替我美言。”
我没有驻足,步履不停,说道:“担待?我不会担待。”
轻微的秋风里,我听见他沉沉叹息。在我的记忆里狄少頫意气风发,很爱笑。可是这几日但凡见着他,他总在叹息。
或许他仅仅是喜欢对姐姐笑而已。
他叫我:“公主,留步。”
我回头:“何事?”
“宴会赐婚时,我所言并非为虚。”
他拒婚时说了很多话,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指的是哪一句。
“我常年在外,对家中照顾不周。公主金枝玉叶,嫁给我确实委屈。”
我站定:“你想说什么?”
“河西动乱,我借此次面圣机会,想请命前往。”
我读过兵书。河西距酒泉隔山而望,脚程仅几百里而已。过了酒泉就是金庭帐,那儿有姐姐。
他宁愿扔下新婚的妻子,也要去边关守自己真正的心上人。我无法言明自己的感受,只觉得长街上秋风乍凉,风刀刺穿了我的皮肉,剜烂了我的心。
“关内外大小战乱不断,若想彻底平定,恐需些时日。”
我嗫动唇瓣:“多久?”
“三年,或五年。”
眼泪弥漫,在眼眶里氤氲得满满当当。我利落转身,不肯让狄少頫看到我的哭相。
流干了泪后我昂头看高处,黛色的砖瓦高耸,把湛蓝的仲秋碧空割成了方正的一方天。我的反应比姐姐迟钝,我才意识到宫里的天不阔,我们像金丝雀一样被束缚在其中。
如若我再聪明一点儿,开慧再早一点儿,早点抬头看看天空,知道外面的世界偌大,选择良多,也许我不会择狄少頫为婿。
我会恳请父皇把我嫁入寻常百姓人家,与夫君琴瑟相鸣,朝暮相见,能真如祖母所言,把轻唤乳名这样的事也当做闺房乐趣。
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狄少頫请命成功,带兵北上。
他一去三年,除去捷报战讯,他从不往家里寄一份书信。父皇逐渐察觉我的委屈,最终心疼我的处境,答应我在狄少頫回京后准许二人和离。
逐渐放下对这场姻缘的执念后我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唯有一点不好,那便是母后叮嘱侯夫人好好管教我,切不可让我贪玩坏了规矩。我想出去玩闹的计划回回施展不利,侯夫人为了监督我,特意派了她身边最得力的管家来我院里当差。
我被困在院里,整日里只得读书绣花,偶尔兴致来了,和碧儿手谈几局。但碧儿水平太差,我和她下棋总归不尽兴。
去冬我迷上了话本,有一次溜去街市买了一堆话本子回来,整个冬日窝在房里倚窗偷看。
老管家以为我收敛了玩性,放松了警惕,还叮嘱碧儿多让我出门晒晒太阳,生怕我整日憋在房中闷坏了自己。
婚后第四年暮春,狄少頫回来了。
他又打了胜仗,河西彻底安宁。用父皇的话说,狄卿在,社稷安。
天气暖和后我会带着话本子去院子里赏阅,树下有软椅,是消遣时光的最好去处。午后阳光暖融,我经常看着看着会睡过去。
狄少頫来院里的时候我正睡得酣,梦里听见有人进门,我以为遭贼了。
倏地醒来,迷离看见狄少頫站在院中不远处。
我困顿地眯了眯眼,再次躺倒在椅子上。我心里嘀咕,醒得太过仓促,都看见狄少頫这等不该看到的人了。得再睡会儿。
闭眼没多久,碧儿叫我:“公主。”
我懒怠地用鼻音“嗯”了声。
“公主,你快醒醒。”
我惺忪睁眼,碧儿低着眉,给我不作声地使眼色。我狐疑地朝院中看去,在看到狄少頫的时候当即愣住。
不是梦,就是他回来了。他长身玉立,站在远处清冷冷地看着我。
见我醒来,他人前做戏般地问我:“公主一切可安?”
我微一点头,算是应了他。
这一刻我竟恍惚起来,好像我们还是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进宫请安,我躲在母后身旁娇羞地不敢抬头看他。
我在当年不敢抬头窥探他,而今不敢回头追忆当年痴勇的自己。
我坐直身子下意识伸手去摸睡前放在膝盖上的话本子。膝盖上多了一张薄毯,本子没了踪影。
我心中一惊,抬头看碧儿。
碧儿还低着脑袋,眼角余光瞥狄少頫。我明白了她的意思,顺着她的指引看过去,果看见我的话本在狄少頫手上,封皮上的名字惹眼——《小白蛇情迷痴心郎》。
我记恨狄少頫三年有余,本不想与他多言,但实在难堪话本子在他手上,起身不悦道:“你还给我。”
狄少頫摆手差走了周遭的下人,连阿禾和碧儿都被他清退。
他轻轻翻动书页,浏览一遍后问我:“你日常便是从这些靡靡之物上寻些闲趣打发时日?”
狄少頫博览群书,自然见不惯我看这些。他喜爱姐姐也是因为姐姐熟读诗书,有才华在身。我与姐姐不一样,在知书达理方面我是个俗物,是块雕不了的朽木。
我横眉:“你还给我。”
“公主心大,阅读此物时毫不遮掩,但若被院外人知晓,告知于母亲,该当如何?”
我一时结舌。别说是规矩严明的侯府,只寻常读书人家,也不叫这种话本子进门。狄少頫说得倒是没错,此物为靡靡之物。
“这种东西明令不能在府上出现,要是被母亲发现,罚你跪祠堂都是有可能的。”
我真够倒霉,狄少頫甫一回来便把我抓了个现行。我不想和他争,他想说教便说教,他想去侯夫人那儿揭发我,那我也认。
“从何来的?”
“与你何干?”
“听闻母亲差了周二叔来院里当值,看来周二叔年老不中用了,被你瞒了过去。”狄少頫凝眉瞧书页后的店铺题字,“西市街坊,你溜得够远的。”
他微微勾唇,有点像自言:“我竟从不知晓西市街坊还有卖这等玩意儿的铺子。”
我再一恍惚。他刚刚是笑了吗?
有什么好笑的?
他举起话本:“劳烦借我阅读几日。一路班师栉风沐雨,刚好借此物消遣。待我读完了,定会还你。”
“…………”
我还没看完呢!
狄少頫把话本收起来,唤阿禾:“阿禾,回营。”
阿禾随叫随到,多嘴:“侯夫人叮嘱将军今晚只能歇在院里,属下不敢违侯夫人的意思。”
狄少頫瞧了我一眼,迟疑:“这……”
我站着不说话,心想他这人好无礼,借东西不像借,拿得理所应当。
他的目光里闪过一丝丝失落,拍了拍阿禾的肩:“先回营中,入夜再回来也不是不行。”
他欲跨出院门,我忽得想起什么来,叫住了他:“留步。”
狄少頫欣然转身,阿禾也转了过来,主仆二人像是有所期许地看着我,眼里能映出春日的阳光来。
“听闻将军回京前去了金庭帐,不知有没有见到我的姐姐?”
狄少頫眼里的碎光点点消失,眼睫轻动,乌油油的眸子沉了下来。
“在关外三年,我姐姐一切都好吗?”我说着哽咽,是真的想她,“听闻胡地贫瘠荒芜,胡人茹毛饮血,她还过得惯吗?”
狄少頫沉声回我:“见到了。一切都好。”
“那金庭王室的人有没有为难她?听说婚事有变,和她成亲的是穆和的小儿子颜都,并非长子,是么?”
“是。”狄少頫的话像是在讽我,“荣嘉久在府邸深宅,没想到也关心关外之事。”
我不想理狄少頫的讽刺,只想知道姐姐的处境:“那颜都品行如何?对她好吗?你有没有问问姐姐是否想回来?”
我落下泪来:“三年了,父皇已知赐婚有错,自知亏欠于我,许诺不管我求他什么他都会答应我。而今你定了西北,如果我去求父皇召姐姐回宫,他会同意我的。”
狄少頫冷然道:“陛下会同意,金庭可不一定同意。”
“为什么?”
狄少頫的话出乎我的意料:“颜都单于深爱怀宁公主,金庭上下无人不尊爱他们的汉人阏氏。”
我含着眼泪怔愣,一时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
我喜悦姐姐得人宠爱,又忧愁姐姐或许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公主刚刚说陛下许诺公主一愿?”
我点头。
“公主原本的愿想是与我和离,离开侯府,对吗?”
我轻轻眨眼,眼泪扑簌簌而落。狄少頫是很聪明,敏锐地看穿了我的心思。
狄少頫转身,与我相距几步之遥,道:“春日我在金庭见到了怀宁公主。荣嘉想不想听听怀宁公主跟我说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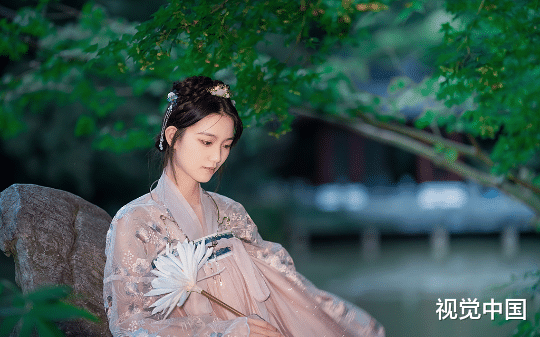





不喜欢结局,对于负心男就不应该原谅,,他怎么会因为别人几句话就爱上你
离谱啊,这种男人不能要啊,公主咋就不清醒,和离了不好吗?
姐姐挺好的,聪慧看得清形势,懂大义明理,和亲后有了自己一番天地,男女主的感情有点莫名其妙。
这样还要?呵呵!这公主是白痴吗?
这公主好贱
史,女主好贱
强行结局吗
这公主贱得像坨狗屎。
姓狄的很渣很渣。[得瑟]
还没看被评价劝退了,我听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