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离“原”世界后,英雄终于全身心地投入了冒险,“越过第一道边界”,第一次完全进入了故事中的非常世界,他准备好迎接冒险召唤中的问题或挑战。
这意味着“英雄之旅”的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在神话故事中,英雄的启程并非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来自多方的支持和阻挠,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

这些人物在沃格勒的“英雄之旅”理论被称为原型。
受到卡尔·荣格的影响,克里斯托弗·沃格勒在约瑟夫·坎贝尔的基础上,引入了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故事角色特点分析的一种手段,由此形成了点面结合的故事分析模式。

荣格在他的心理学专著中指出,原型是贯穿了所有时代和文化,即出现在个人梦境里和个体性格里,也出现在全世界的神话想象之中,是不断重复着的角色或能量。
他总结自身诊断精神病人的临床经验,指出对于原型的感应来自人类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据此,沃格勒总结出英雄之旅模式中存在的八种原型,分别是英雄、导师、边界护卫、使者、变形者、阴影、伙伴和骗徒,这些原型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与叙事功能。
在体育电影中,除了担任主人公的英雄角色必不可少之外,每一部影片中,几乎都出现了其他原型。

有趣的是,这些原型不仅仅局限于相应的角色,还可以通过一件事或者一种抽象化的状态来表现。
在体育电影中,导师一般是经验丰富并且性格执拗的教练,边界护卫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或第一个障碍,信使是告知比赛信息的人。

变形者是主人公脾气暴躁的伴侣,阴影是主人公的对立面、是其对于自我意义的迷茫与困惑,伙伴则是团队中的队友或者支持英雄的朋友,骗徒是英雄的团队中滑稽的小丑或者擅长调动气氛的开心果,这些都是好莱坞体育电影中频繁出现的经典形象。

这些原型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原型与角色之间关系的变化成为影片情节转折的重要因素;这些原型角色的出现也同样推动和展现了英雄们的成长。
原型和角色并非一一对应。《弱点》中的导师由三个角色同时扮演。同样,同一个角色往往并不会从头到尾始终扮演一个原型,而是时常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产生惊人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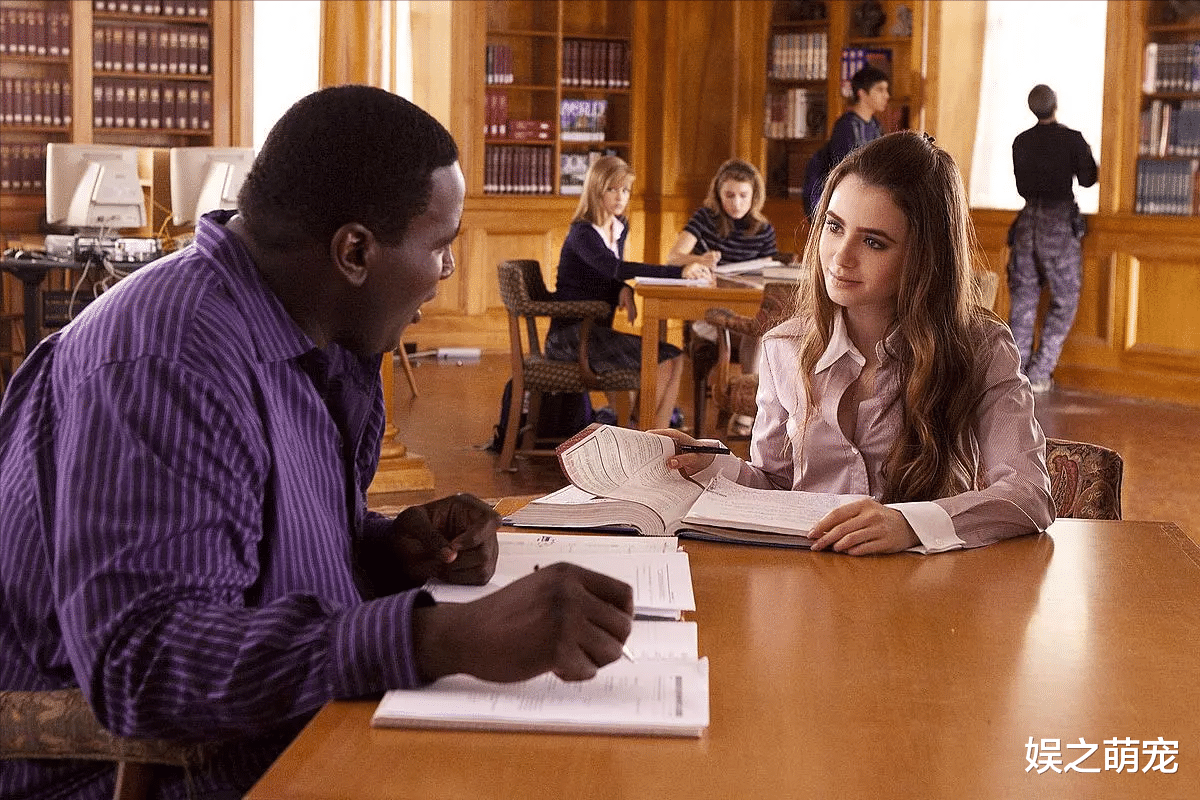
在这种时候,可以将原型理解为角色所佩戴的“面具”,比如《百万美元宝贝》中的法兰基·邓恩的身份随着剧情的发展就发生了变化。
在电影一开始麦琪充满期待地找到法兰基并请他训练自己时,后者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她,对于麦琪多次请求法兰基始终不予理睬。

因而在这里,法兰基扮演的原型便是边界护卫一一麦琪踏上英雄之旅后的第一个“关卡”。
但在麦琪每天坚持来拳击馆练习,并一次次向法兰基真诚地道出自己对拳击的热爱与决心之后,法兰基渐渐被感动,并逐渐对她敞开心扉,最终接受了麦琪。

这时,法兰基将他原本带着的边界护卫“面具”摘掉,开始扮演导师原型。
因此,在本文研究的十五部电影中,原型不再固定在某一角色身上,而是成为了角色脸上的“面具”,可以随时摘下或者戴上,这也为电影中的角色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任何一个角色的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节点。

根据沃格勒的“英雄之旅”理论,原型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代表帮助英雄的正面形象,英雄的导师、伙伴和信使,他们在英雄身边不断提供各种指导和鼓励来帮助英雄成长。
另一类是阻挠英雄前进的负面形象,阴影、边界守卫、变形者,他们通过考验与不断提出异议促使英雄成长,将英雄的考验和逆境逐渐戏剧化。

而骗徒是极具争议性的存在,他们可能是英雄或阴影阵营中的伙伴,也可能自成一派,这决定了这一原型身上的正反两面性。
如《我,花样女王》中的肖恩就是扮演骗徒,他是杰夫的小跟班,为了帮托尼亚出头于是去给她的对手南希一点教训,但他为了吹嘘自己而把事情闹大,最终葬送了托尼亚的职业生涯。

而在本文所研究的十五部电影中,并非只有骗徒存在这种两面性,所有原型角色的正邪之分在电影中被模糊化。
如《极速车王》中的福特集团,既是迈尔斯和谢尔比的伙伴同时也是他们的阴影,在给予二人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在阻挠二人成为勒芒拉力赛的冠军,于是伙伴和阴影这两个原型在这部电影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反两面集福特集团于一身。

电影将原型的正邪之分模糊化后,去掉了原型自身存在的固有特征,也就是对原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去脸谱化,这使得观众难以判断角色此时的真正身份,也使得剧情的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增加了电影的娱乐性和悬疑性。
七大原型与英雄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动英雄的成长。根据以上两点我们能得出原型的多变性和两面性,这也导致了原型与英雄之间复杂的关系。

当扮演原型的角色发生变化时,该角色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如法兰基从最开始做为麦琪的“边界守卫”到“导师”,他与麦琪的关系也从对立走向了合作,这无疑是从正向推动了麦琪的成长。
而当原型展现出两面性时,该角色也同样能够推动英雄的成长,如《极速车王》中的福特集团,在影片中为迈尔斯和谢尔比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在不断设限,挑拨二人的合作。

这也导致二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看清楚了福特唯利是图的权谋商人本色,从而促成两人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以及对体育精神的深刻领会。
因而我们也可以得出,无论原型如何的变化和难以捉摸,不同的原型都能从正向或者反向推动了英雄的成长,加速了英雄在冒险之旅中的进度。

当英雄之旅进行到第三阶段,对于英雄而言,最危险和最具挑战的便是“复活”,这是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最后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面对死亡,这也是与阴影做最后的对抗。
英雄必须经历最后一次考验才能证明自己在冒险之旅中所学到的东西,实现个人成长。
与之前所经历的考验不同之处在于,“复活”阶段的危险性达到了整个故事的最高点,是决定英雄最终结局的对抗。

在体育题材电影中,主人公所面临的最后一次考验可能是英雄在整部电影中最重要的或是难度最大的一场决战,对于英雄而言结局只有成功或者失败;也可能是英雄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一场选择,这一选择将影响他的终身。
无论以何种形式展现,最后一场考验都是决定英雄之旅结局的最关键时刻,是整部电影的“高潮”部分。

21世纪奥斯卡体育电影的创作者们为英雄设置“最后一次考验”时更加倾向与以决战的形式来表现。
诚然,对于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电影而言,没有什么比一场激烈的体育比赛更适合作为电影结束前最后的狂欢了。

竞技体育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也能满足观众对“高潮”部分的期待。
但并不同于其他类型电影,这十五部电影的创作者在展现英雄结局时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结局。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21世纪奥斯卡体育电影中主角未能臝得最终比赛作为结局的影片并不在少数。

这些失败结局的电影在创作上摒弃了传统体育电影简单的励志故事模式,而是从另一种层面解析了英雄所拥有的体育精神,英雄在最后一次考验中尽管身处逆境却仍然坚持自我,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如《奎迪》中的阿多尼斯·约翰逊,尽管在最后的决战中输给了当时的轻量级世界冠军瑞奇,但阿多尼斯坚持战到最后一刻,并且他距离成为冠军只差了10秒钟;在比赛结束后,瑞奇也肯定了他的成就“你(阿多尼斯)是拳坛的未来。

”失败结局的奥斯卡体育电影超越了输与赢的二元对立,同样拥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让观者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物魅力和更加深刻的体育内涵。
改变人生的重要选择。
除了决战这一种形式,用最后时刻的选择来表现英雄是否通过改变真正获得了成长,这是考验英雄价值观的时候:他会依据旧有的习惯来选择,还是作出新的选择。

表面上英雄是在对两种价值观的选择,实际上是英雄对于“旧”的自己和“新”的自己做选择一-是选择重新回到过去那个失败的、有瑕疵的自己和经历了成长后的全新的自己。
在《极速车王》中,面对利奥和福特集团的步步紧逼,卡罗尔·谢尔比并没有听从他们的话将肯·迈尔斯召回,而是尊重肯·迈尔斯,将对赛车的掌控权交给迈尔斯。

在上一次面对这样的选择时,谢尔比选择了福特集团,没有将迈尔斯带去勒芒。
前后两次选择结果的不同,体现出了谢尔比的成长,在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后,谢尔比不再畏惧强权,而是坚持对迈尔斯的尊重和赛车运动的尊重。

而《百万美元宝贝》中麦琪用自己的毅力和努力实现了梦想,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掌声;如果她选择了苟延残喘的活着,无疑是回到了之前在餐馆里做服务员的生活状态一一没有尊严也没有未来,于是她选择用死亡维护自己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