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晚清的时候,中国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外交难题。西方列强不停地施压,硬要在中国设置公使,还想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面对这种情况,清廷创立了总理衙门,还任命了南北洋大臣。那这些大臣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他们和总理衙门有着怎样的关联?为啥要让两江和直隶总督来兼任这个重要职位呢?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晚清朝廷和民间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纷争以及权力的争斗,咱们这就来仔细瞧瞧。
【一. 职责雏形:两广总督兼任;】
在鸦片战争前夕,清廷专门派遣沿海的督抚去处理严禁鸦片从海口进入的事宜,给他们加重事权,还授予钦差大臣的名号。像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就被派为钦差大臣去了广东,第二年又担任了两广总督,由此开创了让钦差大臣办理海上交涉的先例。《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让伊里布当钦差大臣和英国人商议通商税课的事,耆英负责江浙闽三省通商的善后工作。等到伊里布去世后,清廷赶忙命令耆英赶赴广东,最后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把耆英调任为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
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耆英替清政府跟法国、美国等国家签了一连串的条约,由此开创了“钦差五口通商大臣”这个职衔。这个职衔由两广总督兼任,是清政府处理对外交往事宜的最高代表。其承担的职责涵盖了外交、通商等所有跟西方人交往的事务,在国内还得负责各省通商的后续事宜。但凡对外交涉出现争端,清廷也都把事情交给两广总督通商大臣去处理。

在咸丰年间,清朝廷为了阻拦外国使臣进入京城,屡次着重表明五口通商大臣的专门职责所在。皇上的谕旨着重强调这一点。这体现出清朝廷期望两广总督把控“中外交涉”的权力,也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解决各类交涉事务,占据中外交涉的主导位置。
不过呢,五口通商大臣的权力还是有不少限制的。其一,这权力主要就在广东那一个地方,对其他口岸的事儿反应不灵敏。其二,督抚对他的指令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另外,西方国家还绕过通商大臣直接去其他地方了,这样一来,广东的中心地位就受到了影响。其三,两广总督一个人兼着好几个职位,很难专门去管对外的事儿,办事的效率特别低。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五口通商大臣制度才不得不进行转变了。
【二. 内忧外患:列强逼迫与总理衙门的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后,英法联军把广州攻占了,这使得清廷不得不派钦差大臣到天津去和他们谈判。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打着“修约”的旗号,坚决要派公使常驻北京,想要插手中国的内政。清政府原本想着用“全免关税”之类的说辞,来阻止公使进京并在那里立足。但是呢,这个愿望很难达成,英法美等国家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态度特别强硬。
除了公使进入京城这一事项外,列强又提出了一连串新的诉求,像在沿海区域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许西方人在我国内地传教、实施领事裁判权等等。在列强的军事胁迫之下,清朝廷只得选择退让。1858 年 6 月,英法联军直逼天津,清政府无奈地和他们签署了《天津条约》,不太情愿地接纳了一部分条件。

《天津条约》签署后,各国公使接连进驻北京,西方的勘界委员也相继进入我国境内对通商口岸进行勘察。鉴于愈发严峻的形势,清廷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对外事宜。1861 年 5 月,总理衙门得以正式设立,由盛京将军英柔担任总理大臣,承担相关事务的管理职责。
总理衙门设立后,原先的相关制度有了重大变化。咸丰十年九月,钦差大臣桂良等人提议,往后各国事务的办理改在上海交由商人办理。到了次年十二月,清廷宣告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专门处理上海与各国的交涉事宜。就这样,南北洋通商大臣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其中南洋大臣在广东,北洋大臣在上海,分别负责南北的商务交涉工作。
与此同时,清廷对总理衙门的职权进行了严格把控。《钦定总理衙门事务馆章程》清楚表明,总理衙门仅仅是个“联络机构”。真正握有最终决策权的是内阁机构军机处,并且军机处的决议还得经过朝廷准许。总理衙门在体制上处于附属地位,和督抚阶层差不多,没权力直接给地方官员下达命令。所以,虽说叫“总理衙门”,可它实际上就只能作为中外交涉的一个联络部门,权力相当有限。
【三. 权力分野: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的关系】
虽说总理衙门被当作“洋务”的最高机构,然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它的权力是受到很严格的限制的。相较而言,南北洋通商大臣在对外交往事务方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依据《钦定总理衙门事务馆章程》所定,总理衙门的职能为“”。说白了,它就是个传递文件、给予咨询意见的部门,没权力做实质性的决定。真正能做决策的是内阁里的军机处,而且军机处的决定还得经过朝廷准许才行。所以,总理衙门在体制中是从属的,没资格对督抚下达命令。
相比而言,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力更为切实。身为广东与上海这两个重要对外窗口的最高管理者,他们把控着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接的关键路径,在实际的商务谈判中占据着主导位置。
特别是南洋大臣,其权力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没发生前,两广总督曾兼任过“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处理各省海口的通商事务。咸丰时期,清廷多次强调这一点。到了同治时期,清政府更是明确规定“两江总督例兼南洋通商大臣”。由此可见,南洋大臣在中外商务洽谈中处于关键地位。
北洋大臣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其职责在于引领地区性的对外交流事宜。清廷曾下达指令称“”。上海作为华北地区向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入口,北洋大臣在这一区域的重大外交事务上具备决策的权力。
除了具备对外交涉的权力外,南北洋大臣还握有处理地方涉外事务的权力。总理衙门只能和他们协商。要是产生分歧,就会由军机处直接做出裁决。所以,作为实际操作的人,南北洋大臣的看法常常起着关键作用。

当然了,并不是说总理衙门一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在重要的事情上,总理衙门是可以提出建议和办法的,能给中央的决策当作参考。不过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南北洋大臣实际权力的限制。这么一看,晚清的对外体制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况:总理衙门进行咨询,军机处做出决策,地方督抚负责执行,这形成了三级的分别,也出现了一种有限的权力互相制约的局面。
【四. 兼任之源: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的特殊身份】
为啥清廷会让两江和直隶总督去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这个重要职责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缘由。
在清政府看来,两江总督的职责极为重要。毕竟长江流域乃是中国的经济要害之处,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稳。所以,向来有两江总督“地位尊崇”的讲法,其地位仅在军机大臣之下。而在外交事务方面,两江总督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时候,清廷把两广总督耆英任命为钦差大臣,专门处理和西人通商的事情。等到了同治年间,清政府还明确下令了。从这些能充分看出,清廷把两江总督当作是进行对外交涉的重要人物。

直隶总督的对外职能起初表现在处理租借码头这事儿上。嘉庆年间,广东拒绝外国人租借码头,引得英国抗议,最后是直隶总督做出裁决,准许码头租赁。往后,直隶总督多次参与处置有关外交的事务,像耆英被调任为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时,曾让直隶总督暂代广东的相关事务。由此可见,清政府早就把直隶总督当成外交权力的重要承担者了。
在同治年间,上海变成了对外开放的重要地方,直隶总督的对外作用愈发重要起来。清政府让直隶总督同时担任北洋大臣,负责上海地区所有外交和商务方面的活动。尤其是北洋大臣不在的时候,直隶总督更是把该地区的对外事务全部管了起来。
两江和直隶总督由于兼任南北洋大臣,便能分别把控内河与沿海这两大交通要道,从而成为维持中外关系的重要力量。当然,清廷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有对中央集权的考虑,就是借由地方代理的形式,避免权力过多地向外分散。不过总体来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兼任,主要还是因为这两地在晚清外交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五. 权责失衡:权力纷争与制度困境】

虽说南北洋大臣在中外交往交涉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他们跟总理衙门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关系并不清楚明确,这往往造成了权力方面的争执和制度上的难题。
一方面,南北洋大臣靠着手中的实权优势,根本不理会总理衙门的指令。按规定,总理衙门得通过“协商”的办法跟地方大臣进行协调,要是有了分歧,得由军机处来做决定。然而,督抚们大多作风散漫,把总理衙门不当回事,常常违背其意见,擅自做主行事。
清同治八年,总理衙门让南洋大臣把收罚的银两解送交到军机处进行核查,然而却被广东巡抚陈宝箴给拒绝了。陈宝箴指责说:“这种类似的情况不断出现,南北洋大臣凭借着地方上的实际权力肆意行事。”
另一方面,南北洋大臣之间常常会因为权责划分的问题出现争执。比如说在清光绪十四年,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卫东,和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是否准许外国人购置房地产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他俩针锋相对,谁也不肯退让,最后没办法,只能让朝廷来亲自做出判定。
除了权力方面的争斗外,南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也有不同意见。像海关税收的征收、领事裁判权的管辖范畴等方面,他们双方常常出现矛盾。总理衙门会就此给出不少提议,然而大臣们通常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很少予以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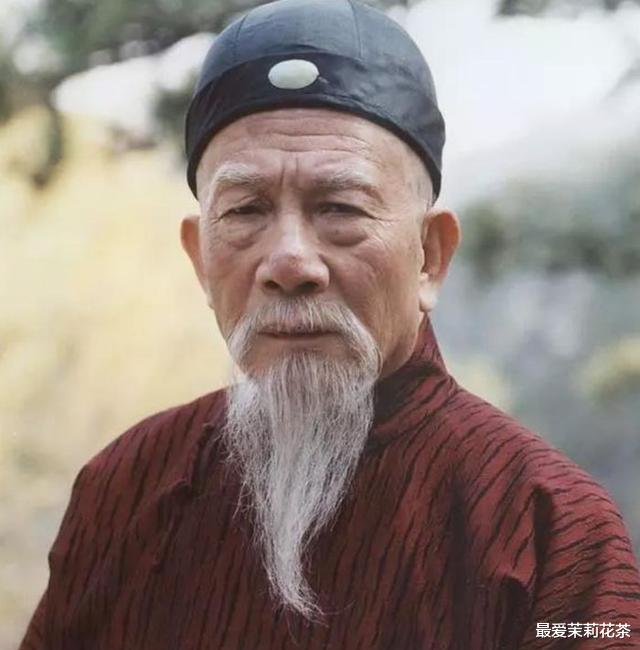
这种权力失衡情况的缘由在于,总理衙门的职责与权力出现了显著的不平衡。按道理讲,它作为“外交”的首要机构,权威性理应比南北洋大臣更高。但因为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总理衙门的权力仅仅局限在提供咨询建议方面,没办法直接向地方下达命令。再看南北洋大臣,他们不但兼任重要地区的总督,还把控着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实际权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
由于权责不平衡以及体制的僵化,总理衙门难以切实地掌控全局,往往只能在具体事宜上独自应对。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其与南北洋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让晚清时期中央和地方在处置外交事务时,屡屡出现矛盾冲突,对外政策也难以有效地予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