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正日喜欢电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在文字记载中,能够确认他亲自指导的电影,可以看出有三部:分别是《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女学生日记》。
《鲜花盛开的村庄》与另一部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都由同一个导演执导,两部电影均在1971年引进中国,成为当时朝鲜农村电影中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观众群落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其实,从金正日在我国出版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对《摘苹果的时候》的拍摄也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的强调组织的作用,直接转化为电影里的台词。
《鲜花盛开的村庄》这部电影更得到了金正日的大量参与,在他的文集中,对这部电影的人物设定、主题基调以及冲突把握,都有具体而细致的意见。
《鲜花盛开的村庄》是一部黑白电影,可看性不如《摘苹果的时候》,但是在当时故事影片已经停拍的中国影院里,还是得到了观众的热烈的追捧。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看起来节奏缓慢的农村题材影片,在中国观众那里,获得了如痴如醉的反馈。
在容尚谦著所著的《恰同学少年》(2016年版)一书中,作者写到:
朝鲜电影是最受我们欢迎,也是最追捧的电影。第一次看朝鲜电影是《鲜花盛开的村庄》,知道团部放映这部电影的消息,我和刘宝琦、陈列、廖新生等几个人,收工后从前线工厂出发,两个多小时走了30多里路,去享受这顿精神大餐。团部大操场人头攒动,挤在人堆里的我们努力为自己开辟一个立足之地,慢慢地随着大家席地而坐。幕布上出现画面,响起音乐时,全场安静了下来。很久没有看这么吸引人的电影了,很久没有看到生活气息如此浓厚的电影了,人们完全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不时发出笑声,这真是一部让人感动、让人难忘的电影,也是从这部电影,我们认可了朝鲜影片。在我们心里,那时朝鲜比中国好多了,鲜花盛开,衣着鲜亮,生活富足,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影片像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抚慰着我的心灵,让我们从斗争的语境中松缓下来,有一种宁静,一种和平,一种摆脱了现实烦恼的惬意。我只是奇怪,朝鲜那么一个小国家,怎么会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我们怎么就拍不出来呢?随着这部电影,“600工分”这个新词迅速流传开来,不但体态丰满的姑娘一律成了“600工分”,也成了男同胞之间互相打趣的新词。
在王安忆所著的《69届初中生》中,也提及了电影里的一个细节:“杨小萍的个子有一米七二,很匀称。圆圆的脸,一双细细的然而却是双眼皮的眼睛,嘴唇小小的、厚厚的,白白的皮肤上有一些黑黑的痣。大伙儿在一起谈起找对象的事儿,她总爱教训、挑剔人家重外貌的人:“要那么漂亮干吗?漂亮的脸蛋儿不会出大米。”这是从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听来的一句话。人家便反击道:“漂亮的脸蛋会出芝麻。”于是她哑口无言。

电影里的一个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台词,竟然成为中国观众挂在嘴边上的稔熟俗语,也算是一次无心插柳的意外。
《鲜花盛开的村庄》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表现一个农村青年,不安心农村工作,一心想到城里去。
放在今天,这个青年的选择,也算是人间正道,但在影片表现的五十年代,战争刚结束,农村亟需建设,这样的弃农经商,显然是违背时代的需求的。
这样的扎根农村的题材电影,也是当时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一个占据主流地位的类型。
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中国农村与朝鲜的农村一样,都占据着视角的中心位置,农村里云集着最精英的人物,这也使得农村的男男女女的爱情选择,成为影视作品里动人心弦的一种流行色。

男孩与女孩走在乡村里的土路上的一段浪漫情怀,能够给人一种世界的中心的感觉,全世界的目光,都似乎在观望着这对情窦初开的男女之间的心灵撞击,这个时代是农村占据着国家重要中心位置的时代。
《鲜花盛开的村庄》正反映了这样的时代,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共鸣的。
影片里,用以说明农村具有坚守下去的意义的理由,是战争刚刚结束,无数的人们用自己性命换来的土地,值得去建设它。
这是用战时的眼光,来看待坚守乡村故土的意义。
同时,电影里还通过忆苦思甜,来帮助意图逃离乡村的农村青年实现思想转变。

这种转变方式,可以说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节套路模式。
而爱情,也在农村青年的前途选项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有意思的是,与说一不二的扎根农村主题的坚定性相比,在影片里的爱情选项上,却明显带着一种嘲弄劳动的意味。
这便显得有一些奇怪。

一部歌颂扎根农村的影片,但是在潜在的审美的意图上,却张扬的是美貌决定爱情的取舍。
可以看出,人生观与爱情观,用了两个不同的尺度。人生观必须符合时代潮流,那就是要坚守农村这块正确的选项,但在爱情观上,却迁就的是人的审美习俗,甚至在这种习俗里,抛开了人生观对劳动的首肯。
《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那个农村青年,父亲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比较胖,眼睛小,实在称不上貌美如花。

农村青年的父亲却很欣赏这个胖女孩,说:“越看越喜欢,嘴唇厚,说明她不爱说话,胖说明她身体结实,听说她去年挣了600工分,一个工分三斤半米,这就是二吨多粮食,另外还有现钱。”
父亲的爱情观,其实十分匹合农村的实际,那就是能创造财富,带来工分,促进增产,这样的劳动力,本该是农村里的最美丽的一种峰巅,但是这种爱情观,在电影里却受到了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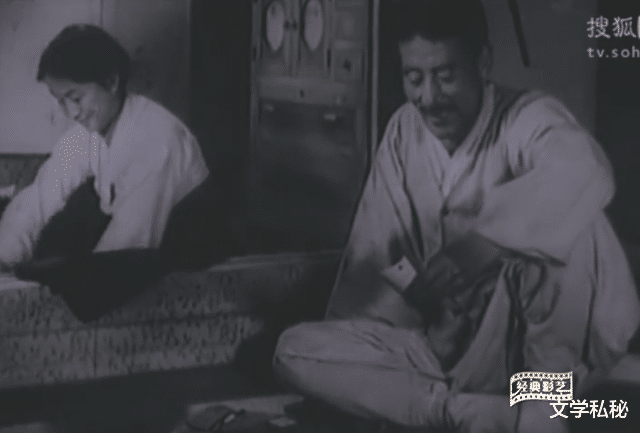
这与电影的主题是相悖离的,电影宣扬的是农村的朴实、苦干与坚守,而爱情观,却宣扬的是美貌至上。
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矛盾着的电影主题与审美的偏离。审美打了电影主题的耳光与嘴巴。

电影的主题,没有促成多少的现实价值,扎根农村的宣扬,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回应,倒是电影里的对丑女的唯生产至上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如这部电影带来的副作用一样,就是在当时,也没有几个观众,受到电影里的扎根农村的主题的耳濡目染而身体力行,反而是吃苦耐劳的丑丫头不能娶的理念,一度时期挂着中国观众的口头上。
电影里的农村青年,最终选择了村里的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主角,留在了农村,也收获了美丽的爱情,电影完成了一个配合主题的乌托邦逻辑演绎。

电影里的这个温柔贤淑的女主角,正是一前一后上映的另一部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的姐姐的扮演者,在《摘苹果的时候》里,这个姐姐把一个朝鲜女孩的那种羞涩娇俏的形象,塑造得楚楚可怜,当时的中国女观众,也对这个女孩塑造出的那种甜美温润的女孩形象艳羡不已,把她称着是朝鲜电影里的最漂亮的女孩。
这样,农村青年在农村里得到的最大报酬,就是有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相伴,这样,农村的艰苦现实,在电影里作了有效的回避,情感上的满足,给电影铁定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这也是农村片里的一个策略,那就是在艰苦的农村里,有着一个天姿国色的美女相伴,这样,农村的困乏,便得到了缓释与缓解。
柳青的《创业史》则写得比较残酷,把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仪的女友给支走,嫁到城里去了,男主角只好找一个大龄女干部当妻子,所以,柳青的《创业史》一度时期受到批判,因为他残酷地预示着农村是容留不下一个漂亮的女孩的。
这是一种农村的真实,但是,显然与时代的主题有偏颇。后来浩然在农村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都把最可爱的农村女孩设定成一个扎根乡土的形象,至少符合小说里的主题对农村生活主舞台的设定基调。

到了路遥的小说里,农村男青年的心仪对象,都是城里的女孩,农村女孩已经不再是乡村里的精华,之后,农村女孩的中心地位,日益丧失,只能成为文学作品里的一个打工者的角色,像《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里这样的农村女孩沾着她们的美丽容颜而给乡村铺上鲜花般的装饰的类型,已经难以觅踪了。

借此,通过《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一个关于胖姑娘的搞笑场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为主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共同的艺术设定,那就是一方面在电影里张扬着农村的价值意义,但是在审美上,却嘲笑着农村的常态化的价值原则,比如胖,能挣工分。
当有一天拉平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的时候,美丽将不再与劳动挂钩,而单纯地具备了自身的独立的价值。

这应该是这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留给我们的一种可以看清历史变迁与烙印的化石意义所在吧。

横笛
主题歌有名,中文同曲歌叫沈阳我的故乡
鱼之乐
很少见到这么好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