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观念在宋代的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这一孕育过程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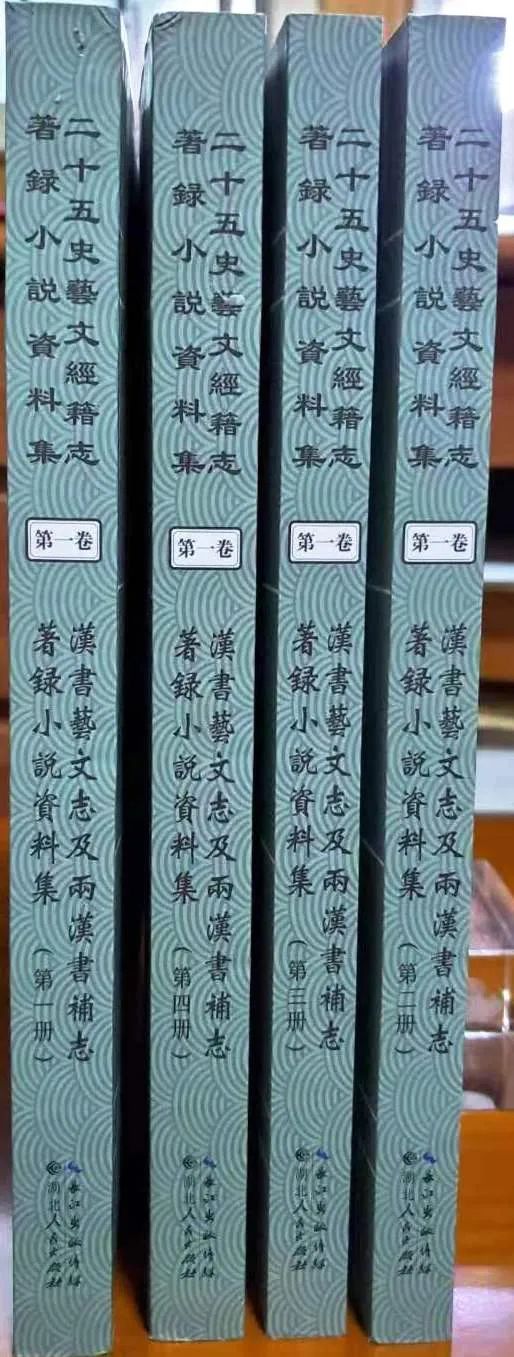
《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了先秦至西汉的小说家及其作品,并给小说家下定义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
这里不仅追溯了小说家的来历,而且概括了他们作品的特征及其价值,成为后来史志子部小说观念的理论基础。
其实,这一观念中也包含有通俗小说观念的某些因子,这种因子不仅体现在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些对小说作品特征的描述中,而且从小说家所从出的“稗官”的职掌中也能够反映出其与通俗小说的联系。
“小说家出于稗官”之说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然而,人们对这一说法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至今也没有消弭。
章太炎、胡适、傅斯年、吕思勉、余嘉锡等都参与过讨论,观点各不相同。章太炎是肯定论的宗主,胡适是否定论者的代表。余嘉锡则作《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力主《汉志》之说可信,认为稗官即小官,指“天子之士”。他们的讨论到今天仍然有重要影响。
笔者曾撰《稗官新诠》和《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二文予以讨论,试图弥合分歧,以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
笔者指出,魏初学者如淳释“稗”音“排”,是汉魏读音,实兼释义。“稗”即“偶语”,亦即“排语”、“俳语”、“诽(音排)语”,也称“偶俗语”,其表现为民间与朝政相关的谤言、谣谚、赋诵等。“稗官”可释为“小官”,但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先秦两汉“以偶语为稗”,提供“偶语”服务的小官自可称为“排官”,亦即“稗官”。

《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
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书,可以证明稗官乃指县令长及长吏以下之属官,传世文献也证明稗官为小官之通称,并不局限于“天子之士”。上古“稗”音“排”,秦汉以“偶语为稗”,西周传留有“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而师、瞍、瞽、矇、百工等即是为君主管理和提供“排语”、“诽语”或“偶俗语”服务的“稗官”。
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则是春秋时期服务于诸侯公卿的“稗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不仅揭橥了小说家与师、瞍、瞽、矇、百工等的身份联系,也提示了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文体上的关联。[2]
由于“俳优”也是“稗官”,而“俳优”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些小说史家以“俳优小说”作为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一些戏剧史家则以“优孟衣冠”作为中国戏剧的主要源头。
“俳优”省称为“优”,其中又细分为俳优、伶优、倡优等类型。有关“优”的传说可以追溯至很早,至少可以追溯至舜帝时的乐正夔。“‘古优’在后来的发展中有过两次重要的分化,对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次是巫觋与乐人的分化,一次是乐人内部旧乐人与新乐人的分化。前者使得乐人的社会地位降低,成为巫觋的附庸;后者使得乐人的结构改变,形成雅乐与俗乐的对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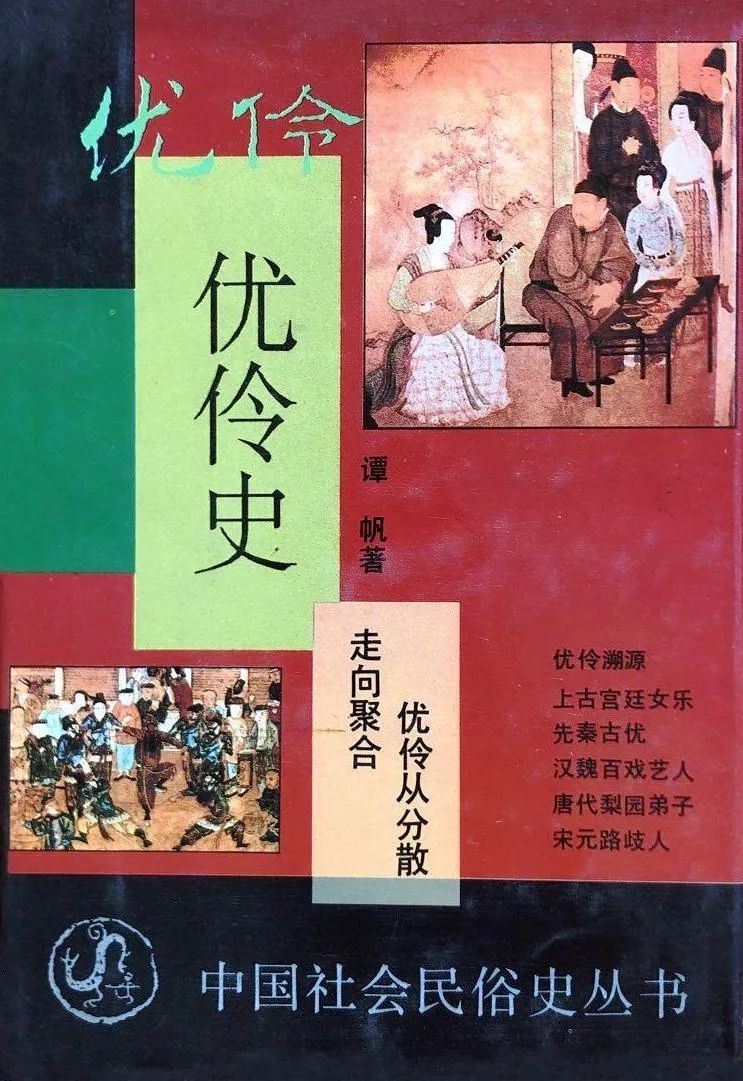
《优伶史》
《汉志》“小说家出于稗官”的判定,实际上囊括了师、瞍、瞽、矇、百工等人的创造,包含有民间文艺和通俗文学的内容,使得后来的通俗小说家们也能够从《汉志》对小说家的定义中找到其阐述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依据,罗烨《醉翁谈录》对小说的定义有《汉志》的明显影响,就是很好的例证。
“俳优”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活跃,他们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各种滑稽表演,进行讽谏或提供娱乐,丰富了统治者的文化生活。由于其“俳语”多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本质上带有民间文化的色彩,因此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源头。中国通俗小说和戏曲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滥觞。
事实上,通俗小说和戏曲在中国古代长期被看作是一家,并不强行作出分别,直到近代早期也仍然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俳优的表演,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艺的发展,“俳优小说”也就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俳优小说”不仅受到民众的青睐,而且得到一批追求创新的正统文学家的喜爱,这从曹植见邯郸淳时“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可以窥见端倪。邯郸淳是汉魏之际的书法家、文学家、游艺家,曹植初见邯郸淳,向其展示才艺,包括“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 [4],说明“俳优小说”是他们的共同爱好。
有人说,“俳优小说”就是说笑话,这一看法可能并不正确,因为笑话都是简短的,从来没有笑话达“数千言”,且笑话只会是“讲”或“说”,而不需要“诵”。

《曹植集校注》
其实,曹植所诵“俳优小说”是俗赋,是早期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样式。俗赋从先秦至两汉,一直在民间流行着,除了俳优的俗赋表演,还有文人的俗赋拟作,其发展未尝中断。
例如,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就是民间流传的俗赋文本。北京大学收藏的抄写于汉武帝时期的竹书《妄稽》是比《神乌傅(赋)》更早的俗赋文本,共100余枚简,3000余字,叙述一个士人家庭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
敦煌佚书《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也是民间俗赋,这些赋采用对话形式,有一定情节,对话部分多用四言,叙述多有六言,基本押韵,语言通俗,风格诙谐幽默。
《燕子赋》最长,3000余字,《韩朋赋》近3000字。王国维曾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些作品称之为“通俗小说”,向大家做介绍。[5]原来人们皆以为它们都是唐代的产物,而1979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批散残木简,其中有《韩朋赋》早期传本残简,可证敦煌佚书俗赋来源甚古,可能早到汉代。

《俗赋研究》
其实,俗赋在汉代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也受到部分正统文学家的欢迎,汉代学者仿制俗赋的作品也不少,如王褒的《僮约》、《责须髯奴辞》,扬雄的《逐穷赋》,傅玄的《鹰兔赋》,束皙的《饼赋》,蔡邕的《短人赋》等,都是模仿俗赋之作。
而曹植自己就创作过拟俗赋《鹞雀赋》。因此,曹植所诵的有“数千言”的“俳优小说”应该就是俗赋,而“诵”俗赋是俳优表演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说是汉代通俗小说的口头表达形式之一。曹植在邯郸淳面前用“诵俳优小说”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也表明“俳优小说”在这些关心民间文艺和通俗小说的学者们心目中是有相当分量的。[6]
“赋”是汉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它吸收了诸多文体之长,形成了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等各种体式,内容上也有体物、抒情、叙事、寓言、谐隐等诸多种类。而俗赋则以叙事类、寓言类、谐隐类诗体赋和散体赋为主,运用日常生活的素材,采用口语化的表达,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色。
以俗赋为主体的汉魏“俳优小说”延续了先秦“稗官”利用“排语”、“俳语”、“诽(音排)语”以反映民间对于朝政的谤言、谣谚、赋诵等的传统,又汲取了汉赋的艺术经验,使通俗小说得到很大的发展,也酝酿着通俗小说观念的突破。
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时期,出现了“唱导”等讲经形式,“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7],有讲有唱。
这种转变了佛经原典形式的讲经文,当时人称之为“变态”,隋唐人称之为“转变”,也称其文为“变文”。“变文”采用了佛经用散文叙说、用偈赞歌唱的文本形式,也吸收秦汉以来流行的俗赋和南朝的俗曲(变歌)的表达技巧,达到了使佛经通俗化、故事化、民间化的效果,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敦煌变文选注》
“唱导”最初是由高僧大德向出家人讲唱经文传授教义,故也称为“僧讲”或“尼讲”。后来僧人利用“唱导”向俗众讲唱佛经故事或通俗故事以邀布施,那当然就是“俗讲”了。因为“俗讲”是由“僧讲”演化而来,它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为了吸引信众,照顾男女老少的需要,俗讲僧在俗讲时一般都要把所讲故事画成图画,然后根据图画来讲解。
由于俗讲本不在于“类谈空有”,而是“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8],所以世俗的内容越来越多,以至后来有不少故事与佛教毫无联系,只是一些街谈巷议的新奇故事,如文溆僧所讲“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9],这就与当时流行的“俳优小说”、“市人(民)小说”没有什么差别了。
俗讲僧为了吸引信众,多聚寺资,自然要想方设法把故事讲得生动,适合普通信众的文化需求和欣赏习惯,而各寺院之间的竞争也必然激烈,这就促进了“俗讲”艺术的发展。受其影响,民间“说话”伎艺也迅速地发展成熟起来。
汉魏以来通俗小说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这一认识变化在《隋书·经籍志》中有了清晰的反映。

《隋书•经籍志》
《隋志》子部没有像《汉志》那样给小说家下定义,而是直接给小说下定义,因为这时创作小说的已经不是“稗官”,或者说不能用“稗官”来囊括,故很难为小说家定义。而小说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倒是需要加以定义。
于是,《隋志》将小说定义为:“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0]
《隋志》不再坚持《汉志》的“小说家出于稗官”之说,而是直接将小说定义为“街说巷语之说”。
这样定义“小说”虽然与《汉志》并不矛盾,且“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也有解释小说出于“稗官”之意,但是,《汉志》所强调的是王官之学对社会言论的有效管理,而《隋志》则更注重民间言论的多样化表达,并且特意将这种表达与《周官》的诵训和职方氏执掌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所掌管的正是小说所要反映的内容,即地方历史风情和民间风俗。
这样一来,《隋志》所定义的小说,其实就包含了汉魏以来的“俗赋”、“俳优小说”、“俗讲”、“说话”等各种民间伎艺,至少在观念上不排斥这些通俗文学,自然也就等于可以接纳通俗小说为其成员。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隋志》虽然对汉魏以来的通俗小说在观念上有所回应,但是,《隋志》小说观念仍然主要体现的是士人小说观念,而非通俗小说观念,它与《汉志》一脉相承,都强调诸子之学来源于王官,服务于政教。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
《隋志》子部总序云:“《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11]
明确将小说与儒、道并称,认为它们都是“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这正是正统小说观念的核心内涵。直到南宋罗烨等人,才将通俗小说定义为用日常口语演说故事,娱乐大众,完成了通俗小说观念的建构。此点上面已经说明。
注释:
[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2] 参见拙作《“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2013年第3期)和《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 王齐洲:《论古优的来历及其分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2015年第4期。
[4]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云:“太祖(曹操)遣(邯郸)淳谒(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
[5] 参见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考古学零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6] 参见拙作《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
[7]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9页。
[8] 【日】释圆珍:《佛说观音普贤菩萨行法经纪》,《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227页。
[9] 【唐】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10]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2页。
[11]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第1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