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炉上的火舌舔着铁钩子,三只青椒串成一串,在蓝烟里慢慢蜷缩。母亲总赶在菜站关门前买回蔫巴巴的灯笼椒,边角带着虫蛀的小孔,倒便宜了粮本户的我们
铁钩是父亲用自行车辐条磨的,弯折处还留着车链油的黑渍。青椒皮在高温下爆开细纹,像旧海报受潮后皱起的波纹。母亲用火钳翻动铁钩,焦糊味混着辛辣窜进鼻腔时,我总忍不住打喷嚏——那是我童年的警报器,预告着即将出锅的美味。


烧透的辣椒浸在搪瓷盆里,表皮浮起焦褐色的气泡。母亲的手指在凉水里一蘸,趁热撕开椒身,滋啦声里腾起白雾。灰绿的椒肉渗出汁水,混着蒜泥、盐粒在铝饭盒里拌匀,最后淋一勺珍藏的菜籽油。油星子渗进焦皮裂缝的刹那,整间筒子楼都响起吞咽声。
最奢侈的是父亲带回猪油渣的日子。凝成乳白的脂块在饭盒里化开,包裹住每一丝烧椒纤维。馒头掰开的瞬间,麦香裹着焦香扑上来,咬下去是酥脆与软糯的厮杀。油渣的荤腥被炭火气驯服,竟吃出几分火腿的咸鲜。
上初三那年,我在煤炉边偷师。火候没控好,青椒成了黑炭。母亲把烤坏的辣椒埋进酱油拌饭,焦苦奇迹般转化成烟熏香。她红肿的手指在冷水里摆动:"烧椒要留三分苦气,像人过日子。"

如今我用喷枪复刻当年的味道,青椒在蓝火中均匀起泡,却再撕不出那种粗砺的纤维感。超市买的薄皮椒太娇气,烤完只剩一滩软烂。女儿捏着鼻子喊呛,她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夏夜里,我曾把最后一口烧椒馒头塞进妹妹嘴里,两个人就着月光舔净铝盒上油亮的痕迹。
冰箱里冻着母亲寄来的玻璃瓶,标签是她用毛笔写的"特辣"。拧开盖子的瞬间,那股混合着煤灰与铁锈的焦香漫出来,阳台上晾晒的衬衫突然变成三十年前滴水的工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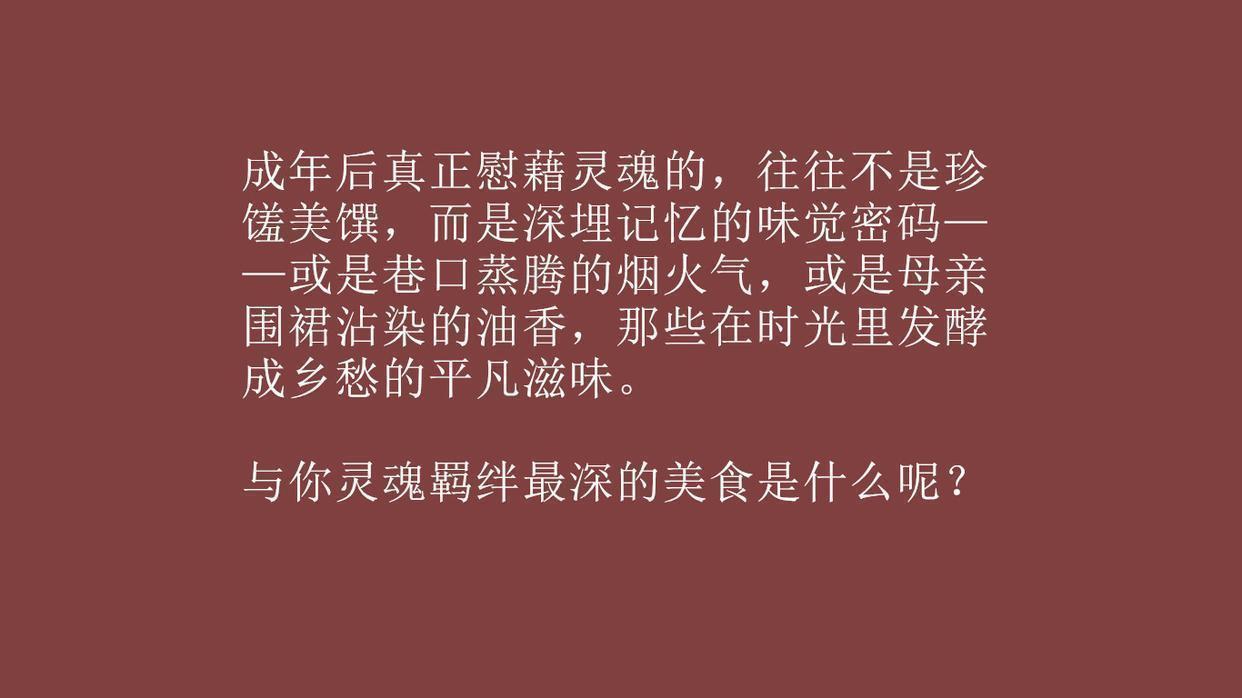
每日一个美食治愈小故事,若这些带着油盐酱醋香的故事曾牵动您的舌尖乡愁,诚邀您点击关注,愿这些故事能给您带来一缕暖光。
最后想厚着脸皮撒个娇~嘤嘤嘤~求鼓励~求关注~求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