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39年那会儿,大学问家欧阳歙可真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就像坐了一趟刺激的过山车。
年初时,他因为“举荐有才能的人,并且在治理上有显著成绩”,从汝南太守升为了司徒,这可是三公里面的一个大官。但没想到,到了年中,因为“度田”这档子事儿,他惹上了大麻烦。说是他上报的田地数目不准确,光武帝刘秀一听,直接把他给关进了大牢,还打算要了他的命。
欧阳歙虽然身陷囹圄,但心里头估计还没跌到谷底,毕竟他背后有个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八代书香门第”,在读书人堆里,他那是相当有面子。听说光武帝刘秀打算要了司徒欧阳歙的命,太学生们坐不住了,一块儿上书求情。更绝的是,有个叫礼震的太学生,还放出话来,说是情愿自己替欧阳歙挨那一刀。
不过,尽管有很多人出面求情,光武帝刘秀却依旧铁石心肠,一点都没动摇。对于这件事,他的立场非常明确:欧阳歙非得死不可。

欧阳歙的离世仅仅是个引子,接下来,这个新兴的国度即将迎来一场残酷的风暴,就像是大雨倾盆,带着浓烈的血腥味。
说到推行“度田令”这事儿,光武帝刘秀那是铁了心。他本身就是豪族出身,但为了立规矩,不惜拿十几个太守那些高官开刀,给全天下的豪族们打了个样:你们可以捞钱,但得按规矩来。谁要是敢乱来,不讲规矩,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条命吧。
刘秀建立新朝那会儿,他和大学问家还有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家族做了个约定,这个约定真的挺管用,让东汉这个大家族掌权的朝代没像后来的晋、宋,还有南朝那样,变得又弱又保守。刘秀和他儿子一开始搞土地丈量,就给这些大家族立下了不少规矩,这些规矩啊,对整个东汉时期各个势力的做法都有很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了三国时期,那时候天下可真是乱得很。
【豪族王朝】
新莽朝快结束的时候,天下乱成了一锅粥。好多股力量都跳出来争地盘,就像个大战场。刘秀他们那帮人能这么快站稳脚跟,关键就在于他们瞅准了当时最有分量的角色——豪强大族,而且很快就拉拢到了这些豪族的站边。
刘秀原本是南阳的大户人家,他身边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得力助手,就是那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多数人也都来自显赫的家族。从这一点来看,东汉实际上就是一个地道的贵族统治的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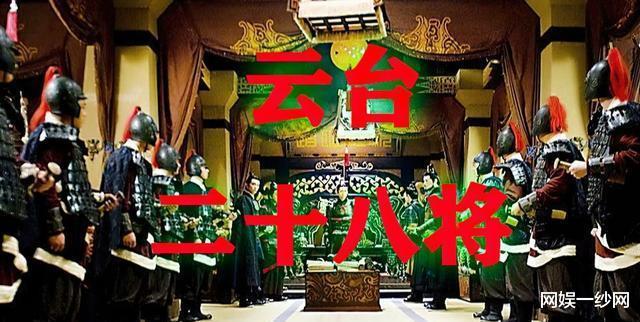
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老爱把人分成各种各样的圈子,还老想着同一个圈子里的人想法都一样,目标也一致,做事还会步调统一。但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根本没法说明白真实世界里那些复杂的关系。
聊到“豪族”这词儿,咱们现在老觉得它跟平民不对付,就好像社会被分成了“豪族圈子”和“平民圈子”,两边儿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但要是真这么琢磨,那光武帝刘秀干的事儿可就说不通了。毕竟,刘秀作为豪族里的“大哥大”,按说该带着豪族一块儿欺负平民才对,咋会反过来对豪族动手动脚,下狠手呢?
社会挺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变。光武帝刘秀对待那些大家族,一开始主要是想拉拢他们,但后来就变成了打压。这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从打天下的阶段,转到了治天下的阶段。
在创业打天下的那会儿,刘秀和那些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主要是绑在一条利益船上的。但等天下安稳下来,当上了皇帝的刘秀,也就是光武帝,跟那些大户人家的利益纠葛就开始浮出水面了。
每个一统天下的集权王朝,都得有个靠谱的财政体系来让国家机器转起来。在古代,大伙儿都靠种地过日子,所以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土地,王朝的财政基础自然也得扎根在土地上。
新莽政权垮台快得很,主要就是土地问题没搞定。刘秀接手后,建了东汉,废掉了新莽那会儿不接地气的土地规矩。不过话说回来,土地这事儿,东汉新朝廷也得直面,躲是躲不掉的。
在搞定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时,刘秀没像之前的王莽那样,上来就搞个大动作。他先做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量地数人,也就是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

如今国家刚安定下来,土地多的是,刘秀琢磨着,这条简单的规定应该挺容易落实的。可他没想到,人的贪心可真不小。好多大家族用实际行动给刘秀上了一课:他们不光想吃刘秀划给他们的那块蛋糕,还想把整个桌子都清空,一点不剩。
【劫贫济富】
刘秀,也就是光武帝,他为啥要让大家量地呢?原因其实挺直接的:国家刚稳定下来,得把土地和人口的情况摸清楚,得有个明明白白的账本。
掌握了详尽的土地和人口数据,国家就能有依据地制定税收政策,并合理安排劳役与兵役的任务。
王莽掌权那会儿,对土地问题下了两剂猛药。头一桩,就是严禁土地被大户吞并;第二桩,则是把那些豪门大户手里的土地全给收了回来。这两手操作,直接戳到了那些大户们的痛处,他们肯定得抱成团来反对啊。
王莽建立的新朝,很快就玩完了,只撑了一代就没了。说起来,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他在土地政策上太不接地气了。
刘秀,出身名门望族,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硬性地不让大户人家兼并土地根本行不通。因此,他搞了个比较宽松的土地法子:大户人家可以多置办些田地,但得按自己实际占有的地亩数老实交税。
到了东汉时候,税收制度基本上是照着西汉来的。那时候,大家主要交的就是地税和人头税。那些大户人家,人多地也多,不过要是按人头和地来算比例,他们其实比一般的自己种地的农民交得还少。因为地税加人头税一起算,大户人家交的总数,比起自耕农来,那可真是少多了。

刘秀心想,那些自称儒生、总爱谈仁义道德的地方大佬们,理应能接受这个对他们挺友好的规矩。他们应该会配合度田政策,赶紧让社会生产恢复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涨起来,那些有钱有地的大家族,财富自然也会跟着嗖嗖往上涨。
可刘秀压根没想到,那些地方的大佬们心里另有盘算:虽说土地税不算太重,但他们琢磨着,要是能给负责清查土地的官员塞点好处,把自家的部分田地给瞒报掉,这样一来,只要瞒下来的地省下的钱比送出去的贿赂多,那这生意可就划算了。
官商相互勾结,这可是个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了。咱们得明白,这事儿可不光是官员和商人之间那点事儿,它带来的后果,往往远超政策制定者的预料。
国家要清查土地,有钱有势的人想隐瞒土地,而有些官员呢,就想着捞油水。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国家在清查土地时,心里其实对各地的土地数量有个大概的底,所以那些想帮有钱人隐瞒土地、从中捞好处的官员,也不敢做得太过火。最终上报的土地数量,得跟国家心里那个数差不多才行。
一边是有人想偷偷卖掉田地赚黑心钱,另一边呢,账本上的数字又得对上,这可咋整?有招儿,啥招儿呢?就是“再让老百姓多受点苦”。
在东汉时候,官员们量地的时候,把老百姓自家住的房子、围的院子都算作了田地报了上去。这样一来,普通农户的地被多算了多少,那些大户人家的地就相应地少算了多少。这么操作一下,大户和官员们不就都捞到好处了吗。
把这样的账本呈上去后,朝廷乐开了花。他们瞅见的账本,简直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大户人家手里的地不多,自个儿种地的农民手里地挺多,这经济状况,健康得很。那些大户和当官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毕竟他们在丈量土地这事儿上,可是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上面的大官到下面的小官,个个都挺开心,就是那些自己种地的老百姓心里不痛快。土地多少,那直接关系到要交多少税。虽说光武帝刘秀老说税收要轻,实际上税率也确实不高,但问题是,老百姓手里的土地被硬生生算多了,这不就等于悄悄涨税了嘛。在古代,这些自己种地的农民,日子是最难过的。朝廷的税、劳役、当兵,一个都逃不掉,还得受地方官府和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欺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糊口。现在,又用这种离谱的方法给他们“加税”,他们对朝廷当然是一肚子怨气。
起初,光武帝刘秀对这事儿一头雾水,不过地方上的官员自个儿露出了破绽,让刘秀察觉到了不对劲。经过一番细查,刘秀慢慢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搞清楚了。
得知地方官员和大家族借度田令之机中饱私囊,刘秀火冒三丈,立刻动手在全国搞了个大搜查。新上任的司徒欧阳歙,因为收了人家的好处,帮着大家族躲过度田检查,结果被光武帝刘秀毫不留情地抓起来杀了。
刘秀处理掉欧阳歙这个代表人物后,并没打算收手。仅仅是因为度田事件,就有好几位太守被牵连丢了性命,数量加起来有十多个。

刘秀铁了心要告诉全天下的人,度田这事儿得实实在在干,一点商量都没有,没得商量。
见皇帝动真格的,大多数地方官员不敢再为点小利益去包庇那些豪门大族了。豪门大族们见软的手段没用,就打算给光武帝刘秀来点“硬的”。于是,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这四地的豪门大族干脆直接宣布:起兵造反了。
【土地密码】
或许有人会觉得不解,就算如实上报田地,大户人家顶多就是多交点税,而且这税钱还不一定得他们自己掏,他们只需把田租往上一提,轻轻松松就能把这笔开销转嫁给租地的农民。这样一来,大户人家何必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起义呢?
这个问题挺棘手,要解答它,咱们得先弄明白土地是怎么一点点被少数人占去的。
从春秋战国那会儿起,各国都迈进了自家种地赚钱的年代。这个自家种地啊,就是说朝廷把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分给农民去种,农民呢,得给朝廷交点税,还得去服劳役、当兵啥的。
每个人的本事不一样,脑子转得快慢也有区别。时间一长,有的人家里钱多了起来,有的人不光没钱,还欠了一屁股债。这样一来,那些日子过得滋润的,就用自家多余的钱去买那些过得紧巴巴的人的地,慢慢地,土地就都被少数人给占去了,这就是土地集中的事儿出现了。
这种土地集中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土地兼并的一个最基本形式。不过说实话,在真实世界里,土地兼并的情况很少会完全照着这个理想化的路子走。
尽管人的聪明程度不一样,但大体上看,人都是讲道理的,他们会权衡好坏来做出自己的选择。
土地对自耕农来说,那可是最值钱的家当。按常理说,除非是自耕农糊涂到家了,不然谁会傻到把自己的土地给卖了?能让自耕农狠下心卖地的,就俩原因:要么是实在没法活了,要么是觉得卖了划算。而这两个原因,它还互相有关联。要达到这种地步,光靠市场上那些买卖可不行,还得有政府插一脚才行。
说实话,帝国的头头们巴望着老百姓大多是自个儿种地的农民,这样一来,国家收税多,需要人手时也好召集。想让这事儿成真,那就得保证农民们能靠种地活下去。说白了,就是给农民分点儿地,让他们种种庄稼,交完税、服完劳役和兵役后,还能养活家里人。
别想着这事儿能轻易搞定,你瞧瞧中国这两千年的皇朝历史,能真正实现这目标的时光,估摸着连一成都占不上。

这种自己种养、啥都靠自己的小农经济,说起来挺好,但实际上很难一直撑下去。挺有意思的是,那个特别想让老百姓都当小农的国家,结果却老是让那些小农破产,或者自己把地给卖了。
说白了就是,前面说了,自耕农只有在没办法或是觉得卖地更划算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地给卖了。那什么情况下自耕农会最没办法呢?很显然,就是国家用暴力手段逼得他们没法活。你看,从秦二世那朝代垮了之后,后面的皇帝都说自己收的税少,可实际上呢,每个朝代一开始,国家的权力机构就越大,要养的人就越多。为了养活这么多人,朝廷就得想尽办法收税。
说到征税,就得考虑到底该向谁收。虽然每位皇帝都盼着能从有钱人那里多捞点税,但权力这玩意儿挺玄乎。经过各种权力的运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有钱人靠着能搭上权力的快车,少缴了不少税,反倒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跟权力沾不上边,结果税负重担都落到了他们头上。
在自个儿种地挣钱的日子里,各级官府的五花八门税费啊,那可是专门盯着那些本本分分耕田的农民朋友们。说起来道理也简单,只要你有地在那儿,你就没法躲,收你的钱自然是最顺手的事儿。
通常情况下,自耕农靠着自己的田地过日子,一般不会破产。但历史多半时候都不那么太平。因为各种各样的重税杂费,有些自耕农就会想:这地留着有啥用,还不如没有呢。
手里有地,那就得交好多乱七八糟的税。但要是没了地,去给大户人家当佃农,好处可不少。一来,土地税就不用交了。二来,大户人家或许还能帮忙遮掩身份,这样一来,人头税、兵役、徭役这些也都能省了。这么一来,佃农们就只需给大户交点地租,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税、徭役、兵役比起来,这买卖简直太值了。
你以为隐瞒人口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靠暴力强迫佃农们不加入国家的户籍管理,但真相可能是这些佃农主动请求地主帮忙,让他们从国家的户籍里去掉名字。
现在,咱们详详细细地把土地兼并这事儿说清楚,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儿明白,为啥那些大家族就算豁出命去,也得藏着掖着自己的土地呢。
新莽时期的大动荡结束后,东汉这个新兴王朝建立起来。那时候,人和土地之间的矛盾还没那么尖锐。东汉政府握着好多公家的田地,打算白送给老百姓去耕种。
东汉早期,光武帝刘秀沿用了汉文帝那套让百姓休息、少交税的政策。那时候,官府收的税啊费啊不算离谱。所以,对老百姓来说,当个直接向朝廷交税的自耕农,其实是个挺不错的出路。
人类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以前很多人宁可抛弃朝廷正规户籍,去给大户人家做佃户甚至家仆,这是因为相比之下,这样做比当朝廷的自耕农能赚更多。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回到朝廷的户籍系统,当个有自家田地的自耕农,看起来更加划算。所以,要是朝廷能够顺利地把土地和人口都统计清楚,那肯定会有大堆佃户离开大户人家,选择接受朝廷分的土地,自己去种地。
结果,碰上个挺棘手的事儿:虽说土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宝贝,但对当下的大家族来说,它反倒可能成了累赘。你得找人种地,地才能生钱嘛。以前,这些大家族靠雇长工来种地,钱是哗哗地赚。可要是长工们都跑了,光凭他们自己,哪种得了那么多地?地没人种,自然就没收益。可土地税是雷打不动的,种不种都得交。为了减少点损失,他们琢磨着给地方官塞点好处,少报点自家的地。但这招儿行不通,最后,他们一咬牙,打算铤而走险,干票大的。
【豪族契约】
青、徐、幽、冀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光武帝刘秀起家的根本。因为当初这四地的大佬们直接站队刘秀,所以他们的势力被保留了下来。即使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开始解散地方军队,但这些大佬们手里还是握着不少自己的兵马。

没错,那些大家族手里的那点私家兵马,跟光武帝麾下云台二十八将那强大阵容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但这些家族武装的麻烦之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能打,而是他们在地方上根深蒂固,跟当地的官府关系错综复杂。每当朝廷派中央军来镇压,他们就躲得无影无踪,等中央军一走,他们又重新冒出来捣乱。靠着这种耍滑头的战术,这些大家族一度占据了好多郡县。
不过刘秀可是乱世中拼杀出来的霸主,这种小手段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对人性的弱点了解得透透的。
碰到那些大家族武装力量四处骚扰,加上地方官不作为,刘秀直接下命令:
各个地方的强势团伙,只要五个人联手干掉一个人,就能逃脱法律制裁。
对于那些在镇压行动上不够给力的官员,以前他们要是有啥疏忽大意的行为,咱们就不再追究了。从今往后,就看他们能干掉多少反叛者,以此来评判他们的功劳。
这两条规矩,一个让本来抱团的大家族之间开始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另一个则大大激发了地方上那些官员们打压叛乱的动力。
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很快就被人平息了。
刘秀,也就是光武帝,用实际行动向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家族表明了,这天下到底是谁在做主。他靠自己的力量,让那些人清楚地认识到,谁才是真正掌权的人。
因为连武装起义这样的极端办法都试过了,却一点用都没有,所以那些大家族慢慢就不反抗了。这样一来,刘秀推行度田令的时候就顺利多了,遇到的阻碍小了不少。
刘秀把参与叛乱的那些大家族的地给收了,还让他们搬家到别的地方去住,这样一来,他们的老底就被端了。
那些没跟着起哄的大家族,也挺识相,老老实实地把自家的土地数量报了上去。这样一来,因为清查田地而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就这么消停下来了。
自打汉武帝发了那个《轮台诏书》认错后,大户人家的势力就一天比一天大。他们亲眼瞅着西汉王朝垮台,又看着东汉王朝建起来。这大户人家的事儿,就成了两汉四百年里头的头等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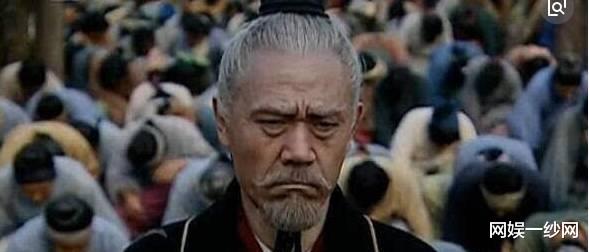
碰到这个问题,两位关键人物各自亮出了他们的解题方法。
王莽和刘秀两个人,家里都挺有钱有势,而且小时候都没了爹。不过王莽他们家,那可是当时最牛的大户人家,有钱有势到不行。就算他爸早走了,他也用不着去社会上摸爬滚打。他只要好好读那些“圣贤书”,再按书里教的去做,就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大权。这样的家庭背景,把王莽养成了一个不了解社会底层怎么回事的书生气十足的人。所以他才会脑袋一热,觉得靠发一道命令,把大户人家的地都收回来,就能一下子把大户人家的问题给解决了。
然而,光靠那些僵硬的文字是搞不定实际难题的。王莽搞的社会尝试,哪怕抱着再高的理想,也肯定因为太不接地气,最后只能变成一场空。
和刘秀比起来,王莽的背景就显得有点不同了。刘秀呢,他只是个小地方上的小贵族后代,而且从小就没了爹。但他可比王莽更懂这社会的门道。为啥这么说?因为他啥活都干过,下过地种过田,也卖过米赚过钱,甚至还跑到长安去念过书。他的家庭条件吧,说是能帮他多长长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但也没好到能让他不碰社会实际,去过那种高高在上的日子。
王莽和刘秀两人都啃过儒家的那些老书,不过刘秀因为真刀真枪地在社会上历练过,所以对书里头的道理体会得更透。
因此,当世间乱糟糟的时候,他能一眼瞅准豪族这个关键,着手处理豪族的问题,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难题迎刃而解。
刘秀心里头门儿清,豪族这事儿根本没法连根拔起,所以他打一开始就琢磨着怎么给豪族套上笼头,立下规矩,还得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干。
度田风波,说白了就是刘秀拿十几个高官当筹码,跟那些大家族做了个交易:你们尽管去赚钱,占地也没问题,但要是钱袋子鼓了,地盘子大了,那税也得跟着往上涨。
光武帝刘秀,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办事实在,不拐弯抹角,直接针对当时社会上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想出了解决办法。这套方案,说真的,在当时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法子了。
刘秀搞了个度田政策,跟那些大户人家订了个规矩,这事儿对东汉影响可大了。在东汉刚开始那会儿,这个规矩既让大户们有劲儿往前冲,又不让他们乱来。就这样,汉朝靠着这个新路子,照样显得很厉害,很有面子。
没错,啥东西都不会永远一个样,哪个方案也不能一次性搞定所有问题。等那些豪门大户变得更强,成了吓人的大家族,那时候出现的新麻烦,就得找新的招数去对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