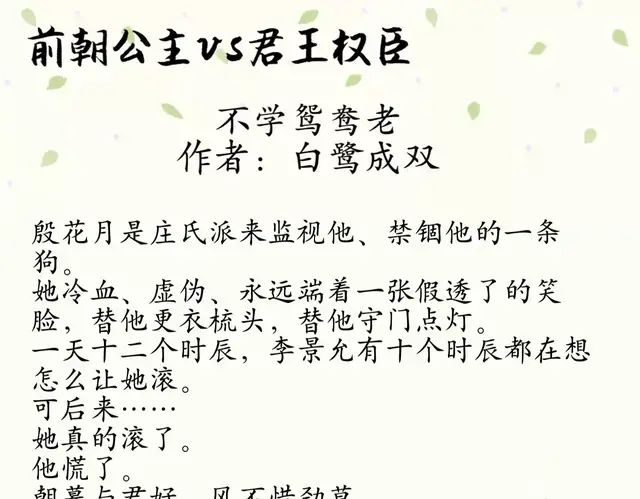《抱着宿敌》
作为一名合格的小跟班,我身娇体软,貌美嘴甜,颇得公主青睐。
后来公主远嫁,我抱着宿敌哭得最大声。
「呜呜呜,没了你,我可怎么活?」
「放手。」
「不放。」
第二日,薛世子是负心郎的谣言传遍上京城。
作为罪魁祸首的我,鹌鹑一般躲着不敢出门。

1
平元十五年,戍边多年的沈老将军入京贺寿,其子沈酌与盛阳公主一见钟情。
同年皇上赐婚。
公主大婚那日,满城红绸,万民欢庆。
我小酌几杯后,酒意上头。
左摇右晃间,逮着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扑了上去。
来了上京后,除了爹娘,公主最疼我。
眼下,最大的靠山要远嫁了。
我一时悲从中来,哭出了声。
「呜呜呜,没了你,我可怎么活?」
身下的人,传来一声闷哼,他攥着我的手,咬牙切齿道:「再乱摸,爷砍了你的手。」
公主果然变心了。
从前我破了点皮,她都舍不得,现在竟然要砍了我的手。
我哭得更伤心了。
「放手。」
「不放。」
最后,我哭得太累,抱着人睡了过去。
第二日,我从崔府醒来,便得知公主今日就要离京。
残阳如血,古道漫漫。
我戴着帷帽,站在官道上,瓮声瓮气道:「殿下,臣女舍不得您。」
公主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旁。
「好楚楚,快让本宫再瞧瞧你这张小脸。」
掀开薄绢,公主眼神一颤。
「呀!怎得眼都肿了?」
想来是因为昨日醉酒,今晨梳洗时,眼肿得不能见人。
我正欲细诉不舍,旁边传来一声冷笑。
「呵!」
沈酌看我的眼神委实算不上友善。
都怪他拐走了公主,我嘴角一撇,委屈地落下泪来。
公主瞪了沈酌一眼,搂着我柔声安慰。
「一介莽夫,莫理他。」
顾不得一旁沈酌越来越黑的脸色,我再也绷不住,埋头扑进公主怀里哭出了声。
「呜呜呜,殿下,您带上我吧。」
公主一边拿手帕轻轻擦拭我脸上的泪,一边捂着胸口,心痛到极致的样子。
「心肝儿,莫哭了,仔细叫风吹坏了眼。
「北地环境艰苦,本宫怎舍得你跟来吃苦。」
我哭得肝肠寸断,只觉得来日之路一片暗沉。
沈酌走到公主身边,催促道:「公主,走吧,莫误了时辰。」
我死死抓着公主并不放手,公主亦舍不得我,她下巴支在我肩上,直呼心肝儿。
沈酌咬牙道:「此处风大,崔姑娘体弱,想必不宜久留。」
最后,公主还是放开了我。
沈酌立刻吩咐人带我回城,又迫切地扶着公主上了马车。
隔着重重人影,我只看得到车辙跑过的滚滚尘土。
2
送走公主后,转头我便听说了薛从钰是负心郎的传言。
据说被他抛弃的女子,抱着他要死要活。
长公主得知此事后,气得动了家法。
我和薛从钰向来不对付,听到这个消息后,忍不住笑出声。
结果侍女面露忧愁,「小姐,你可知那女子是谁?」
难不成是熟人?
「谁?」
侍女支支吾吾:「小姐昨日……」
我嘴角的笑顿住。
「小姐昨日抱着世子哭了许久,最后世子要走时,你还扯着世子衣袖舍不得放手。
「要不是世子眼疾手快遮住了您的脸,今日怕是……」
天塌了。
薛从钰有多小气,我是知道的。
七岁那年,公主点了我进宫伴读。
我爹欢天喜地地送我入宫。
他原是南边的小官,一朝走运,携家带口升至京城。
京中世家林立,公主选伴读这等好事,本是落不到崔家头上的。
但公主好美人。
我长得随我娘,生得一副好相貌,这才入了公主的眼。
进宫前,爹娘嘱咐我宫里都是贵人,要谨小慎微,万万不可闯祸。
但一个小孩子又能记住什么事。
进宫的第一天,我就得罪了薛府的小霸王。
公主指着随母进宫侍疾的薛府小少爷,问我认不认识他。
金灿灿的日头下,小少爷眉间一点朱红,像极了阿娘房间里的神仙像。
我点点头,脆生生地唤出了声。
「认识,是仙女。」
「哈哈哈,薛从钰你也有今天。」
公主笑弯了腰。
仙女涨红了脸。
我左看看右看看,不知所措地缩到角落。
最后,小少爷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哇哇哭着跑掉了。
自此,我与薛从钰的梁子便结下了。
第二回见他,他命宫人将我捉住,逼着我叫他哥哥。
我爹常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我乖乖地叫了。
我唤一声,他应一声,来来回回足足浪费了一个时辰。
直到他眉眼舒坦,伸手将嬷嬷为我梳好的发髻揉乱,才肯轻点下颌放我离去。
走到无人处,我朝脸上狠狠抓了一把,然后顶着一头潦草的乱发跑进公主寝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公主怒了,薛从钰惨了。
听闻他被禁足的消息,我忍不住多吃了一碗饭。
自小到大金尊玉贵被人捧着长大的小公子在我身上连栽两个跟头后,反而越挫越勇。
小霸王耀武扬威,我自当回敬一二。
一开始,我不明情况,只敢暗戳戳地搞事,后来,仗着公主宠爱,我性子愈发大胆,即便是遇见了薛从钰,也敢呛声一二。
3
只是好景不长,现在公主远嫁。
我怕薛从钰找我算账,便不愿出门,推了邀约的宴贴,整日待在府中。
不出几日,便消瘦下来。
阿娘看在眼里,心疼极了。
我赖在阿娘腿上,她揉过我的发顶,哄道:「小冤家,跟丢了魂似的,也不知何时才好?」
我不愿阿娘为我忧心,想着今日上元节,不若趁着热闹,去街上瞧瞧。
我刚带着侍女出府,便被人堵在了巷子里。
小巷暗色无边,深邃幽静,唯有后门亮着两盏檐下灯。
「终于舍得出来了。」
月白灯明,如鬼火荧荧,薛从钰噙着笑,从暗处走来。
檐下有风吹过,灯火跳动,映出他似妖的轮廓,光影明灭,一半在明,一半在暗,我竟分不清他此刻的表情。
我干巴巴笑了声,欲溜走。
「好巧,世子雅兴,我不便打扰,告辞。」
他的侍从堵住出路。
薛从钰挑眉,一副懒散从容的样子。
「不巧,等了你几日。」
我退一步,他进一步,直到被他抵在墙角,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怕是来者不善。
我朝侍女使了眼色,快去叫人。
侍女捂嘴瞪眼,最后红着一张脸,转身跑了。
我还没想通她为何脸红。
薛从钰睨了我一眼,神色倨傲。
「你害我受罚,自己却躲在府内逍遥,天底下哪有此等好事?」
该来的躲不掉。
「我错了。」
「错哪里?」
「不该醉酒纠缠世子,令世子清誉受损。」
薛从钰耳根染上薄红,他神色怪异地看着我。
「怎么今日这般乖觉,往日那张牙舞爪的样子呢?莫不是学人转性了?」
我正色道:「世子是天上的仙人,我一介凡夫俗子,可不敢放肆。
「往日种种,还望世子莫与小女子计较。」
半晌,头顶传来一声轻笑,薛从钰曲指在我额头轻轻一敲。
「哼,谅你也不敢。」
我捂住额头,忍了。
他轻咳两声,别扭道:「既然在这里遇见了,小爷今儿就勉为其难领你去逛逛。」
「啊?」
我诧异地看着他。
就这?
他敛了笑意,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你不愿?」
我才不信他蹲了我几日,就为了带我去逛逛?
莫不是又想到了什么戏耍我的诡计?
许是我怀疑的眼神太过露骨,他阴阳怪气道:「崔楚华,你不会是怕了吧?」
瞧着他眼里的挑衅,我难得被激起几分情绪。
4
街上人潮如织,花灯错落,连天的火龙亮如白昼。
薛从钰随手挑了盏漂亮的花灯塞进我手里。
「替小爷拿着。」
行至樊楼,有人高声呼道:「薛兄!」
李元奉从二楼支出半个身子,兴高采烈地招手。
「快上来。」
他是李太傅幼子,家里人宠得无法无天,也是个混不吝的主。
据说前几日闯了祸,李太傅不得已将他拘在家中,不承想今日在这儿遇上了。
一进房间,他便凑上前围着我转了一圈,眼神亮得无法忽视。
「崔妹妹也来了,灯下看美人,越看越好看,几日不见,妹妹愈发好看了。」
我默默与他拉开距离,果然他的脸皮还是这么厚。
「砰!」
薛从钰将茶杯重重地搁在桌上,他似笑非笑地看过来。
「我倒是不知你几时多了个妹妹,一口一声,也不怕闪了舌。」
李元奉讪笑道:「不曾,是我高兴糊涂了。」
他又吩咐仆从添了一壶酒水。
白玉雕琢的杯中盛满澄澈的液体,灯火交映下,如一汪月下幽泉,闪闪发亮。
「这是樊楼新上的月白酿,每日限供十壶,颇讨京中女郎欢心。
「崔姑娘,刚才是我唐突,便借此赔罪了。」
我尝了一口,入口酸甜,回味清香,不愧是寸土寸金的樊楼,果然非凡。
我一时贪杯,多饮了些。
席面过半,李元奉的小厮从外匆匆道:「公子,不好了,老爷回来了!」
李元奉腾地一下站起身,慌张道:「薛兄,崔姑娘,我们改日再聚。」
他走得匆忙,好似背后有人追赶一样。
我埋着头,专心戳着薛从钰买的花灯,恍若未闻。
「夜深了,我送你回去吧。」
薛从钰站起身。
我点点头,也跟着站起身,却是绕过他走到临江的窗边坐了下来,双手支着下巴看向窗外。
楼下,水声潺潺,灯影绰绰。
我闭上眼,如临梦境。
梦中仙子将我抵在窗边,唇色如血,我抬手蘸了茶水点在仙子眉间。
水痕顺着如玉的肌肤滚到唇边,我几乎看痴了。
仙子握住我的手,眸光潋滟。
「楚楚喜欢吗?」
「喜欢。」
5
自上元节后,薛从钰便打着公主托他照拂我的幌子,隔三岔五差使仆从送些小玩意儿来。
这事传到阿娘那里后,惹得阿娘看我的目光越发深邃。
「一转眼,娘的阿楚长大了。」
阿娘接过侍女手中的梳篦,动作轻柔地将我的发丝梳开,又取了木樨油抹在发尾。
她叹息道:「阿楚也到了该议亲的年龄了。」
我抬眸看向镜中人,面泛酡色,梨涡浅浅。
我转身抱住阿娘,含羞道:「楚楚要一辈子守着阿娘,哪儿也不去。」
阿娘轻拍我的背部,低声笑道:「还是个小孩子心性啊。」
几场连绵细雨过后,天气回暖,莺飞草长。
京郊多温泉,阿爹早早便置办了庄子。
近日春光正好,我便张罗着携侍女前去小住几日。
行至半路,马车突然颠簸几下停在了官道上。
仆从站在马车旁,苦着脸道:「小姐,车坏了,此地距庄子还有些距离。」
随行的仆从不善修车,重新回城派车已然来不及,一时间一筹莫展。
我掀开车帘,下了马车,路上行人寥寥。
这时,后方传来一阵马蹄声。
行到跟前,马蹄停了下来,隔着薄暮,我对上来人清冷的眉眼。
是刑部的陈晏,陈大人。
刑部凶名在外,素来出酷吏,唯有陈大人不同,端方君子,如同诏狱上方的一抹清辉,所有污浊都无处遁形。
阿爹曾多次称赞陈晏端方正直,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只是,我与陈大人的交集并不怎么美好。
初见时,他奉旨办案。
一行人路过抱月楼,我与公主正在窗边打闹,一阵风过,我的手帕恰好落到了他头上。
清冷的陈大人拎起那方粉色绢帕,面若冰霜。
偏生公主看热闹不嫌事大,还振振有词道:「楚楚眼光极好,我瞧陈大人姿色独绝,世无其二。」
陈大人抬首,远远看了我一眼,竟是一言未发便走了。
我自觉做错了事,也不敢朝陈晏讨要那方绢帕,反而处处躲着他。
薛从钰不知从哪儿听说了此事,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格外不善。
6
眼下,倒是避无可避。
陈晏勒紧马绳翻身下马,缁色衣袍随风翩然。
「崔姑娘。」
我神色不自然道:「陈大人。」
视线扫过旁边的车马与仆从,他询声问道:「可是马车坏了?」
他又召来随行的人,「此人善工艺,或能修好。」
我乖巧地立在一旁,有些犹豫地捏捏手心,到底要不要问陈大人要那方绢帕。
可看着眼前光风霁月的陈大人,怎么也不像是会留女子贴身之物的人。
兴许早就扔了。
我默默吐出一口气,还是不提为好。
不多时,马车便修好了。
我眉眼微弯,感激道:「今日多谢陈大人。」
陈大人站在一旁,身姿如玉,他神色平静道:「举手之劳,今日天色微迟,崔姑娘这是要去京郊?」
「去庄子小住今日。」
陈大人点点头,敛眸若有所思道:「曾听家中长辈提起京郊寺庙灵验,陈某本想去求枚平安符,只是公务缠身,便一拖再拖。」
我正愁如何答谢他,如今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便笑着道:「这有何难,大人要的东西,过几日我便差人送去陈府。」
陈晏抬眸看向我,清隽的眉眼舒展,眸中清波微荡。
「如此甚好,谢过崔姑娘。
「今日还要回城述职,不便久留,告辞。」
如同来时一般匆忙,那抹身影很快便消失在空旷的官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