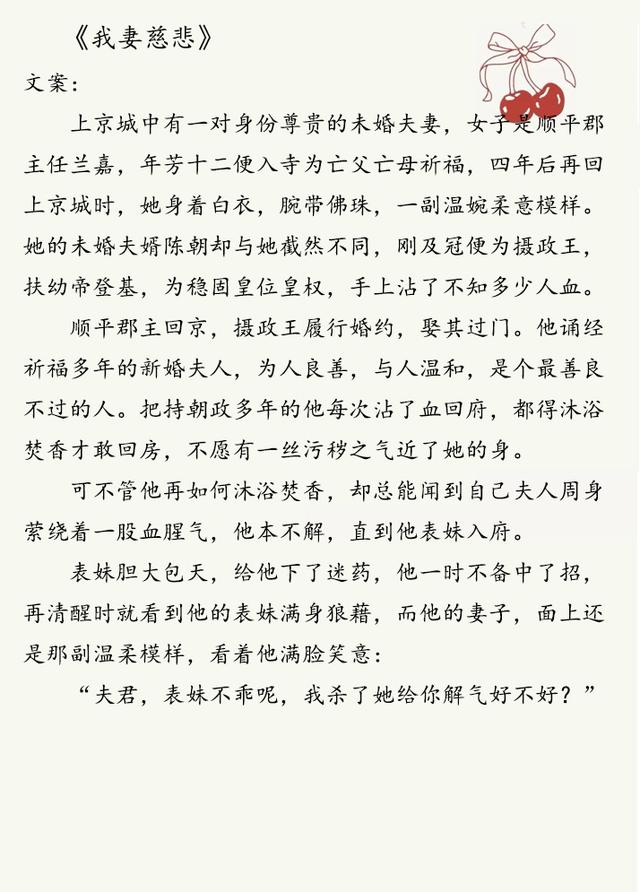我这一生被卖了两次。
举家南迁之前。
我小娘跪在地上,恳求父亲和主母把我卖去做妾。
说我本就是个玩意儿,卖到哪里都一样。
兴许卖去做妾,还能多进二两银钱。
我父姓陈,是洛州城里首屈一指的大布商;我娘是我父亲从洛水河上赎回来的,给了个名分,做了贱妾。
六岁头上随娘一起去花园里摸蛤蟆骨朵儿,一声「娘」被恰巧经过的大太太听了去。
大太太身边的妈妈一巴掌拍了下来:「没规矩的东西,不过是个玩意儿,也敢当你一声娘,叫小娘!」
娘连忙拉着我跪了下来,身子伏得低低的:「是妾无状,没能教好七姑娘,只此一次,还请太太责罚。」
大太太驻足,盯着跪在地上的我娘和我,半晌后开口淡淡地说道:
「是该学学规矩了,七娘呀,打从明个儿起,你就每天都到三娘身边伺候吧!」
娘把身子伏得更低了,以面贴地:「太太,七姑娘还小不懂事,现在就去三姑娘身边,怕冲撞了三姑娘,反成累赘。」
太太嗤笑音色也冷了几分:「不小了,六娘到二娘身边时,也就七娘这般光景,规矩还是早些学起来才好。」
大太太示意身边妈妈将我先送回院子,让娘留下听训,我不愿先回,便扯住娘的衣襟:「娘我怕,一起回。」
那妈妈拧着我的胳膊咬牙道:「七姑娘,该长些记性才是,什么娘不娘的,你只有小娘!」
我吃痛地哭出了声,娘则往前挪了几寸,伏在大太太脚下抽泣道:
「太太,太太,都是妾的错,不关七姑娘的事,她还是个孩子。」
那天娘回来得很晚,回来时脸肿得高高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我哭着扑了进她的怀里,「娘娘娘」地喊着。
她抚着我的发顶柔声道:「顺儿,
以后要叫小娘,万不可再咖娘了
原就是我不配,如今却拖累了你。」
我不懂什么配不配,我只知道不能叫娘,是因为只要我叫娘,我和娘都要挨打,从那夜起我没再叫过她一声娘。
2
府里有两男七女,大公子、二公子和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皆由大太太所出;四姑娘、五姑娘是秦姨娘所出,伺候在大姑娘身边;六姑娘是杜姨娘所出,伺候在二姑娘身边。
那天花园的事后,我开始每日晨起去三姑娘身边伺候,起初时常会被三姑娘和她身边的妈妈丫头搓磨,说是教我识规明理,我便心生了怯意。
一日夜间回了院子同小娘讲:「小娘,我能不能不去三姑娘那里了?」
小娘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红肿的掌心,她霎时红了眼眶,背过身去沉默许久,终是心疼地说道:「顺儿,去不去由不得你我,你要乖顺,才能少吃些苦头。」
一晃就到了冬日,我开始喜欢往三姑娘房里去了,因为在三姑娘的房里烧着个红通通的盆子,说是叫炭盆,那个盆子烧起来整个屋子就会变得热乎起来,就连榻上的被子都给人一种松松软软、暖烘烘的感觉。
不像我们院里冬日里到处冰冰冷冷,屋里的墙角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霜,夜里睡觉时我要和六娘挤在一处,将三条硬邦邦的被子叠在一起盖在身上,小娘和杜姨娘挤在一处,她们则只有一条被子可盖。
杜姨娘和小娘一样都是父亲赎回来的,杜姨娘生了六娘没多久,就被安置在这处离角门最近、离主屋最远的院子里了,过了两年,小娘也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搬了进来,而我那个父亲自我有记忆起,只遥遥地望见过几次,这个院子他从不曾踏足过一次。
六娘和我说是因为我们的小娘出身太低,又失了父亲宠爱,所以才由主母做主安置了在这里,被父亲长长久久地遗忘在这个萧瑟的院中,过着仆妇不如的日子。她说我们本也是这个家的小姐呀,只不过是庶出而已。
小姐?庶出?之前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因为我小娘不曾提起,我一直以为我生来就是这个家的下人,到了年岁就该伺候在主家小姐身边,不承想我竟也扛了个陈府小姐的名头。
3
十四岁那年,朝廷要和临国开战,为了征收军饷把手伸向了洛城中的富户,洛城中的大商都掏出了大半的家财,陈府更不例外。由于我父亲早年间与太守的妻弟起过龃龉,这次洛城纳征恰由此人负责,所以陈家几乎掏光了所有家底。
眼瞅着战事将起,父亲和大太太决定变卖剩余的家当,举家迁往南方避祸,大太太的娘家在南边,到了南边靠着仅剩的积蓄和娘家的帮衬,陈家或许还能有重新兴起的一天。
听闻这个消息的夜里,我一回到院里,小娘便从屋子里疾步走了出来,走到院门口左右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又匆匆地把我拉回到房里。她蹲身将手伸向床下,翻腾许久,拿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包裹,塞到我怀里。
「顺儿,这个你拿着,这是小娘这些年偷偷地积攒下来的,你收拾一下,今夜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就从角门旁的小洞钻出去,切记不要再回来!」她声音很低,却带着十分的急切。
我一时间很难反应过来,小娘为什么这么做,就在愣神的当口,房门「哐啷」一声被踹了开来,大太太身边妈妈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
「我说姨娘,这是闹哪出儿呢?这是要让七姑娘走去哪里?先别急着走,随我一起去太太房里回话吧!」
随我们一起去太太房里的还有六娘和杜姨娘,父亲和大太太坐在上首,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了我的父亲,他一双眉眼尽显疲色,目光从我们几人身上一一地掠过,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就仿佛在看几个物件儿一般,他右手的食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旁边的桌几,良久开口道:「如今战事将起,府里也今时不同往日了,日后怕是不能护佑你们了,接下来你们的去处便由大太太做主安置了。」
言罢便起身离开了,出去时连一个眼色都没给立在下首的我们。
大太太对身边的妈妈说:「叫牙婆过府吧,看着给两位姨娘寻个好去处,两位小姐就让牙婆找个好一些花楼安置了吧!」
4
我们回到院子就被围了起来,想是大太太怕我们逃了吧,杜姨娘见这架势就再也绷不住了,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边哭边喊:「这天杀的,真真地是人如彘犬啊,在府里做小伏低多年,六姑娘也当作丫头子一般送去了二姑娘跟前伺候,没过过一天庶出姑娘的日子,还想怎么着?那黑心的老贼妇,卖我千道万道我都认了,竟还要将我的六娘卖去花楼,这是不肯给我们娘/们儿留活路了!」
说罢面露狂色,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朝着六娘扑去,瞬间双手就攀上了六娘的脖颈:「六娘,别恨为娘,要恨就恨这世道,恨你怎就不是个带把儿的,你若不是个姑娘,就不用面对眼下这些污糟了,不如为娘这就结果了你,省得你去遭那千人跨、万人骑的罪过了,那花楼不是人能去的,为奴为婢尚有一丝尊严,进了那花楼那就是一摊烂肉任人宰割了,那就不是人了啊..……」
小娘和我上前将她拉开,小娘把六娘搂在怀里顺着气,院外的婆子见状立马冲了进来将杜姨娘扣住,杜姨娘才没能再反扑回来,只是哭得声音更大了。
几个婆子看杜姨娘哭得凄惨,终是起了恻隐之心劝道:「姨娘看开些,好死不如赖活着,姑娘花骨朵儿一样的年纪,你怎忍心让她就这般去了?花楼也不见得差哪儿去,万事皆有缘法,许是姑娘以后会走出一条康庄路也说不准呢!」
杜姨娘立马挣起身子要去扑打那婆子,嘴里狠狠地骂着:「康庄你老子娘个头,你个瘸腿瞎眼、肠穿肚烂、黑了心肝的老货,既是康庄路,你怎得不去走?怎还入了这府里做粗使婆子?康庄路你现在就去卖了你家女儿孙女去走呀!」
那婆子被骂得羞红了老脸,大力地推搡了一下杜姨娘,拍了拍衣袖子,怒怼道:「姨娘这是骂谁呢,别是借着老婆子我羞臊当家太太呢,我劝姨娘还是安分些,等着当家太太安置吧,真的惹恼了,把这如花的姑娘送到那下三滥的胡同儿园子里去,可当如何是好?」
杜姨娘听那婆子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也就熄了气焰,呆愣愣地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小娘把六娘顺倒在我怀里,走过去轻拍着杜姨娘的背:「也不是毫无转圜的余地,明天咱们再去求求老爷太太,看看是否还有别的出路,哪怕送出去做妾。」
杜姨娘抬头望向小娘,泪沁的眸中闪过一丝光亮,瞬间又暗了下去呢喃道:「我刚这一通发作,怕是已绝了我们母女的生路了,那老贼妇何时又是肯听哀求的良善之人,怎可能放过我们?没出路,没出路……」
那天夜里我们院子里良久无话,只有阵阵哭声此起彼伏,直至深夜方歇。
杜姨娘房里,她蜷缩在床上哭累了就阖眼睡下了,六娘则抱着双腿靠在床里角落,任由泪珠滴答地落在膝头,无声地哭了良久,也渐渐地闭上了眼睛,小娘搂着我在床沿边上看她们都踏实地睡下了,便带我回了房。
「小娘,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吗?我会被卖去花楼对吗?秦姨娘和四姑娘、五姑娘也会被发卖了吗?」我和小娘躺在床上,我嗫声地问道。
「她们不会,她们跟我们不一样,秦姨娘是老太太的远亲,是良家子,又得大太太和大姑娘的欢心,应是要一起南下的,顺儿,睡吧!」
第二天一早,被一声「坏了事儿了」惊醒。
5
听到那一声惊呼,小娘鞋都没来得及穿就冲到了杜姨娘房里,一进门看到杜姨娘安安静静地悬在了房梁
上。
从下往上看去,就如同是一只硕大的布袋子早已没了生气,床榻上的六娘除了颈间青紫的掐痕就仿佛睡着了一样,可她才十六岁啊。
没过多久就有几个手脚麻利的婆子拿来了两张草席,带了几个小厮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小厮将挂着杜姨娘的绳索割断,她「嘭」的一声坠了下来,小娘这时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看了看这院子的来人,除了婆子和小厮再无其他人,就连大太太身边的妈妈都不曾出现。
他们要用草席子将人裹上的时候,小娘上前拉住了一个婆子:「妈妈,能否通融片刻,好歹让我给她们擦洗一下,换身衣裳,也好叫她们干干净净地走,全了这一世为人最后的体面。」
婆子睨着眼睛瞟了一眼小娘,一把拍在小娘攀在她小臂上的手上,没好气道:「姨娘可真是好性儿,还有空操心这两个断了气的,再说了,草席子一裹什么干净体面的。活着的时候都没体面,临了找体面,找得着吗?姨娘快些让开,别耽误咱们时辰了,如今府里事多,等着咱们的,可不就这一桩事儿。」
小娘讪讪地收回了手,立在那里,看着他们把杜姨娘和六娘草草地一卷,扛出了院子。
她们大概会被丢到乱葬岗吧,也或许会像没了用处的物件儿一样,被随手丢弃在不知名的荒山。
杜姨娘和六娘这边收拾停当了,小娘便带着我去了主院求见父亲和大太太,进了主屋便拉着我跪在他们身前,没等父亲和大太太说话,小娘便狠狠地磕了几个头。
「老爷、太太,妾知道如今家中艰难,与其将七姑娘送去花楼,不如送与他人做妾,本就是个小玩意儿,发卖到哪里都一样,七姑娘姿色算不得上乘,送去花楼怕提不起价儿,不如找户人家做妾去,说不定还能多进几两银子。」
小娘就那样一个头一个头地磕在地上求了许久,父亲和大太太似稍有动容,但并没有直接应下,还是叫我们先回了院子。
回去后小娘沉默不语,就那样静静地坐在门槛前,只是从面色中能看出几分纠结,她也许思量了很久。但最终还是从烂包裹里拿出了两根银簪子,塞给了守在院外的婆子好歹说动了她,天快擦黑时,那婆子给小娘送来了两道黄纸。
入夜后带着我进了杜姨娘的屋子,将那两道黄纸烧了去,这是唯一能为她们做的了,也算是有人记得她们曾经来过吧。
小娘说,杜姨娘糊涂呀,怎么就趁所有人都睡下的时候,亲手结果了自己和六娘,不去争上一争,怎知就到了那不可活的绝路了呢;小娘还说,杜姨娘或许是想保全六娘在这世间为数不多的和仅剩的尊严。
我问:「活着和尊严哪个更重要?
小娘说:「活着,尊严就像野草一样会重新再长出来,可命却只有一条啊,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只要人还在,万事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即便是绝路也可逢生,也只有活着,才可以好好地活着。」
我问:「活着和尊严哪个更重要?」
小娘说:「活着,尊严就像野草一样会重新再长出来,可命却只有一条啊,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只要人还在,万事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即便是绝路也可逢生,也只有活着,才可以好好地活着。」
也许是那天小娘磕破了头,让父亲和大太太心生了恻隐,也许是那比我父亲还大上几岁的江老爷出手阔绰。
小娘真的为我谋得了一条她所谓的生路,其实我想说,无论是做妾还是被卖去花楼,皆不是我之所愿呀,可是这世道谁又在意我愿与不愿呢。
三天后我被塞进了一顶小轿,悄无声息地被送去了江府,做了江老爷的陈姨娘。
临行前小娘告诉我她叫沈怡蓉,自小被卖去花楼,虽一生受尽搓磨,可依然想在这世间留到最后,只有咬着牙关往前走才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甜,不然这一辈子亏得慌。
她说她给我了取了个大名唤作「顺清」,她希望我此后的人生平安顺遂,清平安乐。
最后她小声地说,她恨自己护不住我却又生下了我。可是我并不怪她,她何曾又有的选呢?
我想告诉她我也恨自己,因为我也没能护得住她。
我把她塞给我的那个包裹悄悄地留给了她,我已然有了生路,可她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也希望她可以好好地活着呀。
出院子的时候我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回头看见她,我娘沈怡蓉,如同枯槁的落叶一般,无力地倚靠在门框上,好似只要一阵风起就能将她「簌簌」吹落。
我回身,用尽全力大喊了一声:「娘!」
她摸着眼角,温温柔柔地回了一句:「诶~」
6
去了江府后不久,便起了战事,听说陈家也已经南下了,我娘呢,如今又身在何处呢?
沈府的日子比我想象中的好,除了要伺候江老爷就寝以外,其他都很好,因为我也有了人伺候,一个妈妈、两个丫头,日常起居与吃喝皆有人为我安排妥当,我那时在想,外面兵荒马乱,我却能在此安得一隅,也许这就是娘说的好好活着吧,我想我娘了。
入江府的第二年末,我生了个女儿,直到女儿满月时江老爷才来看了一眼,没待上半刻钟便要起身离开,我拉住了江老爷的手:「老爷,不为孩子起个名字吗?
江老爷有些错愕地看了我一眼:
「女娃儿家家,哪需刻意地起什么名儿啊、字儿啊的,就按排行叫个十二娘刚好,你好生将养着。」起身便走了出去。
张妈妈看我满脸的失落,便同我说道:「姨娘,可知道,这府里除了大太太所出的姑娘是起了名字的,其余的都是按着序儿叫的,又不是生了个哥儿,所以名字这事上无须太大想头儿,大家都这么叫着的呢。」
我心道原是这样,姨娘只配叫小娘,姨娘生的姑娘在他们看来亦不配有名字。所以在陈府时别人都叫我七娘,只有娘叫我顺儿,唤我顺清。
战事拉拉扯扯地持续了数年,战事初歇时我的甜甜已经长到了三岁,对了,我给我的女儿取了名字,乳名甜甜,大名如饴,我希望她能甜甜美美地过一辈子,这一生都不用知道苦痛为何,我的女儿,她配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儿啊、字儿啊,她可以不是十二娘,但她必须是如饴。
也是那年江老爷撇下了这满院子的妻妾子女自己一个人去了,大公子挑起了江家的大梁,成了江老爷,大太太也变成了老太太。
如今的大太太看着公爹留下的这些妾室和庶子女,似乎是犯了难,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老太太看她犯难,便道:「有些不可留的,便不必强留,遣了牙婆子另寻去处罢!」
显然我就是那些不可留的,牙婆上门之前,我去寻了老太太,我跪在老太太近前,把身子伏得低低的:「太太,这些年承蒙您的看顾,我才能在这府里,不知愁事地过着滋润日子,只今时不同往昔了,我不能,也不愿再拖累太太了,我愿和牙婆走,只是恳请您让我带上十二娘,她如今还小,留在府里也要劳烦他人来看顾,就请太太让她随我去吧!」
老太太自是乐得我带走甜甜的,一个话都说不全的女娃娃,都无法送出去联姻卖好,走了不仅一了百了,还能多得几块碎银子,有什么可不允准的呢。
就这样,隔天清晨太阳初起的时候,我带着甜甜离开了江府,和几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女子一起坐上了牙婆子的马车,马车骨碌碌没停歇地行了一天,天黑透的时候在离洛城近百里的茂城城外停了下来,牙婆子带我们进了一所一进的院子,说是暂且安顿在这里,让我们早些睡下,明天一早要来人挑人的。
7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牙婆就把我们都叫了起来,让我们梳洗干净,说一会儿有几位爷要上门瞧人了,牙婆站在门口叉着腰:「我可跟你
们说都精神着点儿,造化好的被人挑中去做姨太太,从此以后吃香喝辣的不在话下;造化不好,我也不能多留你们在这儿啃嚼我的银子,我定早早地打发了你们去那园子花楼,给我换些现银子添添嚼谷。」
我心口泛酸,原来在牙婆子眼里我们这些人能做妾已然是大造化了。
身边的姑娘陆陆续续地被挑中,我被剩了下来,牙婆打量着我和我怀里的甜甜,嘬着牙花子道:「非要带个这么个拖油瓶子,不然就你这身条儿、样貌不早被人挑了去?这么个小不点儿,可叫我怎么办?卖去当童养媳人都嫌小,我看眼下也就花楼不嫌弃你们娘俩儿,女娃娃在别处是草,在他们那里可是个个都是个宝呢……要不是那鸨母子个个精明的跟猴儿似的,价儿压得太狠了些,我这就送了你们去……
在我以为我终是逃不过去花楼的命运时,又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身材颀长,走路时有点跛脚,皮肤黝里,那张脸只一眼就会雕见横在他
右颊狰狞的疤痕,再细看下去,他的五官立体竟如刀刻般俊朗,一双眼犹如鹰隼一般,看人的时候过于犀利,好似带着一股子肃杀之气,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实话说,除去面上的刀疤和跛了的脚,他还真是个齐全的俊俏公子呢,起码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可能是脸上刀疤的缘故,他看人的眼神似带着煞气,让人不敢直视。
他将目光从我身上收了回去,便和牙婆低声地交谈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牙婆提高了音量:「这价格可不行,你加点儿,人你立马带走!」
牙婆面向着我说:「你运道不错,爷相中了你,要带你回家呢!"
听到这话我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想也没想地顺势就跪在了那男人面前,手轻拍着怀里的甜甜对他说:「爷,这是我女儿,求爷把她一起带上吧,我会做些缝补零活,也可以帮人做浆洗来养她,定不让爷多操心……」
我话还没说完他便探手将我从地上捞了起来,略带嘶哑的声音清清冷冷地说道:「莫跪,有话站起来说。」
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在我跪下的时候,能够将我扶并起告诉我别跪的人,不觉中我竟红了眼眶,他的这个举动就好似一阵暖风,从我心头轻抚而过,我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牙婆看我红了眼,在一旁捏着嗓子道:「哎哟喂,我说爷能相中你们娘儿俩,这可是你天大的造化呀.怎么还要甩泪珠子了呢?」
我不可置信地望向了男人,想得到他的回应,可眼睛里的水汽就那么不争气地翻腾了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他叹了口气,随后对我道:「容我点时间,两日后来接你们。」
我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我再一次逃过了花楼,泪也大颗大颗地掉下了下来,我朝他弓着身子不住地说:「谢谢爷,谢谢爷……
牙婆子见今天就把我打发了可笑歪了嘴,「咯咯」地笑着冲着男人说道:「这位爷,咱可说定了只多留两日,这两日的吃喝都得算您的呢!」
8
两日后临近傍晚时,那男人叩响了小院的大门,进门就丢给牙婆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子,牙婆笑接过袋子在手上掂了掂,立马见眉不见眼地笑开了,两步一扭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把我塞到男人跟前:「成了,你运道好,今儿就随爷走吧!」
就这样,我和甜甜坐上了男人那架没顶子的牛车,随他进了茂城,我们一路无言,只有甜甜一会儿
「娘,你看这里」,一会儿「娘你看那里」地说着,牛车摇摇晃晃,甜甜没多久就歪在怀里睡着了,大概一个时辰,牛车停在了一间猪肉铺子门前,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到了。
我抱着甜甜下了车,站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终是问出了那句盘在我心头许久的话:「爷,买我回来是做妾的吗?」
男人起先一愣,随后抿唇道:「你想做妾吗?」
我抬眼看了看他并没敢接话,我可以不想吗?
他看我立在原地没有说话,便放柔了语气对我说:「我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若愿意咱们就一起过下去,你就是我娘子,还有,我不是什么爷,粗人一个罢了。」
听到那声「娘子」,我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给出怎样反应,我也可以做别人娘子吗?我真的可以吗?不是妾,而是正头娘子?
我定定地把他望着,就连步子也忘记了挪,直到他从我怀里接过了熟睡的甜甜我才反应过来,我伸手想抱回甜甜,他却说:「先进去再说
从铺子穿过了到了后面,是一个不大小的院子,一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厢房,还有一个小厨房,院子中央还有一棵桂花树,由于赶上了花期,空气里递着脉脉甜香袭人心怀,一阵风吹过,带下了如同金色小蝶般的花瓣,飘落在树下的小圆几上,煞是喜人。
直到他轻嗑了一声,我的思绪才被拉了回来,冲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爷,为了接我们,想是还没用过饭吧,我现在就去做饭。」
他腾出一只手拉住了我:「不急,先安顿孩子踏实地睡下。」
他抱着甜甜走入了正房,将甜甜轻轻地放在了床榻上,转身对我说道:「你随我来,我有几句话同你说。」
我随他出了正房,他坐到了桂花树下的藤椅上,伸手指了指他对面,示意我也坐下。
他缓缓地开口道:「听牙婆说你是大户人家的,男人遭了变故才出来的,你看到了我这个情况,面上和腿上都落了伤,这个铺子就是我的营生,只要你安心同我过日子,养活你们娘儿两个吃喝不成问题,但绫罗绸缎、穿金戴银怕是不能了。」
听他这么说我连忙摇头,摆着手道:「这已经很好了,很好了,不要绫罗绸缎,不要的,不要的,我只求爷别嫌我们是个累赘,我以后一定好好地服侍爷,叫爷省心。」
他捏了捏眉心:「还有,别爷啊,爷的,咱们老百姓不讲那一套,我姓薛,薛乘风,你呢?」
「我?顺清……沈顺清」我对他撒了谎,我姓陈啊,但我想随我娘的姓,想把她的姓氏作为我的念想,长长久久地念下去。
那天夜里我们吃过了饭,我把甜甜带到了东厢房,陪她玩了一会儿便哄她睡下了。
我起身去了正房,我去时他不在,他正在前面铺子归置东西,我站在床榻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褪了衣物坐到了床上。
他回来时看见跪坐在榻上的我,瞬间红了脸愣在了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时的我仅穿了一件小衣跪坐在床上,手垂在双腿上搅着手指。

9
他还是走了过来坐在了床沿上,伸手将被子捞起裹在了我身上,他面上竟又红了几分,黝黑的皮肤挂上层层红晕,竟有些说不出的局促。
他以拳抵唇掩饰般地轻咳了一声:「你不必这样,想是你也累了,便早些歇了吧!」
我忙开口问道:「是不是我哪里不好,让你恼了?所以你才不愿让我伺候。」
「我说了只要你愿意,你就是我娘子,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所以你不必这样,我又不是那色中饿鬼,这种事自是等到你心甘情愿才好,而不是现在这样。」
他的声音很轻甚至带着几分温柔,可却让我羞臊得无地自容,我扯过衣裳胡乱地套在身上,逃也似的回了东厢房。
我想起被送进江府的第一天,江老爷强要了我,事后他粗粝的手掌抚过他在我身上留下的一道道红痕,玩味道:「买你来就是伺候我的。你若知道顺从,何须吃这些苦头?伺候我是你的本分,我愿留你在榻上是你的福气,可要惜福才是。」自第一夜后,每每江老爷要来我房里时,我总是披着条薄纱或者穿小衣乖顺地等在榻上。
后来也却是如他所说,他留我在榻上才是我的福气,自他不愿再见我的时候,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和甜甜,仿佛又回到了陈府的小院。
而那夜薛乘风却说,他想等到我心甘情愿,也是从那一夜起,我的人生好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我一夜未眠,天还没亮的时候,听见院里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想是他出门杀杀猪去了,等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我也起身去了厨房。
清粥小菜刚端上桌子的时候,他回来了,看着桌上升腾的热气,眉眼就柔软了下来,一丝笑意悄悄地爬上了嘴角:「去,喊甜甜吃早饭。」
日子就这样过了下来,我有时做完院里的洒扫浆洗,也会去前头铺子里给他打打下手,甜甜也渐渐地和他亲近了起来,有时我还在后院,她便一个人跑去前头找他,他白日里不忙时,便会在桂花树下陪着甜甜玩上一会儿,他时常把甜甜举得高高的,空气里也总是回荡着甜甜银铃般的笑声,那一幕会让人不自觉地弯了嘴角,我想那便是美好吧。
一日下晌,他做了纸鸟,风一吹那纸鸟就「呼呼」地转了起来,甜甜在一旁看得新奇,便摇着他的胳膊:「我玩儿我玩儿…给我转转嘛……转转嘛!」
他点了一下甜甜的鼻尖,附在甜甜耳边哄着甜甜道:「你要说,爹爹,甜甜也想玩,我就给你玩儿。」
甜甜涨红了小脸儿,鼓起了腮帮,转过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对上了我的视线,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那副小模样儿我忽觉得好笑,便笑出了声:「别瞧我,我可什么都没看到。」
甜甜又转过身继续盯着他,他起身扬了扬手里的纸鸟继续哄道:「叫爹爹便给你,不然纸鸟可就飞走喽!」
说罢便挪开步子围着甜甜走了起来,手里的纸鸟「呼呼」地转得更欢了,甜甜终是没能抵抗住纸鸟的诱或,追着他跑了起来,「爹爹爹
爹」地喊着,他将纸鸟递给了甜甜,甜甜一边跑一边「咯咯」地笑着,嘴里还念叨着:「爹爹真好,爹爹真好!」
他便爽朗地笑了,欢乐像阳光一样洋溢在他的脸上,他朝我看来那一刻,我仿佛我被阳光晃了一下眼睛,他真的很好。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准备将饭菜给他送到前头去吃的时候,忽听到「当」的一声,那是刀重重地剁在案板上的声音,随后传来他怒声的呵斥:「婶子,这是在哪听来的这些闲话?怎的婶子,可觉得我是个好性儿的?」
见他动了火气,我撂下饭菜,疾步朝前走去。
10
我走到后堂的就看到一个微胖的婆子在站案前,喋喋不休地对薛乘风说着,那些话就如长了翅膀的尖刀一般,纷纷钻进我心里,狠狠地扎了下去。
在铺子外头不远不近的地方,也围了好些看热闹的人,见这架势我脚底竟灌了铅般地不听使唤了,没能再走上前去。
他买我回来的事情,不知怎的在街上传开了,大家都说薛屠夫在园子里赎了个相好儿的回来,还带了个女娃儿,说这园子里出来的女人不仅身子不干净,心思也大着呢,今天在你屋里,明天指不定在谁榻上。
我想应是这些传闻扫了他的脸面让他难堪了,所以他才动了怒。
薛乘风把刀从案板上提起拎在了手上,吓得那婆子尖叫出声跌坐在地上,我连跑上前去抱住了他的胳膊,他垂头看了我不虞道:「你出来做什么?回后院去!」
我生怕他一怒之下做出些什么,夺过他手中的刀放回到案板上,急得红了眼眶:「你随我一起,好不好?该吃晌午饭了呢!」
他手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发顶,他看向那婆子,目光又一一地扫过那些看热闹的人,掷地有声道:「这话我只说一次,顺娘是我妻,在乡下时便娶过了门,我在这城里站住了脚,才把她们娘俩接过来,今后我若听到谁在乱嚼舌头辱我妻女,可休怪我手中的尖刀无情了!」
人群匆匆散去,萦绕在我心头的那片阴霾,也随着散去的人群渐渐消失得不见了踪影,以往的种种在脑一闪而过,直至今日我才明白,娘说的好好活着是什么。
入夜后月亮犹如一张圆盘爬上了远方的天空,坦白的月色洒在院中好似覆上了一层轻纱,正房的窗户烛光影影、交颈缠绵,是薛乘风点燃了那早已准备好的两支大红花烛,烛火摇曳,直至天明。
他身上有多处大大小小的疤痕,他说那是他多次死里逃生的见证。
他母早亡,那场大又战始于他的家乡,他便随父兄一起被派上了战场,做了最普通的排头兵,随大军东征西讨了数年之久,最后独留了落了残的他,战后便拿了朝廷的津贴放回了原籍,和他同去的父兄为了护着他活下来,则变成了他手中的几两碎银,他不想一个人留在家乡,就变卖田屋来了茂城。
他之前也想过娶妻生子,早日完成他父兄的遗愿,可别人都怕他面上的疤,嫌他跛了的脚,后来他在牙婆那里遇见了我,他见我抱着甜甜缩在一边,像极了当初他父兄将他护在怀里的那一幕。
第二天一早,他将一个木匣子递到我手里,支支吾吾地说道:「以后你管家,钱虽少了些,但我会努力多赚些的。」
我打开匣子里面有一张房契,还有不到一贯的铜钱,这钱……是少了些啊.....
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置铺子和娶媳妇都花了……」
日子真的就像我娘说的那样,只要你咬紧牙关,才会知道什么是甜。
我想我娘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尝到了甜是什么滋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