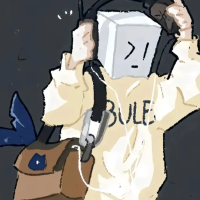这是一个天津女知青在河北农村生活的真实故事,讲的是她和那里的人们建立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每次聊起这段知青岁月,她都会眼含热泪,哭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杨玉琴,她是1968年那届初中毕业的。她在河北青县待了六年多,干农活、落户在那里。后来,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上,回到了天津。但河北青县成了她一直想念的,像第二个家一样的地方。

1969年2月初,十七岁的杨玉琴,初中毕业才半年多,就来到了河北青县的马场公社。她被分配到的村子叫张家屯大队,和她一起从天津来张家屯插队的知青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杨玉琴在内的九名知青,五个女孩和四个男孩,被分到了张家屯二队,大家暂时挤在牛棚院子里那两间土坯房里。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离新年也就十来天。队长张有粮有点尴尬地对知青们讲:“这不快春节了嘛,天又这么冷,你们就先在这儿凑合一下。等春天暖和了,我马上找人把队部那两间屋子给你们收拾收拾,队部大院那边条件能稍微好点。”牛棚院子环境虽不太好,但住起来还算凑合。两间房里都铺了地铺,麦秸和秫秸堆得厚厚的,得有半米,躺在上面软绵绵的,跟睡在高级床垫上似的。旁边屋子里有灶台,还有口能装十二印的大铁锅,带着两层蒸笼,听说这是以前农忙时给社员们送饭用的家伙什。最便利的是,牛棚院子里就有口井,喝水不用跑到外面去挑。给知青们掌勺的是位中年大婶,队里的年轻人管她叫老憨婶,杨玉琴他们也一样,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老憨婶子。老憨婶子是二队里张敬贵的老婆,大伙儿因为张敬贵从小性格实在,就给他起了个昵称叫张老憨。但其实张敬贵机灵着呢,他会做豆腐、能驾车,还会建房子,算是张家屯大队里挺有本事的一个人。说起老憨婶子,她真是个可怜人,打小就没了妈,全靠她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辛辛苦苦地把她拉扯大。十九岁那年,她嫁给了张老憨,二十岁就生了个儿子,可不幸的是,那孩子刚满月就没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结果在两岁那年突然发高烧,没救过来,也没了。第三个孩子又是个儿子,村里的一位老奶奶在孩子手腕上系了条红绳,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三癞子。三癞子身体倍儿棒,一晃眼就长到十八岁了,可他还是很少下地干活。不是说三癞子懒,而是他妈妈老憨婶子心疼他,不舍得让他去受累。毕竟老憨婶子就这么一个心头肉,宝贝得不得了,捧在手里都怕化了。其实,三癞子这孩子挺懂事的,上学时成绩就一直不错,整个生产队就他能念到小学毕业。就是老憨婶子太宠他了,啥活都不让他干,所以社员们对他的印象都不太好。知青们到张家屯二队的第二天清早,老憨婶子就跑到牛棚那儿,帮大伙儿忙活起做饭的事儿。她儿子三癞子,大名张世成,也跟着一起来了,肩上挑着两筐菜,一筐是水萝卜,一筐是大白菜,都是老憨婶子自家地里长的。因为队里没给知青们备菜,老憨婶子心善,就把自家存的秋菜分了点给他们。做饭时,杨玉琴主动跑去帮老憨婶子添火拉风箱,老憨婶子乐开了花,一口一个闺女地叫着杨玉琴,杨玉琴心里暖洋洋的,觉得这称呼特别亲,就像妈妈叫她小名一样。每天一到做饭时间,杨玉琴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拉风箱,还央求老憨婶子教她怎么做窝头和贴饼子。过了几天,老憨婶子拿出了一副用旧棉布做成的套袖,给杨玉琴套在了棉袄的袖子上。她说,棉袄要是弄脏了可难洗了,戴上套袖,做饭烧火时就不会把棉袄袖子给弄脏了。过完春节,杨玉琴最先跟老憨婶子学会了怎么做贴饼子和蒸窝头,还学会了摊煎饼。不过吃煎饼挺费事的,所以老憨婶子只给知青们摊了两次。摊煎饼那会儿,从泡高粱米到磨成糊,老憨婶子一步步都教给了杨玉琴,就连烧鏊子的火候和摊煎饼的手法,老憨婶子也一点没藏着,全教给了她。春耕第一天,知青们跟着社员们一起去地里施肥。天刚蒙蒙亮,老憨婶子就给杨玉琴肩上垫了个棉垫子,让她挑粪。看到老憨婶子对杨玉琴这么体贴,知青们心里都挺不是滋味,都说杨玉琴真是有福气,能有个像亲妈一样疼她的人。从春耕一开始,老憨婶子就不再帮知青们烧饭了。因为春耕春播得赶时节,队里人手不够,连老人和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得下田干活。老憨婶子也得下田拉耧播种,就连张世成(三癞子)也去田里干活了。刚开始参加劳动那会儿,知青们真挺不习惯的,忙了一整天,肩膀疼得碰都不敢碰,两条腿重得像绑了沙袋,一回宿舍就想倒头就睡,哪里还有精力去做饭。好在老憨婶子每天干完活,都会先帮知青们把饭做好,然后再回去忙自家的。那段时间,要不是老憨婶子帮忙,知青们恐怕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呢。1970年秋天过后的一天早上,那天北风呼呼地吹,冷得很,张队长让杨玉琴跟着大伙儿去公社的粮站交粮食。见大家都已经套上了棉袄,杨玉琴也从她的大包里翻出自己的棉袄,赶紧穿在了身上。到了村里粮站排队交公粮那会儿,风停了,天气也变暖和了,杨玉琴便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搁在了拉货的车上。快到晌午,大家交完公粮后,队长问社员们是想在公社那里吃了午饭再回村,还是直接回家并让队里多发一斤小麦。社员们都说想回家吃饭,也都赞成多发一斤小麦。回到家后,杨玉琴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棉袄落在粮站院子里那堆麻袋上了。老憨婶子连忙叫上三癞子,陪着杨玉琴去公社粮站找棉袄。可到了那儿,大家都摇头说没见到棉袄,杨玉琴的棉袄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天气眼看就要变凉了,没有棉袄可咋熬过冬天呢?杨玉琴考虑了两天,打算请假回天津一趟,找妈妈做件棉袄,同时也想在家里多待几天,她确实想家了。

正当杨玉琴打算回天津那会儿,老憨婶子捧着件棉袄走进了队部院子,乐呵呵地说:“玉琴啊,我把自己的夹袄拆了,拿旧棉花给你做了件新棉袄,不知道大小咋样,你快穿上瞅瞅。”杨玉琴接过老憨婶子递来的棉袄,往身上一套,暖洋洋的,特别贴身。那一瞬间,她心里暖烘烘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杨玉琴擦干眼泪,笑着对老憨婶子说:“真是太感谢你了!”可能觉得这么说不太对劲,她又赶紧补了一句:“谢谢干妈!”从那以后,老憨婶子就成了杨玉琴的干娘,而杨玉琴也再没叫过老憨婶子了。那个春节,杨玉琴没回天津老家,而是和孙悦一起留在家里守家。大年三十一早,老憨婶子就把她俩叫到家里,吃饭时,给她们各盛了一碗大杂烩,还一人发了一个枣卷子。坐在旁边的老憨婶子,还不停地把自己碗里的肉和豆腐往杨玉琴碗里夹。那一晚的除夕夜,杨玉琴也是在她干妈家里度过的。于是,杨玉琴和老憨婶子一家变得特别亲近,她开始叫张世成(三癞子)为哥哥,称呼老憨婶子的老公为大叔。老憨婶子觉得叫干爹会更显得亲,但杨玉琴始终没能改口。后来,杨玉琴回天津老家过年时,跟妈妈讲了干妈帮她做棉袄的事。妈妈听后特别感动,不停地叮嘱杨玉琴,要时刻记住人家的恩情,千万别忘了。从那以后,杨玉琴每次回到天津,都会给她干妈带上些当地的糕点特产之类的东西,还有一次特地买了条围巾和一件时髦的城里人穿的上衣给干妈。转眼间,1974年的春天就到了,县里的刺绣厂开始招人。本来,队里是打算推荐杨玉琴去县里做工的,可孙悦却求着杨玉琴说:“玉琴啊,你在张家屯有你干妈疼你,不如把这个工作的机会给我吧。”说实话,杨玉琴还真有点离不开她干妈,但最后她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孙悦。那时候,张世成(大伙儿都叫他三癞子)已经二十三岁了,个子高挑模样俊,可偏偏就是找不到对象。村里的姑娘都说张世成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主儿,长得好却啥也不会干。也有人因为他的小名太别扭,一听到这名字就直打冷颤。老憨婶子因为自家儿子找对象难,心里挺焦急,但干着急也没用啊。张世成的爹总埋怨老憨婶子,说是她把孩子宠坏了,不然怎会找不到对象。可现在这样了,埋怨又能解决啥问题呢。之后,有热心的邻居大妈给老憨婶子支招:“世成他娘啊,你看玉琴那姑娘,长得多标致,多招人喜欢啊,干脆让她当你儿媳妇算了,省的你还得四处找人帮忙说媒。”“那可不成,玉琴是我干女儿,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尽管自己儿子找媳妇不容易,老憨婶子也从未往玉琴那儿想过。一天晚饭后,杨玉琴去她干妈家玩。刚迈进院子,就意外听到张队长和干妈在聊天:“嫂子,你看世成都这么大了,要不我探探玉琴的口风,看她想不想嫁给世成?”“他叔,这可使不得,玉琴是我干女儿呀。就算玉琴点头,咱也不能这么办。知青迟早要回城的,玉琴要是跟世成成了亲,她就回不了城了,咱不能耽误了人家姑娘。”老憨婶子还是拒绝了张队长的想法,因为这事,老憨婶子跟她老公还吵了起来。听了干妈那番话,杨玉琴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看到干妈那么为难,她真动了和张世成成家的念头。可一想到其他知青都一个个回城了,杨玉琴心里就十分纠结。那年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干完活往家走,杨玉琴和刘淑蓉这位女社员边走边聊,聊着聊着就提到了张世成。刘淑蓉脸蛋儿一红,说道:“世成哥人那么好,现在也变得勤快能干了,怎么找个伴儿还这么难呢……”说话的人可能没往心里去,但听的人却上了心。杨玉琴心中暗喜,趁机又好好夸了张世成一番,接着说:“像世成哥这么好的人,真是千里难寻。可惜我只是他的干妹妹,要是能当真的,我早就嫁给他了。”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杨玉琴居然促成了一段大好姻缘,帮干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订婚那天,老憨婶子紧紧握着杨玉琴的手说:“闺女啊,你可真是帮了娘大忙了,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干闺女的份上,我都想给你跪下来磕几个响头……”那年秋天过后,张世成和刘淑蓉就去领了结婚证,还办了婚礼。看着像亲闺女一样俊俏的儿媳,老憨婶子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能帮干妈完成一桩心愿,杨玉琴心里也是美滋滋的。1975年秋天,杨玉琴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她成了张家屯大队头一个被选上去念大学的工农兵学生,而且整个大队就她一个。虽然她去的是天津的一所两年制的中专师范学校,但杨玉琴还是乐开了花。既能上学,又能回天津,这可是美事一桩啊。离开张家屯的那天,村里的父老乡亲都聚在知青点给杨玉琴送别,可就是不见老憨婶子的身影。杨玉琴打包好东西后,急忙跑去跟她干妈道别。一迈进院子,就听见干妈呜呜的哭声。她赶紧跑进堂屋,却发现屋里没人,原来干妈一个人躲在厨房里伤心地大哭呢。瞧见杨玉琴到了,老憨婶子赶紧上前抱住她,边掉眼泪边说:“孩子,我真舍不得你离开,你走后,我想你咋整啊,呜、呜……”那时候,杨玉琴眼泪哗哗地流,哭得说不出话来。拎着干妈给煮的鸡蛋,揣着乡亲们的美好祝愿,心里满是对张家屯这个第二故乡的眷恋,还有对干妈一家深深的牵挂和不舍,杨玉琴眼里含着泪,告别了张家屯,回到了天津。杨玉琴工作后的第二年,就拎着礼物去了张家屯,探望了她的干妈一家还有张队长。等她结婚后,还特地把干妈接到天津,一块儿住了几日。

现在,虽然她的干妈已经离世很久了,但杨玉琴还是会时常回张家屯瞧瞧,看看那里的乡亲们,还有她的哥嫂。杨玉琴表示,那个让她日思夜想的第二故乡,始终让她放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