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0世纪20年代,媒介对写实主义的感知需求激发了表演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但由于电影拍摄距离、镜头焦距与以往的舞台表演有所区别,尤其是特写镜头的使用,银幕要求表演更加写实自然,强调人物状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演员通常需要通过内在情感的共情唤醒外在行动的表现,从而建立起鲜活的角色。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1920年代仍是默片时代,电影表演美学源流多元,混杂了文明戏、戏曲、外国电影的表演方法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模仿。

优秀的演员已经逐步摆脱文明戏表演格调,而转向现实主义表演风格。
无声时期的电影表演重视演员对身体的运用,身体发挥了人物进行语言表达的功能,演员的身体和情感的有机结合是当时表演达到自然写实的关键要素。

周文珠的表演经验经历了初期对自身经验的自觉表现,她经过不断地表演技巧练习与实践积累,能够将不同的情绪进行细腻表现,诠释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最终达到表演与角色统一的效果。

节制的表演尽力调和面具般恒久不变的表情与无数生动自然的细微表情。

它在摄影机前通过表演的内心化来实现。伊·周文珠对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把握具有分寸感,她将内心情感的准确外化,形成了内敛而富有层次的表现风格。
擅长复杂心理状态的层次表现《风雨之夜》是周文珠加入大中华百合公司后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参演的、现存最早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影片中她对角色卞玉清的诠释,可以窥见其表演的整体风格基调。

周文珠的角色话语表达不多,主要依靠动作和情绪来完成人物塑造。
玉清是乡村女性,还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学堂教师,同时,她钦慕有写作才华的余家狗,对于婚姻抱持独身主义态度。

玉清的行为动机并不复杂,但多数以内心活动为主。
影片中展现玉清与余家驹及其女儿娇娜同游山水的片段,玉清和家驹相处融洽,随着谈话愈加亲近,过程中玉清对自身情感的表现真诚、态度克制。

另一条叙事线索是钱大伟反复追求她,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意,玉清选择与之保持礼貌距离,回绝告白时果断清醒。
玉清对待情感的态度含蓄,却不乏个人主见,在语言表达节制的情况下,周文珠使用简练而有层次的人物动作,表现出玉清行动风格上的分寸感,钱大伟面前始终保持距离和沉默,而对待余家驹更加腼腆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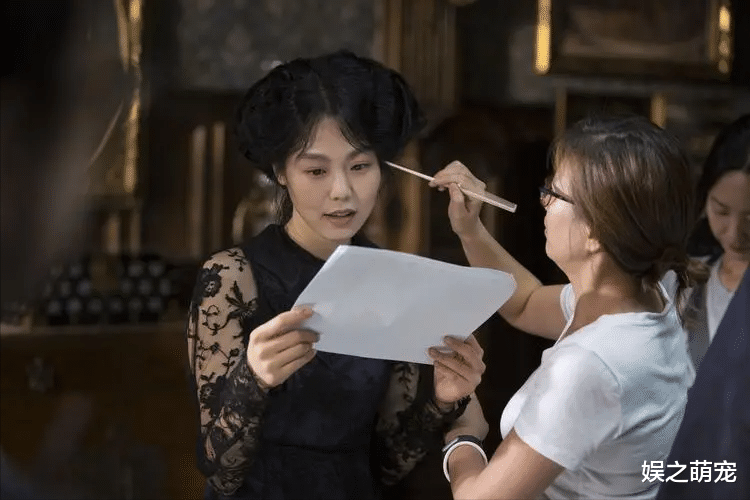
即使是玉清写下余家驹的姓氏被人发现,或是去窗口寻余家驹时不巧碰上娇娜的慌张,周文珠通过保持谈吐温文,收敛着感情的强烈起伏。
在行动的细微差异中表现角色变化,显示出人物心理对情感的自控以及是非分明的清醒态度,将出场字幕中玉清"皎如月,冷如冰"的人物特征展现尽致。

周文珠的表演看似静默而自制,但是她感知人物处境的变化并对其表现做出细微调整,呈现出沉默、安静、欲言又止等不同心理状态。
在这部作品中她的表演已展现出对角色心理微妙把握的能力,与韩云珍外放的表演风格对比也毫不逊色,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角色时常对现代思想态度开放而行动保守。

面对内心情感与外界产生冲突之时,人物选择隐而不发,态度婉转哀伤,因此人物表现出暧昧复杂的形象气质。
周文珠懂得刻画人物的复杂心理,她准确把握情感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类影片的思想表达。

朱瘦菊导演的另一部作品《儿孙福》,影片整体表现风格与前作相似。
周文珠在其中饰演的母亲何氏是一位年轻的寡母,由于她的丈夫意外突然离世,她不得不独自抚养两儿两女,帮助他们成家立业。

影片将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子女同代人之间的隔阂进行群像式的表现,全方位地展示一个家庭的幸与不幸,通过着重刻画母亲的良苦用心,也反衬出子女的不孝与不团结,说明父与子一代关系的隔阂不可控制。
据目前保留的残片来看,影片集中表现何氏的妇女和老年时期,周文珠对母亲两种年龄状态的演绎,显示出她在银幕表演上的野心。

也巧妙地通过同一角色不同时期的差异表现,证明她可以较好地适应角色类型变化的能力。
影片塑造了一位一心只为家庭操劳、为几女着想的母亲、家中有一个推卸责任、脾气暴躁的丈夫,既不关心家庭生活,还把自己的错误怪罪在家庭上。

影片开头丈夫把东西摔碎一地,并且情绪激烈地抱怨妻子,何氏抱着幼小的孩子没有反抗,还在担心孩子的病情,周文珠通过不发一言的悲凉神情展现母亲家中地位的边缘和弱小。
何氏在片中呈现的状态始终是隐忍而悲苦的,周文珠有几处皱眉动作,结合细微的神情变化,表达出角色内心欲言又止的复杂心理。

譬如,何氏在管教女儿的时候,发现刚教育完的小儿子偷溜出了家门,她的说教在此变得没有说服力,同时何氏自己也因此忧心忡忡。
周文珠的这段表演,首先是看向门外表现出疑惑的神情并微皱起眉头,得知儿子离开了家后摇头,当眼睛转回一旁的女儿时,斜眼抿嘴的动作,疑虑立刻转为了无奈。

整体表情变化简练,但是表意明确,值得揣摩。
这一场戏不止说明了她被家庭琐事困扰,也刻画出何氏与孩子之间拥有交流的隔阂,人物皱眉的原因,与先前对着小儿子哭诉、指责女儿时的皱眉并不相同。

前者是伴随哭泣的愁容满面,后者是带着严厉训斥的愤怒情感,表现出母亲对子女的复杂情感。
何氏在保护儿子不受丈夫殴打时,周文珠通过肢体动作和神情变化演出了一个母亲在家庭处于弱势的处境。

何氏冲到房间门口挡住丈夫的去路,双臂张开,露出恳求的神情,周文珠表现出的行动近乎身体本能的反应,她的眉毛弯成向下的八字,眼神也是由下至上地抬起。
在丈夫面前降低姿态并为儿子求情,而在丈夫不肯妥协的行动过程中,她的姿态也逐渐变得坚毅起来,身体更积极正面地展开对抗,不再完全是委曲求全的样子。

虽然影片后半段采用群像的方式进行叙事,前半段描绘了较多何氏的生活处境,周文珠的表演没有将这些看似充满家长里短的情节变得乏善可陈。
而是将人物性格和复杂心理在日常片段的堆叠表现中更加充盈写实,观众可以从更多的细节层次中了解角色状态。

周文珠在《儿孙福》中还对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和行为进行了模仿,塑造老年人的形象。
在影片后半部周文珠以银发皱纹、缺牙和老花镜的造型出现,尽管当时的化装技术并不成熟,她的形体表现始终尽量保持佝偻驼背的状态,行动时动作相对迟缓,弥补了这种视觉上的不足。

周文珠在老人动作和神情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譬如,因为视力不足,她总是越过老花镜看远处,眯缝着眼睛看,给人感觉眼神没有焦点,而当她拿起近物时又会特地拿远一点。
好像能够更仔细地看清楚,符合老人的举止和生活习惯。而在表现老人和儿女讲话时,周文珠基本都是躬着身体头伸向前的姿态。

一方面是老人耳朵听力下降所导致的惯性,视觉上给人老态的气质,也同时直观地从对话关系上展现了母亲和几女的情感不对等,展现出难以真正变得亲近的亲子关系。
电影残片里可以捕捉到周文珠对表演的适度分寸感,她初次在银幕上饰演的老迈形象称不上出彩,对老人行动的还原也有些笨拙。

但这种不熟练作为老年身体表现的一部分融入到了表演当中,这次尝试也成为她银幕生涯的重要跨越。
《清宫秘史》中周文珠扮演伶人的妻子凤英,凤英在演剧之后被迫与丈夫分离,困于亲王府,当她知道自己不能脱身后产生了极其悲愤的情绪。

当时的影片评价肯定了周文珠对人物心理状态准确把握,“悲愤”和“悔恨”是两种不相同的情绪,但很容易被混淆简化成为单一的“恨”。
要区别这两种相似的情绪是有一定难度的,“伊始终坚拒,后来伊知道不能脱身便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唱托宫女交给伊的丈夫。

周文珠表演这满腔悲愤的神情,堪谓恰到好处。面部的表情,四肢的动作,以及全体的姿势,使人一望而知是‘悲愤’,不是悔恨。
周文珠从神情状态和动作表演上都没有过度表现,还原了悲愤的情绪,也得到了当时观众的肯定。
注重面部表演与情绪分寸把控电影技术的进步影响了电影镜头景别和场面调度的选择。

写镜头在1920代开始有了广泛应用,在近景或特写的镜头下,演员的面孔被绝对放大,成为观众注意力的焦点,演员脸部的细节变化将会是人物情绪表现最直接的途径。
郑正秋曾谈起电影表演“在银幕上,因为又大又近,就此不宜过于做作。

无论眉目只见一颦一笑,哪怕极细微的动作,都会有过火和不自然的危险,何况于举手、动足、起坐、立、走、更容易出毛病了。
“这一观点概括了早期电影表演形式不宜繁复夸张的特点,讲求表演的节制和准确性。

1920年代的电影表演在讲求真实性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内心表演"的观念说法,凤昔醉和万籁天都分别发表文章就"内心表演"做出界定分析。
凤昔醉认为内心表演者,其表演由心中而传达于面上也,故须心中有所感动,而后面上始能发生表情。

强调了演员与角色的情绪体验共振才能将内心感受通过面部表达出来,万籁天则认为内心表演者,非如其名之赤心示人也。
实则欲知心腹事,但看目中情耳,因影剧之工为物,不类戏剧之口中言可以传达心意,其一切情绪,皆由目光中流露出来。

强调演员需要切身体会角色的经验以及眼神传情的重要性,尽管阐述重点有所差异。
最终指向都是对角色情绪、经历的体验、认为银幕表演应当生活化、写实化,自然表露人物细微情绪变化。

"内心表演"显示出早期中国电影对演员面部表演的重视,理解角色的内心活动也是演员进行表演的重要前提,当时有评价指出了周文珠的情绪表现能力。
周文珠女士是饱含着生活挣扎的情绪表现,所以她可以是沉静的,也可以是流动的,处处显出深刻的含蓄。

她善于调动面部表情来诠释人物的情绪,在亦动亦静的变化中维持着表演的分寸感。
《殖边外史》中周文珠扮演的后妈,对继女黎阿贞态度凶悍,并企图与自己的侄子合谋通过不道德的方式侵占夫家的财产。

周文珠生动形象地演绎出角色的情绪发展,将人物状态刻画得比较到位,最典型的是她在同一场戏内快速地切换
两种态度变化,从短时间内面部表情的差异表现了后妈的双面派性格。如周氏推搡继女之后进行告状,周氏快速由阴冷转为谄媚的神情。

又或者,而对继女出嫁前生病想要推迟结婚的请求,周氏毫不犹豫地凶狠拒绝,而转头看向外人时立马表情变得和善起来。
影片与后妈相关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周氏和侄子周顺卿预谋的过程展开,大部分设计是为推动戏剧冲突发展而存在的,后母是个一心为自己着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周文珠通过几次抬头时的神情变化,把后妈富有心机的形象呈现出来,她的面部表情做出了迅速而明确的状态切换,将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
当侄子提议把继女嫁给他的时候,周氏首先表现出的是不以为然,认为侄子提出的请求不过是些玩笑话,抬头看着侄子,眼神发出质疑,中途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转头干活并没有给予理睬。

侄子见周氏无动于衷,想通过讲情理来让周氏帮忙,可是侄子本来就为人不佳,也已有相好的对象,周氏继而撤了撤嘴,眼神带着轻蔑,表明她对侄子的不信任。
于是侄子进一步说出对周氏处境更有利的话,试图挑起她的兴趣,周氏显然对侄子所说的事情有些许心动,她不再像前两次快速地抬起头回应侄子的话,而是停下了手中在干的活。

抬头先朝远处看了看,再转头意味深长地和侄子对上眼,最后眼神停在了侄子的身上,长久没有接话。
从周氏的反应可以看出她意志在侄子劝说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影片在拍摄这段情节的时候,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景别变化。

由中景出现姑侄两人谈话的场面,切换到特写放大周氏的表现,当周氏被侄子几乎说服,景别松动,变为近景。
镜头拍摄从形式上暗示了周氏接下来可能会做出的行动,也体现出她自私的本性。

周文珠采取将后妈的心理活动用面部表情外显的表现方式,也恰好成为后妈两面派为人的一种展示。
周氏在看似不经意的时刻提出继女的出嫁事宜时,她的表情暴露了她的企图心,黎长福提出女儿要嫁给小时候一起长大的竹马,周氏立刻转头翻脸,皱紧眉头瞪着眼睛,做出不可思议的夸张反应,以表示她对此决定的不满。

而后,黎父问周氏的看法,周氏转头眼神马上就显得柔和了许多,若有所思地告诉黎父让自己侄子和继女结婚。
在说出“预谋”的过程中,她的眼睛并没有像开始直接表达消极情绪那样,牢牢盯着对方,而是飘忽地朝一旁看去,并非常快速地眨了一下眼,又重新看回来,直到说完自己的想法。

这段特写镜头里周文珠的面部表情变化微妙且充满迷惑性,一面打着为继女好的帆子,一面为自己的私心说谎,塑造出后妈势利眼的形象。
在《儿孙福》中周文珠也通过面部表情的层次表现,表现出人物更完整和复杂的性格。何氏由于偶然丧夫,不得不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这种家庭氛围使得她的个人情感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她的需求始终不是首要的。
影片中母亲的行动和情感表现往往是跟随几女的行为发生的,而当她发现丈夫离世的事实时,三次镜头切换到周文珠的近景画面,面部表情成为观看的视觉中心。

暴露出何氏未受控制的本能反应,先是惊讶和无助的情感表现,转而在她突然松懈的眼神里看到了面对丈夫的死亡时短暂的如释重负,但是当她再次看向自己的孩子。
何氏又意识到了自己的母亲身份,随即眉头不自觉地又皱紧,情绪变得紧绷。

尽管只有短短几秒的表演,周文珠的面部变化十分简洁和节制,没有过分渲染单一的情绪,将何氏丰富的情感波动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因为镜头景别的缩小具有强调的作用,有时可以超越语言的表达,影响着角色情感的再现和观众情感的投入,贴合人物性格、进行准确的面部表演是写实表现的重要基础。

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提出过"微相学"理论,意指"根据细微的面部表情变化来体验和了解人物内心活动的细微变化。”。
严结合了电影的镜头变化,认为可以通过人的面部超越空间的限制,进入人的心灵世界,这一说法和早期电影表演的需求有着共通之处。

都强调演员面部表情细腻和写实的表现,周文珠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变化控制情感的力度,展现出她进行面部表演的能力,以及切身体会角色思想性格的自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