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某日,江西省民政厅职员王家珍于瑞金县叶坪乡调研,至傍晚,与途中邂逅的两位村民交谈起来。
他询问道:
二十年前,附近是否有家庭收养过红军后裔?
出乎意料,一位老伯稍作思索后言道:
朱坊村老朱家曾收养一名孤儿,据传此娃为红军所留。
王家珍闻言,猛地拍腿,心中激动:历经数月搜寻,终有了一丝线索。
他焦虑万分,渴望即刻赶往那户人家探寻真相,奈何夜幕降临,只得暂且返家歇息,待明日清晨再去寻访。

临睡前,他思索:若真有消息传来,毛主席与贺子珍同志定会深感欣慰。
确实,他们寻觅的正是二人之子毛岸红。与声名显赫的毛岸英相比,毛岸红至今仍鲜为人知。
毛泽东几段婚姻中共有十个子女。
战火纷飞时,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衲四人靠民众养育与历练成长,广为人知。其余六人则或早年夭折,或行踪不明,鲜有人知晓。
毛岸红与其他孩子失散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颠沛流离,毛泽东的十个子女】
毛泽东的十个孩子中,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及三子毛岸龙均为杨开慧所育。

毛岸龙出生时,毛泽东在井冈山。母亲过世后,他与兄长们在上海地下党开办的幼稚园生活,该幼稚园专为党员子女设立。
后来,因叛徒出卖,幼稚园遭破坏,他在此期间病逝。他与毛泽东虽为父子,但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1928年,毛泽东因长沙情报有误,误信杨开慧已牺牲,遂与井冈山首位女党员贺子珍结为夫妻。

至1937年底,贺子珍前往莫斯科,她与对方在十年婚姻中共育有三子三女。
长女诞生于1929年,为毛泽东首个女儿,深受主席喜爱,被赐名“金花”。
但红军刚占领龙岩,随即又要转移,毛泽东遂为贺子珍寻得一户人家寄养,告知她:
革命胜利后,我们将重新寻回她,让她回到我们身边。
产女后即将分离,贺子珍内心痛苦,却也别无良策。
1932年4月,她返回欲接小“金花”,却得知孩子已因病去世,深感遗憾。
同年底,贺子珍于福建诞下男婴,缓解了丧女之哀。毛泽东依辈分命名其为毛岸红,与毛岸英等三兄弟齐名。
孩子出生时,贺子珍患疟疾,医生告诫避免母乳喂养以防传染。
毛泽东为新生儿子毛岸红找了一名奶妈照料,因受当地习俗影响,奶妈常以其小名“毛毛”呼唤,久之,众人皆以“毛毛”代称毛岸红。
毛毛在夫妻身旁成长,转瞬已两岁多,他浓眉大眼、口齿清晰,深受毛泽东喜爱。

在忙碌之中,我总会抽空拥抱、逗弄他,并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要时常陪伴在他身边,给予关爱与欢乐。
你长大后定能超越我,因你名字中比我多了一个“毛”字,这或许预示着你将有更多潜力与成就。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
毛泽东与贺子珍商议后,定将毛毛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夫妇在根据地抚养。离别前,贺子珍取棉花,亲手缝制棉袄给毛毛。

苏区遭敌占领后,为保安全,毛泽覃将毛毛隐秘送至江西瑞金一警务员家,托其寻觅合适老乡进行寄养。
毛泽覃英勇牺牲后,与那位警卫员的联系中断,导致毛毛自此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早产一男婴,因反“围剿”战争环境艰苦,孩子不久夭折,甚至未及命名。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某小村,贺子珍于此诞下一女婴,此女为毛泽东第七个孩子。
前方长征路遥远艰苦,危机四伏,贺子珍无奈再次放弃刚出生的孩子,交由当地白苗族老乡抚养。
一年多后,贺子珍在陕北诞下一女,小名“娇娇”。相较于兄长姊妹,娇娇颇为幸运,能在父母近处生活。
1940年,李敏被派往苏联,陪伴在莫斯科就医的贺子珍,期间毛泽东正式为她命名为李敏。
同年末,江青诞下毛泽东第十个孩子,亦是最后一个,名为李讷。

姐妹俩的命名源自《论语》中的某句,该句被精选为她们的名字,既保持了文化底蕴,又彰显了命名的深意与精准。
君子应言语谨慎,不轻易发言,而在行动上则需迅速敏捷,果敢决断,以实际行动展现能力与决心。
姓李而非毛,源于毛泽东当时使用化名“李得胜”。
贺子珍抵莫斯科后不久,诞下一男婴,为毛泽东第九子,位于李敏与李讷之间。
毛泽东未见他,未赐名,仅知贺子珍唤其“瓦沙”。此子不足一岁,患重感冒转肺炎,就医途中不幸夭折。
同时,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婚姻因她坚持离开延安而终结。
贺子珍在莫斯科未等到毛泽东的和好与关怀,却收到要求结束婚姻的信,这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寻找“毛毛”,毛岸红身在何方?】
贺子珍在苏联历经十年苦难后,终于在建国前夕重返祖国。
这十年间,国内形势巨变:日寇投降,国民党败退,新中国迅速成立,革命成功。她与毛泽东的婚姻也已结束。
在沈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迁居上海隐居。对于那段婚姻是否后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她深深思念着自己的孩子。
在她生育的六名子女中,除李敏外,三子已夭折,另有两女下落不明。寻回这两个失踪的孩子,是她当前最迫切的愿望。

长征途中,于贵州诞下的女儿,刚出生即被托付给当地村民。
无名无貌,亦无辨认之物,何以寻觅?贺子珍经多方探问,皆无所获,终无奈放弃。
或许,唯一尚存希望寻获的,便是“毛毛”了。
贺怡,作为毛泽覃的妻子及贺子珍的妹妹,对寻找毛毛一事同样极为关注。
贺怡夫妇最初共同承担了照顾毛毛的责任,毛泽覃牺牲后,毛毛失踪,作为婶婶兼姨妈的贺怡深感愧疚。
因此,她始终惦念寻找毛毛,但因战事紧迫,她需兼顾工作与照顾李敏等人,始终未寻得合适时机去打听毛毛的消息。

解放前夕,事情迎来了转机。
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后,暂住于北京香山别墅。
一日,贺怡来访,满面喜悦地告知毛泽东:已获毛毛消息。
毛泽东闻之,心中略感激动,但听完贺怡详述后,转而生忧。
他觉孩子与记忆中的毛毛大相径庭,但贺怡激动不已,仍决定速往江西带回孩子,以便毛泽东亲自辨认。
数月后,贺怡前往吉安任职,途中重访赣南寻找毛毛,却遭遇车祸。
贺怡不幸当场逝世,其余乘客,含其子在内,均受重伤。

毛毛的线索又断了,毛泽东闻讯后沉默片刻,随后说道:
别让这孩子再寻了,就让他留在百姓之中吧。
【一波三折,朱道来到底是不是毛岸红?】
尽管毛泽东已表明无需再寻且未再提起,贺子珍作为母亲仍不愿放弃,尤其在独居上海期间,对孩子的思念愈发强烈。
1953年,贺子珍致信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细述毛毛相关事宜,并恳请其协助寻找。
事实上,邵式平在收到贺子珍信件前夕,已接获中央电报,指令协助寻找失踪的“毛毛”。

为此,江西省政府特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王家珍等成员遍访江西各地,尤其在瑞金,他们几乎逐户进行走访调查。
因此,文章开篇所描述的那一场景便应运而生,保持了原有的逻辑与中心思想,用词精准且表述流畅。
王家珍等人坚持不懈地寻访后,终获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1934年秋,朱盛苔与黄月英夫妇收养一名男孩,该男孩由两名红军送来。
名叫“朱道来”的年轻人,年纪与毛毛相近,血型匹配贺子珍,且面容与年轻毛泽东有几分相似,这一发现尤为引人注目。
综上所述,江西方面确认,朱道来即为昔日所称的毛毛。
贺子珍审阅资料后,情绪略显激动,认为该孩子极有可能是自己失踪的儿子毛毛。

黄月英等人抵沪后,贺子珍目睹朱道来时,情绪难抑,激动不已。
端详朱道来许久,她颤声说:“毛毛,这正是我的毛毛。”终难以自持,她紧紧抱住朱道来,痛哭起来。
照片送达时,周恩来与刘少奇先行审阅,均认为其与毛主席有几分相似。随后,该照片送至毛主席处。
然而,毛泽东阅读后并未直接表明态度,仅淡然回应道:
这个孩子与年轻时的毛泽覃相貌颇为相似,从外貌上看,二者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令人不禁产生联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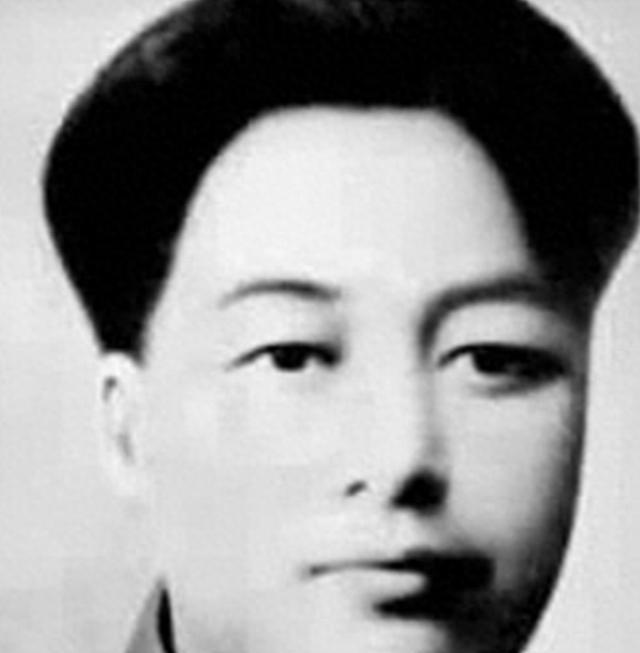
此句非全然否定,于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认同。
事情再次转折:一烈士家属向中央反映,称朱道来非毛岸红,亦非毛主席之子,实为其子霍小青。
朱月倩乃烈士霍步青之遗孀,1933年霍步青在福建牺牲后,她诞下孩子,并以霍步青之名,取名为霍小青,以资纪念。
1934年,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村民抚养,毅然踏上革命道路,从此与孩子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她依据记忆前往江西寻找孩子,最终成功找到了黄月英一家。
事情进展令负责同志为难,两位母亲均坚称朱道来为己出,且二人均为革命立下大功,现今皆迫切寻子。
特征或相貌均无法确定亲子关系,若发生误认,将如何应对?

当时,华东局办公厅主任亲临处理,经大量调查仍难定论,因过程中突发一个小插曲。
黄月英与朱道抵沪后,贺子珍热情相待,并详细分享了毛毛往昔生活的诸多细节。
工作人员询问黄月英时,她坚称朱道来是贺子珍与毛主席之子,并出示一件小棉袄作为贺子珍当年的留证。
工作复杂性增加,是朱月倩误传,还是黄月英等人希望证实朱道来的身份,而故意提供相关证据呢?此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证。
朱道来对自己身世一问三不知,因他被领养时年仅三岁,对那般遥远的事情毫无记忆。

工作人员只能将情况上报中组部,请求其介入处理。
【毛泽东一锤定音:红军后代,党来养!】
朱道来抵京后,邓颖超、帅孟奇等众多领导前往招待所探望该孩童。
朱月倩到场,看过孩子后坚称其为己子,这一举动使众人愈发为难。
失散多年且缺乏先进医疗手段鉴别血缘,孩子究竟是贺子珍还是朱月倩所生,当时无人能给出准确结论。

关键时刻,毛主席果断决策,一锤定音。
他听完周总理汇报后,立即作出结论。此事在李敏女儿孔令梅的书中有所记载。
外公审视照片与材料后断言:他虽不似幼时模样,终究是红军血脉,应由党组织培育。
资料显示,邓颖超受中组部之托,召集知情老同志,就孩子归属议题进行了讨论。
座谈会上,邓颖超宣布:“朱道来”实为革命烈士霍步青之遗孤,本名霍小青。
但贺子珍及其兄贺学敏等人,始终坚信朱道来即是他们失散的孩子小毛毛。
最终,朱道来既未赴南京朱月倩处,也未至上海贺子珍处,留京继续学业,日常生活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

帅孟奇家中收养了一批烈士后代,因此在照顾和教育他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多年后,朱道来仍与三位“母亲”保持密切联系,但因技术限制,其身份始终未能完全确定。
毛泽东一生在处理子女问题上,始终秉持无私原则,未曾有过个人偏袒,坚持公正对待。
1950年底,近花甲之年的毛泽东闻悉毛岸英牺牲消息,深感悲痛,挥笔写下《枯树赋》名句以抒怀。
昔日汉南种柳枝,今朝摇落满江潭。树经岁月已凋零,人生短促更何堪。
他强忍丧子之痛,反过来劝慰众人:战争难免牺牲,勿因其子而过分哀伤,视此为常态。

三年后,关于朱道来是否为毛岸红的问题,他首要考量的是另一位革命母亲的感受。
他的十个子女中,多数曾被寄养他处。他曾深情述说:
这些孩子自幼历经艰辛,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遍尝百家饭食,足迹踏遍万里路途。
这十个孩子中,三人早年夭折,另有三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当年,他得知贺子珍遗弃刚出生女儿的消息后,表示过:
我们投身革命旨在惠及后代,但彼时因革命需要,却无奈舍弃陪伴后代的时光。
伟人的广阔胸襟,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其气度非凡,彰显出崇高的品质与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