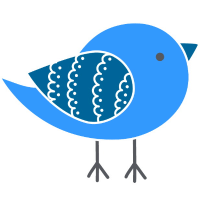2
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高中年级6个班,4个理科班2个文科班,每个班50名学生,这些学生均来自全县各个乡镇。能考上县一中念高中的学生,毋庸置疑,都是很优秀的。文理分班是在高一上学期,经过分班考试,学生的选科,就这么定下来了。再就是学校配给各班各科的教师,教师一配好,就跟班走,从高一一直跟到高三。许平所在的班,进校时是高一(4班),经过分班,就成了理科高一(3)班,接下去就是理科高二(3)班高三(3)班了。班主任李焕青是教物理的,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40来岁,微胖,身材不高,穿着得体,衣服换来换去给学生的感觉还是原来穿的那一套,黝黑的脸,额骨微微隆起,充满智慧的眼睛凹进两道浓密的眉宇之下,更显得清澈深邃,厚厚的嘴唇,低而略宽的鼻子,所有这些,使他的脸有棱有角,这么多年的沧桑岁月和辛劳付出好像都刻在他坚毅的额头上。

教室后面有一张桌子,单独成一排,那就是李老师的专用桌,抽屉里放着粉笔、参考书、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每天早晨的半小时早读和下午第三课时的自习课他都会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备课或批改作业。学生们老老实实不敢动弹。李老师明文规定不允许男女生讲话,当然更不允许谈恋爱。一开班会就强调:“三年后,你们就各奔东西了,这期间,千万不要谈情说爱,你们心智还不成熟,你们还真不懂得什么是爱、怎么去爱,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了。”开始,同学们哄堂大笑,继而好像都在揣摩老师话的份量,个个沉默。女同学更是把脸面搁在桌面上或捂在掌心里久久不愿抬头好像被熊似的。许平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他没有和班上哪个女孩背前背后搭咯什么但他还是出了一身汗。他是学习委员,出于责任,要收发作业本,也要经常和女同学讲话,有时也会迎来那么莞而一笑,有时也得接受来自女同学的怪脸色。这一点,他比其他男同学优越,是老师给他的特权,这一点,同学们并不计较。有些男生也想试试,但又不敢越过这条防御地带,一跨过去,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情来。
李老师规定,同学们每天必须要到教室上晚自习课。这条规定,对于住校生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那些离学校十里八里路程的学生就不一样了,住校吧,花那些住校费伙食费又不值得,不住吧,每天晚上还要来回跑。同学王晓云就是不住校的一类。她家紧靠铁路线,县城火车站离她家镇上也就一站远,十分钟就到了,慢车站站停。她通常是晚上下自习走,第二天早晨又返回学校。这样一来,她坐车就是她每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但她无论把时间安排得多么妥当,时间长了,还是有惰性的,有时干脆就不来了,在家学也是学呀!所以她经常挨老师熊,轻则脸红,重则哭鼻子。她一副聪明相,眼睛机灵机灵的,薄薄的嘴唇关不住她的嘴,她爱说爱动,但大多数和许平说笑,因为许平是学习委员,又是邻位,座位仅隔一个走道。不仅许平惊讶,连李老师也佩服,每次考试,她的成绩总是处在班级前十名。所以大家知道,老师熊她,也是点到为止,过多的是表扬。
那晚,王晓云又回家了,第二天上早自习课时她才回到教室,头发梳成马尾巴的样子,用橡皮筋高高地束起隆在后边,走起路来,“马尾巴”上下一跳一跳的。同学们眼光聚焦在她头上,她脸绯红,鬼知道是羞的还是风吹的。下午下第二节课的时候,许平送物理作业本去老师办公室,老师突然问他:“王晓云来了没有?”许平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按规定,学生考勤是班长负责的,老师这么问我,好像是我没有看好她似的。李老师昨晚并没有在教室呀,他怎么知道她没来呢?是谁打了小报告?肯定是班长了。许平赶忙说:“上早自习课时,她就来了。”李老师长嘘着一口气,说:“这孩子聪明是聪明,班里几个女生就数她了,高考她把握性最大,不过就是不用功,最后的关键阶段了,你要管一管同学们的学习,最近学习气氛有点松懈了,是不是觉得成绩好坏已定型了?下一节课,我要叫几个同学上黑板做题目,看看到底怎么样,会还是不会。”老师说着,许平机械地点着头。回到教室,许平把这事告诉了王晓云,让她有个“爬黑板”的心理准备。她把物理书掏出来哗啦啦心不在焉地翻翻,又啪地合上,调皮式地看着许平,说:“哎,许平,我明天上黑板,要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你帮我提示提示。”其实她说的是多余的话,怎么提示呢?又不是在下边,我们俩能围绕一道题,交头接耳,大方地讨论。讲台上怎么行呢?许平心里想着,但还是不加思索地点头说:“好!”

上课铃还没有响,李老师就径直走上讲台,顺手拿起一支粉笔,手搭在额头上想了一下,然后写到黑板上。同学们蹑手蹑脚地回到座位上,看着黑板。“杂技演员在半径为R的圆形墙壁作飞车走壁运动,墙的摩擦系数为µ,人加车重量为G,问车速达到多大时才不至于掉下来而作匀速圆周运动?”写完,李老师在教室里走了两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同学们屏声静气,空气凝固了,生怕叫到自己头上。李老师还没有走到讲台上,边走边喊:“班长,你带个头,上来!”班长郭树栋犹豫地站起来,抓耳挠腮。他平时反映不快但很用功刻苦,因此成绩还算过得去,同学们不大喜欢他,怨他干事呆板,过于认真不讲情面。“不——会。”长时间的沉默,还是不会。“坐下。戈军呢,上来。”李老师叫班长坐下的那短促而铿锵的声音使大家一怔,只见戈军慢腾腾地弓起他细长的腰,沉默,“不——会。”“坐——下!”李老师拖着很长的“坐”字音,“下”字一声很干脆。
这是李老师的开场戏,找一个对题目反映不太灵活的但对题目又感觉不是很深奥的同学上来做,是做不好的,真正能做好题目的他要放在最后喊上台,老师回回这么做,反而让前边上台的同学很难看,私下里这些同学都不喜欢李老师,倒是嫉妒起后边上台会做题目的同学了。这回要轮到王晓云出场了,许平不由得偏过头看她,只见她在稿纸上画了一个不像别的女孩子画得很规矩的圆筒,内壁有个东西在挂着,纸上还有她计算的公式。许平侧过头看她时她也注意到了他在看她,于是她欠过身把稿纸拿给许平看,小声地问:“咯是这么解的?”许平说:“是的。”她莞尔一笑,转身挺直了身。
“王晓云,你来解一下。”李老师喊道。同学们齐刷刷地抬起头看着她,都轻松地松了一口气。王晓云看了许平一下,笑了,然后快步走上讲台。李老师在侧面看着她在写在画,此时此刻,老师绷紧的脸松了下来,露出了一丝笑意:“好!好!好!”王晓云做好后带着一种恰意的微笑轻飘飘地回到座位上。然后,李老师面向大家解释:“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乍看起来,似乎无从下手,只是拐了一个小弯,只不过是‘牛二’定律加静力平衡,圆周运动加‘牛二’定律的运用罢了。”
这一次,算是给大家打了一针镇定剂,连向来往回家跑的王晓云也不回家了。
毕业之前,准备解决最后一批同学们入团的问题。由于整天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一时抽不出空,班级团支部委员会决定抽个中午放学时间,把学生入团的事情讨论讨论,并邀请李老师参加。在讨论每个人的入团问题上,班长总是拿着条条框框说事,说某某同学条件尚未成熟有待考察发展,参会的人总会争得面红耳赤。在提到王晓云入团问题上,他说:“今天,李老师在场,是最后一次讨论入团的问题了,按理说给大家一个顺水人情,都通过算了,带着团员的身份进大学进社会;但是,共青团组织是纯洁的组织,是党的后备军,青年的先锋队,这就要求我们在座的还是要按标准来衡量。关于王晓云,我承认她的学习成绩不在话下,但有点那个,什么事都有点不在乎,小聪明,有时无视课堂纪律,自觉得缺那么几节课也并不比你们成绩差,这一点李老师不是不知道。”他边说边求同似地看着老师,接着说:“再者,那个、那个苗头也不大对劲。”许平心里咯噔一下,他会把那些上纲上线的问题全都搬出来,真遗憾他爸妈把他出生在这个年代,要是在风风雨雨的文革十年中,他绝对会高举语录英雄气势置人于死地,叫你浑身是嘴说不清楚。“就拿她的打扮来说,时下流行的马尾巴带进了班级,引人注目,一些同学拿她成了笑柄,说什么马尾巴功能是什么,跑呀跳呀。”郭树栋振振有词的发言叫你找不到一点漏洞,再枯燥无味的东西他总会把它盘得圆圆滑滑,有滋有味。许平不能再听下去了,“班长同志,关于你提及的那些,我再谈谈我的看法,确实,她在遵守纪律方面就是缺那么几节晚自习,但是论学习成绩,你这么认真可还是略逊一筹。请原谅我直说,这是事实。今天我也当着老师的面我敢说我们班同学如果成绩都能像她那样占居前十名,统计一下,也就是全年级前四十名在我们班,如果是这样,我宁愿我们班同学都少上几节晚自习。如果你把这么个问题揪着不放也按条条杠杠说事,那么我问你,你要发展哪些人,不上线不上把的人吗?还有那个发型不发型的,人家是所好,怎么舒服怎么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以说那是一种美,为什么不允许人家美呢?至于男生他们爱讲啥他们讲是了,他们长期地被某种认为是不良的是邪恶的意念所禁锢,一旦有什么新鲜事他们像伸头鱼鳄似的大惊小怪,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却认为不得了了,世风日下喽。也难怪,我们被禁锢得太久了,不过班长你要负主要责任。”许平有点激动了,也有点肆无忌惮了,不过他知道班主任李老师还是欣赏王晓云的,不可能因他的检举而削弱了老师对她的好感,他倒是有点可怜班长了,班长啊班长,你失算了。
其他几个支委一直缄口不言,但是从他们对许平的发言所流露出的表情上来看,他们是过得去的,这使许平心理得到一些安慰。最后,由李老师作总结,他还是老一套,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有意见有分歧总是避免不了的,入团的事由支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谁一个人也不能掌握一个人的命运。

对李老师,许平能说他什么呢,难道在这种场景下要求老师偏向自己吗?不可能。老师只能以这种方式折中,况且班长是绝对按照他的路数来要求别人的,在这一点上,班长是老师的忠实门徒。在许平看来,念了这么多年书,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老师,这么要求严格的老师,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操碎了心。
在回寝室的路上,几个支委闷闷不乐,只顾往前走。还是许平打破了这个难堪的局面,拍着班长的肩,说:“何必为这事伤脑筋呢?就这么两个多月时间了,很快就各奔东西了,将来某某某上大学了,还不是团员身份,我们也不好看。唉,班干部,也难呀!”
“我真羡慕你,不光学习好,而且,就连……”许平心里一咯噔,头脑一怔,班长从来不说半吊子话,今天怎么了?他说话向来都是单刀直入,今天怎么了?就连、就连什么呢?难道他内心还有什么话不便说出口?还有什么积郁不便发泄出来?
“许平,你是不是对她有点那个了?我早就看得出,你俩互生情愫,难得啊!”
许平突然明白了,明白了那个“就连”的下句,明白了“那个”的意思,他真没往“那个”上想,不过想想也很欣慰,她真有“那个”意思?不过他还是愤愤然地回击:“班长,我向来是尊重你的,今天你说这话你要负责!”他几乎大喊,同时握紧拳头。怪不得人家,他摇摇头。
作者简介
陶继亮,笔名水拍岸,安徽省明光市作协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乡镇、市直机关,曾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市水产局副局长、市委组织部选派办主任、市人社局局长、市民宗局局长、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等。散文、小说散见于《滁州日报》《明光文学》等媒体公众号,散文《孤独的“正塘”》入围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入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