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叫槐树湾,路是土的,房是泥的,穷得叮当响。
我二十八岁了,还是个光棍,村里人总是不怀好意揶揄我:“小栓子,眼瞅三十了,夜里想女人不?”
我心里急,可咋办?
槐树湾的姑娘早跑城里打工去了,谁也不愿意嫁在这山沟沟里,男多女少,娶媳妇,在我们这儿比登天还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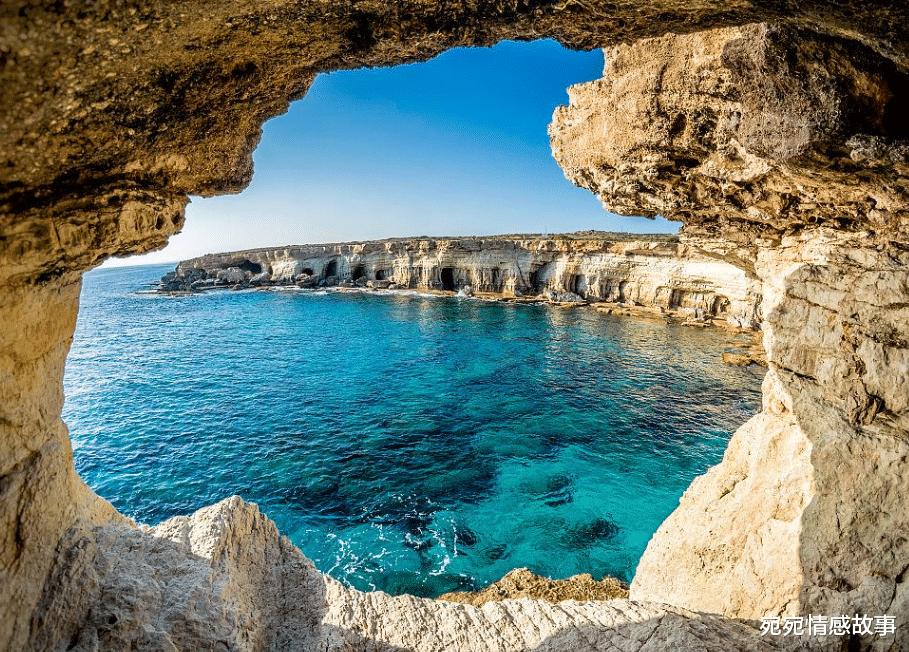
那年春天,我爹狠下心:“砸锅卖铁也得给你弄个媳妇!”
家里东拼西凑,找了个媒婆,说外省有个姑娘,模样俊,二十二岁,家里穷,愿意嫁过来,要十万块彩礼。
十万块啊!我们家种地一年才攒两三千,我爹把能卖的都卖了,又借了五万,才凑齐这钱。
新娘叫小翠,来的那天穿件红花袄,皮肤白净,眼睛水汪汪的,跟画上的人似的。
村里人围着看,啧啧称奇:“小栓子这回有福气咯!”我头一回见她,脸红得跟烧熟的铁,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婚礼简单办了,请了几桌人,杀了两头猪,摆在院里吃了顿席。
晚上她睡在我旁边也不吭声。
一个月后,她还是整天闷着不吭声。我下地干活,她就在家喂鸡,扫院子,话少得可怜。
我问她咋了,她就笑笑:“没事,不喜欢说话。”我爹看她老实,说:“这媳妇不错,能过日子。”
可我总觉得,她心里藏着事儿。
一个月后的赶集那天,村里人一早挑着菜去镇上卖。我扛了两筐土豆,小翠说想去看看热闹,我就带她一块去了。
集市上人挤人,卖菜的、卖鸡的吆喝声不断,小翠跟在我后面,东瞧西看,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丫头。
我忙着跟人讲价,扭头一看,她人没了。我急得满集市找,喊破了嗓子也没见影儿。
后来一个卖布的老头说:“刚才见个红花袄的姑娘,跟几个男人走了,往车站那边去的。”
我脑子嗡一声,筐子扔地上就往车站跑,可哪还有人?车站就剩几辆破三轮,风吹得灰扑扑的。
我蹲那儿,脑子里乱成一团,十万块啊,家底全砸进去了,我爹知道后,气得抄起扁担要打我:“你个没用的,眼皮子底下让人跑了!”
我没躲,低头说:“爹,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
这事在槐树湾炸开了锅。
有人笑我:“小栓子,十万块买了个婆娘就睡了一个月!”还有人怂恿我:“等抓回来,狠狠打一顿就老实了,隔壁村有个婆娘要跑,抓回来衣服扒了,腿都给打断了,这不不敢跑了……”
还有人悄悄说:“那小翠八成是骗婚的,外省来的多了去了,估计就是犯罪团伙,专门搞这种杀猪盘!”
那几天,我整宿睡不着,盯着炕头她睡过的地方发呆。她走前留下的红花袄还挂在墙上,我拿下来闻了闻,有股淡淡的香味。
我寻思是不是我哪没做好?可我天天干活到晚上,回来还给她烧水洗脚,对她也够好了,现在我明白了,她一开始压根就没想留下。

村里人议论了一阵,也就散了。
可这债还得还啊,这年头,农村光棍多得数不过来,花钱买媳妇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
隔壁村老张,花八万买了个越南姑娘,生了个娃才跑,算他运气好。我这十万下去,啥也没落下。
后来我听说,外省有些地方专门干这买卖,姑娘被卖过来,熬几天就跑,钱早分好了。
我没去找她,也找不着。十万块没了,我爹也病得越来越严重,我也慢慢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