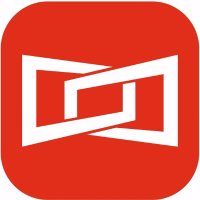文|草西
我是“隐于市”的字耕农,她是“隐于山”的真农人。五个月前,我翻越巴朗山,去见金子。从城里辞职、瞒着家人去种地,金子已在村里生活了两年多时间。我们都在探索独立于系统之外、最小限度与工具人合作、最大限度与自然人协作的生活方式。
1
七人座的旅游专车开过卧龙,来到巴朗山。垭口海拔4000多米,风景是美的,空气也是稀薄的。山顶有终年不化的冰雪,仅望一望,灵气便注入体内。巴朗山沿街,经幡飘扬在雾气中,农民摆摊卖着烤土豆、牛肉串。不少游客将轿车停在路边,走到山坳的平地拍照打卡,制造拥堵。
穿过巴朗山,就来到小金地界,两边的山带给人强烈的压迫感。金子所在的大水沟村,就隐藏在深不见底的群山中。大水沟村历来是富饶之地,贯穿村子的是一条隐没在杂草中的湍急小河,从不缺水。遇到旱季,邻村的人都跑来借水,拉巨长的水管。在海拔落差达500米的山坡上,分段种植着采收期不同的作物:山腰是苹果,山顶是莴笋、土豆等。我到访的时候,莴笋成熟了,土豆花也开了,路边的野草莓、野蔷薇迸发着野蛮的生命力。
城里是酷暑,穿短袖都闷热难耐。山上却冷得多,黄昏过后,气温仅有十来度。遇上雷雨天,则更冷。刚下车时,阳光刺得我皮肤像是有上万只蚂蚁在爬,山风却吹得人凉沁沁的。
见到金子时,她正在牧云坡货仓取快递。和上次见面相比,她的脸蛋更加红扑扑、胳膊更紧实有力,证明她确实在认真种地。牧云坡是扶贫机构衍生的一家社会企业,以销售可持续耕作的农产品为主。当地妇女边说笑边打包,动作娴熟。
难得下山一趟,金子采购了一大堆零食,还网购了鸡爪之类当地人不怎么吃的食物。村里人冬天就吃肥腊肉炒酸菜,饮食比较单一。金子不大吃得惯。
抱着几大件东西,她约了一辆出租车。爬升,爬升,再爬升,我们到了她住的那栋贴着黄红相间瓷砖的民宅。她是朝鲜族,进门习惯脱鞋。那间门口摆着一双拖鞋的房间,便是主卧。严格来讲,是卧室加客厅,有猫在两间房子里穿梭。
到了晚上,我们在主卧旁的房间吃饭。这间屋子的一半面积是一个长沙发,用砖和水泥砌成,更洋气的名字叫火箭炕,类似东北的暖炕。金子刚搬来时,徒手盖了这座炕,从买泥巴、粗砂,到抹腻子、安烟筒,全都自力更生。
我们一边吃饭闲聊,一边扔些纸垃圾和细树枝,算是体验了一把火箭炕的暖意。金子没积攒多少柴火,烧火技术又不行(比较浪费柴),她更常用的是电。冬天24小时开着油汀电暖器,做饭基本靠电饭煲、电炒锅、电磁炉……不过,当地积雪经常压断电线。每到停电的危机时刻,她便跑到隔壁的嬢嬢家蹭饭、蹭热水,这似乎已形成条件反射。
2
对一位单身女性来说,找到合适的地方去种地和生活,绝不是拍脑门或碰运气的事。金子花了两三年寻找,她的理想是“地和人要在一起”。不能是上楼后的农村——菜地大多距离集中安置区很远。
从龙泉驿、郫县、新津,再到远一点的都江堰,她都去考察过。2017年前后成都市区扩张迅速,近郊如火如荼搞建设,土地随时可能被占用,租地不大稳定。川西她常去,也在那边开展过项目,最后她找到了大水沟村。
那次,金子是带种药材的朋友去转村,在这里遇到了嬢嬢。嬢嬢比金子的母亲略大几岁,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是金子朋友的同事,这是金子选择来此落脚的重要原因;二女儿在县城当公务员;老三是儿子,忙于生计。
大水沟村不算贫困,也不算闭塞。这块风水宝地曾归土司管,种植过鸦片。解放后,土司制度瓦解,旧有秩序打破。迁居到此的汉人较多,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藏区的氛围。当地人姓氏较杂,意味着没有哪个家族一家独大。村子风气良好,没有拐卖传统。
与嬢嬢聊天后,金子感觉两人气场特别合。下决心之前,她做了充足的准备。首先要了解土地的归属,如果租的地是村民家唯一的土地,那风险就比较大。其次要了解家庭成员的人品、职业、未来打算等。虽与嬢嬢一家认识,但在正式搬上来前,金子还在嬢嬢家住过一段日子,双方有一个磨合过程。
嬢嬢为人简单,难得的是还有边界感。租地的头两年,金子尚需兼顾成都的工作。“上班很痛苦,精神在山里,肉身却在城市,被自己的执念折磨着。”农田几乎处于闲置状态。金子仅辟出一小块地,实验性地种些玉米、豌豆、番茄等。种了也不勤于打理,嬢嬢心急,却没干涉,还担心她白花了租地的钱。
在大水沟村,嬢嬢和她一大家子是金子的保护伞,也是对外的窗口。“地方找得不对,返乡就会失败。”金子租的房子,是嬢嬢弟弟的。嬢嬢娘家兄弟姐妹众多,房子挨得近,像贴身保镖似的罩着金子的家。

3
我曾问金子,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她推荐了《裸猿》。随着人口爆炸,城市空间越来越拥挤,我们周围遍布陌生人。“我们变得不信任陌生人,不遗余力地拉开和他们的差距。”裸猿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伤害,一方面渴望亲密行为,一方面又排斥躲闪,精神上和身体上出现了一系列症状。
疫情前,金子和我讨论过一个问题:另一半X要做什么?半农半X生活,是日本的盐见直纪先生提出的,通俗的说即是兼职农人,收入不全靠种地。
金子曾在吕植老师创办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当志愿者,也在其兄弟机构工作过。2012年,她给自己找了份工作,在天津静海一家农场,管理生物农药出入库,为的是学习可持续耕作技术。一年后,她到了四川雅安,参与灾后重建项目。
在彻底搬到山里种地之前,金子曾做过翻译,但稿费少得可怜,时不时还被拖欠。本来就是为了逃离竞争社会,又何必主动去卷?她也参与过社区堆肥项目组,出差多,项目协调工作也繁杂。总之,她无暇安心照顾自己的地。
金子是2021年1月从成都搬到这里的。她花了三天时间整理行李,将衣服、烤箱、锅碗瓢盆、电饭煲等用得上的东西全部打包,叫了一辆七人座商务车,塞得“一条缝隙都没有”。两只最宝贝的猫,被关进夹在行李中间的笼子里,一头雾水。搬家时恰逢一场大雪。两只猫被她裹在羽绒服里,带到了室外。她捏着它们的小脚,轻轻触碰山野间的积雪。“那么多肥肉,还冷得发抖。”
两只猫从城市迁来,不知野生世界的残酷。有一次,大猫偷偷从门缝里溜了出去,纵身奔跑,却掉进了粪坑。金子焦急地找了半天,惊动了周围的村民。耗时许久,才找到一身屎尿的大猫。每次回忆这段经历,金子满是歉疚。她几乎用光了所有洗发水和沐浴液,才勉强搓干净她的大宝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猫对自己的体味始终嫌弃,不停舔来舔去。惊吓过度的金子,给卧室门安上了落地防盗纱窗,防止两个小家伙再次误闯野生世界。
这次行程,我带了一本单读的杂志书《多谈谈问题》,打算送给金子。抵达的第一晚,我窝在五斤重的被子里先睹为快。耳边传来鸭子“嘎嘎嘎”的叫声,像鬼畜一般。我正在读吕植老师《人应当有取舍,保护环境应当讲公平》这篇时,落地灯突然灭了。从窗帘的缝隙里,我望见刀锋似的闪电,仿佛要把房子劈成两半。
金子曾说,她刚搬来收拾房屋时,趴着擦地板,发现有很多裂缝。顺着墙角往上看,屋顶也有裂痕。原来,村里的施工队很难做到标准化,而房子又建在斜坡上,随着时间推移,地基下沉,地砖受力挤压,就会渐渐出现缝隙。马尔康地震那次,金子在地里,她感到大地在晃动,赶紧跑回家,一手抱一只猫冲了出来。邻居们倒是习以为常,还曾露天过过夜。金子待在厚实却没钢筋承重的房子里,心情跟高原的云朵似的,阴晴不定。
闪电之后是暴雨,我有些担忧,想给金子发条消息,手机却没信号。我只得钻进被子,蒙头睡去。翌日清早,电还没来。金子告知,这里经常停电。她还故作神秘地问,晚上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没?原来,昨晚听到的鸭子叫是农民催赶野猪放的电子狗叫声,经风的加工走样成了鬼哭狼嚎。

4
我去过不少所谓“打工换宿”的农场,不是干农活便是做饭,从早忙到晚。金子家却是个例外。她不爱派活,本身也不是以务农为生。她开玩笑称,这里是“发呆民宿”。
在金子家我没干什么农活,仅拔了两次草。这里的作物出奇的壮,除光照充分之外,也与水多有关。车前草是我在别的地方见过的两三倍大,长在地里实在碍事。车前草被称为“百草之母”,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考据得出“几乎所有古老的药方中都有它的身影”。但在金子的地里,它是无用的玩意儿。我奉命行事,尽数拔掉。还有一种植物,金子称“大根”。我上网查了一下,貌似是牛蒡,比其他杂草高出一截,绿紫色的叶片比橄榄球面积还大。
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一书中将杂草形容为“植物世界里的贫苦农民”、“无归属的少数派”、“边界的打破者”。说起来,我们和杂草处境相当,胜似同类:我是主动辞职的独立写作者,金子是背着母亲偷偷种地的新农人。继续留着杂草,会影响唯一经济作物豌豆的成长;除掉它们,我又心怀歉意。好在金子种地采用的是懒人法,割掉的杂草就地覆盖,保水之余还能沤肥还田,杂草也算没白牺牲。
除草就像给大地挠痒痒,其实,我们中了杂草的诡计。有的杂草仅凭碎根,便能起死回生;有的杂草潜伏在我们的鞋底,被散播到原本无法抵达的地方。一场暴雨过后,它们又会露头猛长,真是防不胜防。杂草仿佛在嘲笑我,“你来之前我们就在;你在之时我们整日为伴;你不在了,我们继续生活。”当然,对于跟金子一样的农人来说,第一要考量的还是生存,只有我这种闲人才有时间玩味这些形而上的问题。
一座普通民居里住着一个女人,在乡下本就是容易让人嚼舌根的事。独居女人身上可以贴一大堆标签——大龄、未婚、不务正业。我不愿她成为任何主义或时代情绪的代名词,非要归类的话,不如称为“杂草系女人”。
她就是她,是坐在火箭炕上,担忧着冬天上哪儿砍柴火的女子;也是割舍不下城市的便利,时不时要下山一趟,跑回成都看《阿凡达》,二刷三刷巨幕影院的女子。

5
屋外响起铁皮被棒槌猛击的声音。我放下手中的书,跑出去看。一个男人推开铁门,径直走到小院里。他说要找金老板买烟,我说,金子去地里干活了。
嬢嬢的小卖铺开了二十多年,金子是她忠实的顾客,买鸡蛋、可乐还有奶茶等等。嬢嬢出门常忘带钥匙,她就拿了一把钥匙放在金子这儿。如果嬢嬢去县城帮女儿做饭、带娃,金子就替她看铺子。顾客都知道,嬢嬢不在,就来金子家敲门。嬢嬢即使出趟远门,销售额依然不错,金子功不可没。
我没小卖部的钥匙,也搞不清楚价格,只能去找金子。我跑进厨房,趴在窗口,冲田里喊着她的名字。我看不见她,全凭感觉,喊声就像撒出去的种子一样,随风飘去。
金子“唉”了几声,说马上回来。一进门,她不忘揶揄了句,“我不是老板,是店小妹。”
那男人的举动令我有点不舒服,但我没当场表露。等到晚上和金子吃饭,我才跟她讨论起私闯家门的男人。我遇到过几个本地女性顾客,都是过门而不入,等在外面。一位年轻的母亲走了很长一段山路来给孩子买药,哪怕敲门声十分焦急,她还是站在门外等候。为什么这个男人没一点边界感?
我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次外出。那天牧云坡的工作人员邀请我们去隔壁村寨。金子叫的还是那辆熟悉的出租车。在大山里生活,又是独身女士,安全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行车途中,看见一位老头独自沿着马路往下走。司机与他寒暄了几句,得知老汉要去山脚下的营业厅充话费,顺道便载上了他。两人聊天时,老汉口音较重,我只听得懂大概。老汉当了一辈子光棍,过了62岁还没娶媳妇。我和金子挑了挑眉。她接收到我的信号。我老听她讲,农村的单身汉越来越多了。
司机劝老汉搬到镇上的养老院住,免得身体出事来不及送医。老汉却惦记着家里的玫瑰园,说再过十年才考虑养老。当地办了一家精油厂,附近的农民种玫瑰花,卖给厂里提取芳香物质。老汉打算等到干不动了,再搬去兄弟家住或请个保姆。司机建议他,还是去养老院合适。“一年挣三万,留一万五养老,反正不要在大水沟待了。”但司机也感叹,“在养老院住也有弊端。昨天还一起打牌的人,今天就死了。心理压力大。”对许多单身老汉而言,养老院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
6
金子出山,不坐摩的,便是搭顺风车,偶尔凭双腿,从牛走的小道,也即过去的土路上下。有些路段,弯弯绕绕从别家门前过,没点胆子真不敢冒昧打扰。
金子曾带我走了十多分钟,路过一座羊舍。不远处有两个村民正在缝补大雨后倾轧的山体。山下的路,泥巴越来越粘脚。我俩并排走过挖掘机,身后传来轮胎“噗噗”声。金子停下脚步,转身看了看。一辆装满莴笋的大卡车笨重地朝我们开来。金子挥了挥手。卡车吐完两口气,稳稳停下来。卡车的挡风玻璃上装饰着经幡,车门印着暗金色的手持转经筒。
司机姓刘,跑运输,和金子住一个村。除司机外,车里还有一个男子。没办法,只好三个人挤在副驾驶位上。我猜,要不是见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金子宁愿走两小时山路,也不会搭上这辆“男士专座”。
车子开到半山腰,对面驶来一辆黑色商务轿车。
“好熟悉。”金子说。“那是老板,老板的车。”刘师傅说得下去一趟。他停下车,从烟盒里抽出两支烟,躬着身子跟老板打招呼。这位老板在当地租了大片土地,雇佣农民种莴笋、土豆、玫瑰花等。疫情三年亏了不少,只等今年收点本回来。
车子重新启动后,刘师傅对金子说,“你可以在我这里拿货啊。我也收豌豆。”金子没搭话,他又说:“苹果,苹果一定卖得好。”当地产的苹果一向有名。从熊猫大道拐入小金县城,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颗巨大的人造红苹果,宣示着当地的主打产业。
我了解的金子,是不愿跟人嘻嘻哈哈讲笑的。金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解释,自己种的是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的豌豆,不适合走大宗商品交易。
“你跟老板说,做他小三。”刘师傅嬉笑着话锋一转。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要不是在车上,早翻脸走人了。
“我只卖货,不卖身。”金子怼了回去。我猜,她心里早已经扇那男人几个响亮的巴掌了。车上另一个男士稍微有些分寸感,打了个哈哈,转移了话题。
车子终于抵达主路旁的加油站,我和金子逃一般的跳下车,嘴上还说了声“谢谢”。在等待去县城的面包车时,我对金子说,生活在这里真不容易。金子平时不爱跟村里的男人来往,原因就是,男人擅长试探,不立即怼回去的话,他们会得寸进尺,认为女人在撒娇。在村子里,金子一般分不出谁是光棍,所有男性都是她警惕的对象。
7
有一天金子在地里忙着,突然来了辆警车。四个人下来,其中一位女警招呼了她。
金子正卖力干活,被打断后,有些不耐烦。
“你是金XX吗?”
金子说,对呀。
“为什么没登记,没有办常驻证明?”
金子说,跟村书记打过招呼了,“我肯定要拜山头。”
“你住哪里?”
金子指了指高处的房子。即使是偏远山区的警察,还是相当专业。三个人围着金子,女警还跟她套近乎,降低她的防范意识。另一个把房间仔仔细细转了一遍,包括卫生间。
两个男警查看了金子的证件,好奇她来这里做什么。“种地啊。”金子带他们转了一圈菜地,介绍了种植方式和正在生长的农作物。警察临走时,叮嘱她有事一定要打110,“会立即出警”。
原来四姑娘山附近的镇子,有人租房制毒被捣毁了。那段时间,所有常驻的外来人口全部被排查了一遍。
警察上门没两天,村里又来人了,名义上是探望,其实是了解情况。每个村子有一套自行的规则。平白无故进村的人,村民会十分警惕。金子搬进村子后,光是社区服务中心的人就来过好多次。有一次他们上门统计老年人常规疾病,把金子归为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好丢脸啊”。她还被迫站在大门口拍了张照片,以作证明。
村里知道来访者的身份,安全才有保障。以前金子来此做项目,先要跟县里报备,他们会派一个对接人,级别至少是村书记。如今是独自上山讨生活,金子有嬢嬢一家“照顾”,又跟村书记打过招呼,还算有个保障。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不少开发商蜂拥至农村,让许多农民看到了商机。刚搬上去那阵子,村民误以为金子是大老板,想把村子的发展重任寄托在她身上。他们爱问,金老板缺不缺人手,需不需要招工?两年过去,见金子确实没啥动静,又认定她是来这里“搞科研”的,总之,没一个相信她来“生活”。
一些村民希望金子能为村子做些贡献,当她做不到或只为自己而做,他们会心理失衡,觉得没把利益分给村子。“毕竟是外来户,没给村子创收,还占用村里的资源。”

8
在盒马超市,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的蔬菜上有油墨打印的“产地:小金”字样。我待的那些天,刚好遇到莴笋丰收期,大卡车每天往成都运送头一晚采摘的新鲜莴笋。
当地的规矩是,一个生产队负责采收一片区域,每个队有一个换工小组,十几二十人。哪家农忙,大伙就一起上,种土豆、油菜、莴笋等等。但金子却还在犹豫要不要加入。她担心被卷入村子的日常劳作,比一个人种地更辛苦,不出工都不行。
金子曾参与过修缮水池的集体劳动,也曾连着三天,和村里的姐妹一起上山捡松果当柴烧。姐妹们见她的麻袋没装满,还帮着往里塞。她心里想,这样算是被村子半接纳了吧?
山就这么大,各有各地盘,捡柴火考验友情,采菌子更甚。邻居大姐进山采松茸,金子想跟着去,就算不采松茸,采些便宜的菌子也好。但她又觉得有些越界,最终按捺住了一颗冒昧的心,拜托大姐帮忙采摘,再按收购价买下。
金子希望,她与村民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忙到要死要活时,金子会想,“种得这么累,菜应该卖贵一点。”她试着种了三个品种:云南的薄皮豌豆、老品种菜豌豆和北方人喜欢的荷兰豆。她发现,成都人更接受菜豌豆。嬢嬢说,这种豌豆至少要卖三块钱一斤。金子说,她卖20多块。
不管怎样,卖菜并不挣钱。金子种了三亩地,2022年销售额统共2000多块,还不够支付一年地租。她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活出一条路。“我是菜鸟,还在学习。”
想起我们聊过的话题:另一半X要做什么?我认为应该倒过来,即“半X半农”更符合现实。X的占比肯定要大过农的部分,才能在当今社会维持基本的平衡。农业离不开土地,所以,半农生活注定被土地束缚,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2018年,金子初次萌生了返乡生活的念头。到现在,想必她心里已盘算清楚,想要过体面的生活,仅靠种地是不可能实现的。
——完——
作者草西,非虚构写作者,记录生活日常里的小人物和时代故事。
本文图片摄影: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