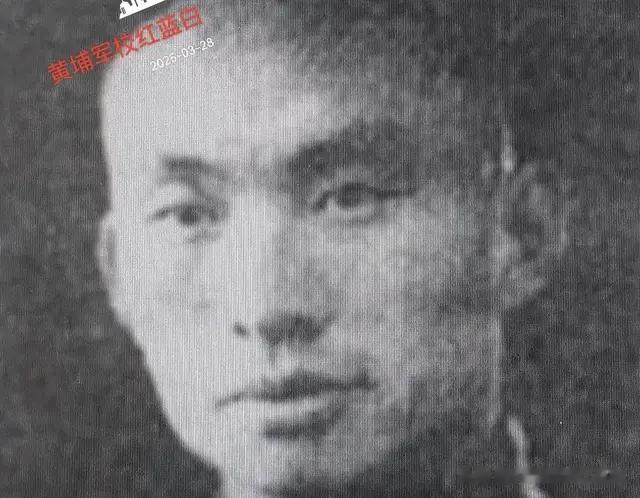文|熊玲历史
编辑|熊玲历史
养心殿的烛光在康熙眼底跳动,他正摩挲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奏折:左首明珠督造的台湾府城图墨迹未干,右首弹劾其贪墨百万两的罪状血迹犹新。这位帝王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雪夜,明珠顶着满头霜花呈上《平三藩策》时,袖口还打着粗麻补丁。

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还凝着晨露,索额图已被褫夺顶戴押往宗人府。经过乾清宫时,他忽然放声大笑:"纳兰明珠那厮贪的雪花银,怕是能铺满太和殿广场!"这话顺着穿堂风飘进御书房,康熙的朱笔在明珠请罪折上悬停良久,最终画了个殷红的圈——不是斩立决的勾决符号,而是个圆满的句点。

台湾鹿耳门的炮火映红海面时,明珠正躺在京郊别院的湘妃榻上把玩东珠。施琅的捷报与弹劾他强占民田的奏章同时送达,康熙却将后者塞进了密折匣最底层。直到某日早朝,御史当庭哭诉明珠府邸堪比亲王府制,少年天子才恍然惊觉,当年那个在兵部门口啃冷馒头的寒门侍郎,如今已养出了四十房妻妾。

尼布楚条约谈判桌上,明珠的翡翠扳指与沙俄使臣的蓝宝石戒指相撞出清脆声响。这位礼部尚书操着生硬的蒙古语,将条约边界线向北推了三百里。当使团副使悄悄塞来一箱金沙时,他却转手熔铸成八十尊金佛,供奉在康熙亲征噶尔丹途经的寺庙里。此事直到三百年后,承德外八庙的喇嘛仍会向游人讲述:"明珠大人送佛那日,袈裟下穿的是打补丁的官服。"

索额图在诏狱受审时,刑具碰撞声惊飞了檐下的春燕。他至死不明白,为何自己为太子谋划的每步棋都成了催命符。直到断气前听见狱卒闲聊,说昨日明珠进宫面圣,竟穿着二十年前的旧朝服,袖口的龙纹补子都磨成了素绢。这位曾权倾朝野的国丈突然呕出血来——他终其一生学不会明珠的生存智慧:贪财好货的权臣,永远比胸怀大志的能吏让皇帝安心。

畅春园的荷花开到第七茬时,明珠的棺椁正缓缓出城。康熙特旨允其陪葬帝陵三十里外,墓碑上"辅弼良臣"四字在夕阳下泛着诡异的光泽。送葬队伍中有个布衣老者,将一方沾满墨迹的旧奏折投入火盆,纸灰飞舞间隐约可见"台湾赋税加倍"的批红——那是康熙默许明珠中饱私囊的价码。

南书房暗格里,至今锁着幅未完成的帝王画像:康熙执朱笔点向舆图上的雅克萨,身后阴影里跪着两个模糊人影。画师临终前告诉徒弟,右边那个捧血书的是索额图,左边举金印的正是明珠。当御前太监来取画时,只看见满地碎纸,仿佛这对宿敌终究在丹青里同归于尽。

景山的老柏树记得,康熙晚年常对着明珠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怔忡出神。某日暴雨击碎窗纸,湿透的书页间突然飘出张地契,赫然是明珠强占的苏州百亩良田。老皇帝颤抖着将地契凑近烛火,却在焚毁瞬间瞥见背面小字:"此田岁入尽充密折线人费",火光中浮现的,是三十年来无数深夜递进养心殿的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