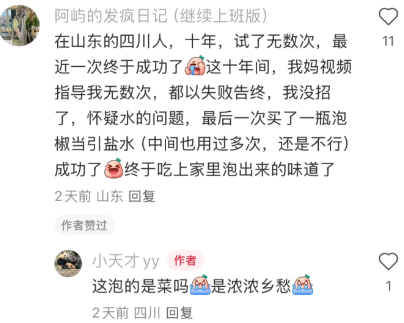我家楼下有家川菜馆,我常去吃,都跟老板娘混熟了。馆子开在老居民楼的拐角,招牌是块掉漆的木板,写着“陈记川菜”。老板娘叫陈兰,四川达州人,说话总带着股辣椒似的冲劲,手上却巧得很,一道鱼香肉丝能把酸甜咸辣配得恰到好处。 老居民楼的拐角,总亮着盏灯。 是“陈记川菜”,招牌是块掉漆的木板,红漆字被雨水泡得发乌,风一吹,“吱呀”响,像句没说完的话。 老板娘叫陈兰,四川达州人,说话嗓门亮得像敲锣,带着股子辣椒似的冲劲,手上却巧——一把菜刀在她手里能跳舞,切出来的土豆丝细得能穿针,鱼香肉丝的酸甜咸辣,配得像早就量好了尺寸。 她总系着条蓝布围裙,胸前沾着星星点点的豆瓣酱渍,像谁不小心撒上去的颜料,洗不掉,也懒得洗。 第一次推门进去是去年冬天,加班到九点,胃里空得发慌,整条街的店都暗着,就这家拐角的馆子亮着盏暖黄的灯,玻璃上蒙着层白雾,隐约能看见灶台后一个穿花围裙的身影在颠勺,锅铲碰撞铁锅的“哐当”声混着辣椒的香气飘出来,勾得人腿都迈不动。 “吃啥?”她头也没抬,正往锅里倒酱油,手腕一抖,弧线漂亮得很。 “鱼香肉丝,少辣。” “晓得!”她应得脆,切菜声“笃笃笃”响成一片,胡萝卜丝、土豆丝、肉丝在案板上排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小兵。 菜端上来时,我眼睛都亮了——肉丝滑嫩,笋丝脆生,酸甜汁裹着每一根食材,筷子根本停不下来,连扒拉了两碗米饭,撑得直打嗝,她在柜台后瞅着笑:“饿狠了?锅里还有粥,免费。” 熟了之后,她就成了“陈姐”。 我不吃葱姜,她每次切配菜都把葱姜另外放个小碗,上菜前用筷子尖挑得干干净净,盘子边堆着一小撮,像两座迷你小山,还不忘瞪我一眼:“事多,葱姜提香都不懂。” 有次感冒,咳嗽得撕心裂肺,刚坐下,她就从后厨端来碗姜丝可乐,糖放得足,姜丝切得细细的,碗底垫着块布,怕烫着我:“喝,发点汗就好了,别传染给我客人。”语气冲得很,我却喝得心里暖烘烘的。 我问她:“陈姐,你咋啥都会?”她擦着桌子笑,手里抹布甩得跟风车似的:“出门在外,多会点能少受点罪呗,总不能啥都指望别人。” 真正让我记到现在的,是去年秋天那个晚上。 我失恋了,整个人蔫得像被霜打了的菜,晚上十点多晃到馆子门口,灯还亮着,她正在收摊子,塑料凳摞得老高,看见我,愣了一下:“今天没加班?” “嗯。”我声音闷得像堵了团棉花。 她没多问,转身进了厨房:“等着,给你炒个鱼香肉丝。” 菜端上来,红亮亮的,我扒拉了两口,没胃口,筷子戳着米饭发呆。她坐在对面,嗑着瓜子看我,瓜子壳吐得准准的,都进了脚边的小筐:“咋了?菜不合胃口?我尝着挺香啊。” “不是。”我摇摇头,眼圈有点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把我的盘子拉过去,拿筷子夹了块肉丝,尝了尝,皱眉:“哦,糖放少了。”然后起身又回了厨房,两分钟后端回来,“再尝尝,这次甜。” 我吃了一口,眼泪“啪嗒”掉盘子里——真的比平时甜好多,甜得有点发腻,却奇异地压下了心里那股酸。 她递过纸巾,没说话,过了会儿才嘟囔:“甜的压得住苦,晓不晓得?多大点事,哭啥,跟个娃娃似的。” 那天晚上,她陪我坐了很久,听我絮絮叨叨说了半宿废话,从怎么认识到怎么分开,她没插嘴,就偶尔“嗯”一声,或者递颗瓜子,直到我情绪好点了,她才赶我:“行了,回去睡觉,明天还得上班呢,迟到扣钱我可不管。” 我走到门口,她突然喊:“喂!” 我回头。 她指了指我:“明天早点来,给你留了红糖馒头,热乎的。” 以前总觉得她说话冲,像炮仗,一点就响,后来才明白,四川人的热情就那样——像他们顿顿不离的小米辣,看着红通通的吓人,吃到嘴里,辣得过瘾,咽下去,胃里暖烘烘的。她围裙上的豆瓣酱渍永远洗不掉,就像这家馆子的招牌,掉漆了也照样挂着;她嗓门永远那么大,却能在我咳嗽时记得煮姜丝可乐,在我难过时多放一勺糖——那些她没说出口的关心,藏在锅碗瓢盆的声响里,藏在酸甜咸辣的滋味里,藏在每一句“事多”“赶紧走”的唠叨里。 你说人为什么会对一家小店有感情? 可能不是因为菜多好吃,是因为那个掌勺的人,把你的喜好记在了心里,把你的狼狈看在了眼里,却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给你添了一勺甜,让你知道,就算日子再难,也总有个地方亮着灯,等着给你炒盘热乎菜。 现在我还是常去,每次路过老居民楼拐角,看见那块掉漆的木板招牌在风里“吱呀”响,心里就踏实。 陈姐还是老样子,说话像辣椒,手巧得很,围裙上沾着豆瓣酱渍,灶台上温着老鹰茶,看见我就喊:“今天鱼香肉丝要甜的还是咸的?” 我笑着回:“甜的!多放糖!” 她瞪我一眼,手却诚实地往糖罐那边伸——日子嘛,不就是这样,有点烟火气,有点人情味,像那道鱼香肉丝,酸甜咸辣都有,才够味儿;而那些藏在平凡里的温暖,就像陈姐多放的那勺糖,不显眼,却能让苦日子,也变得甜滋滋的。
小猫高抬腿像极了美味的大鸡腿
【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