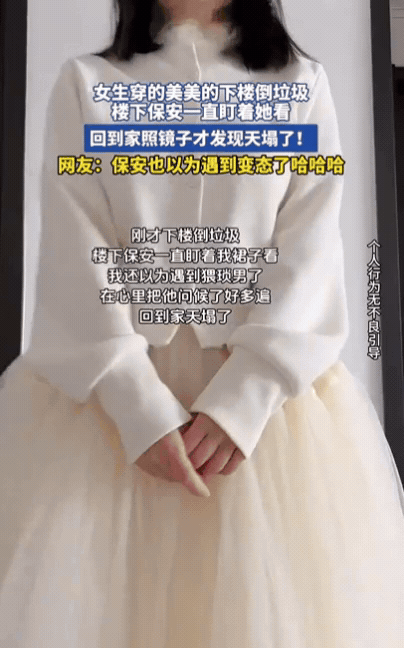表舅50岁那年,因为不愿在老家种地,于是去了城市做保安。后来认识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两人就在外面租房子同居了。表舅第一次带那个女人回老家时,是个清明。他穿着件不合身的西装,裤脚卷着边,女人穿条碎花连衣裙,手里拎着两盒包装精致的点心,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显得有些局促。 我表舅五十岁那年把锄头扔进灶膛,背着蛇皮袋去了城里。在写字楼地下车库当保安的第三年,他领回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安徽女人,他们在城中村共用一个煤气罐,直到那年清明。 我去村口接他们时,老槐树正往下掉白花。表舅穿的西装是物业发的工装,肩膀撑得发亮,像是偷穿了别人的衣服,裤脚卷两道边,露出沾着泥点的白袜子。女人穿条碎花连衣裙,裙摆扫过带泥的鞋帮,手里那两盒杏花楼点心在灰扑扑的村口晃得人眼晕——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在长途汽车站便利店买的,收银小姐用红丝带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 「这是……」表舅的喉结动了动,没说出「对象」两个字。女人把点心往我怀里塞,手指冰凉,指甲盖边缘沾着点蓝墨水,像刚从工厂流水线下来。我们站在树影里,能听见邻居家的狗在叫,还有堂屋里传来的搓麻将声,谁都没敢先动。 谁能想到呢?这个在玉米地里干了半辈子的男人,会在知天命的年纪,穿着借来的西装,带着城里认识的女人,站在祖坟前头手足无措。女人后来偷偷跟我说,表舅在城里总吃剩饭,保安亭冰箱里冻着的包子能放半个月,她就是看不得他啃冷馒头才跟他回的家。 村里人背后说她图钱,可表舅每月工资大半寄回乡下还盖房的债;说她不安分,她却在出租屋里给表舅缝补磨破的袜子。那些细碎的针脚,比任何情话都实在。 那天午饭时,表舅喝多了,突然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我这辈子没出息,可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委屈。」女人没说话,只是默默把他碗里的肥肉夹到自己盘子里。阳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她碎花裙子的褶皱里,像撒了一把金粉。 现在他们还在城里租着房,表舅的西装依然不合身,但裤脚再也没卷过边。每次通电话,女人总会抢着说:「你表舅今天又省下午饭钱给我买了串糖葫芦。」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总有地铁进站的呼啸声,混着表舅憨厚的笑声。 或许生活本就没那么多道理可讲,就像老槐树下那两盒最终被孩子们分食的点心,包装再精致,不如实实在在的甜。我们总在算计得失,却忘了有些人拼尽全力,不过是想给身边人一个像样的春天——哪怕这个春天,来得晚了些,还带着点裤脚卷边的窘迫。
表舅50岁那年,因为不愿在老家种地,于是去了城市做保安。后来认识了一个比他小十几
凯语乐天派
2025-12-16 19:30:09
0
阅读: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