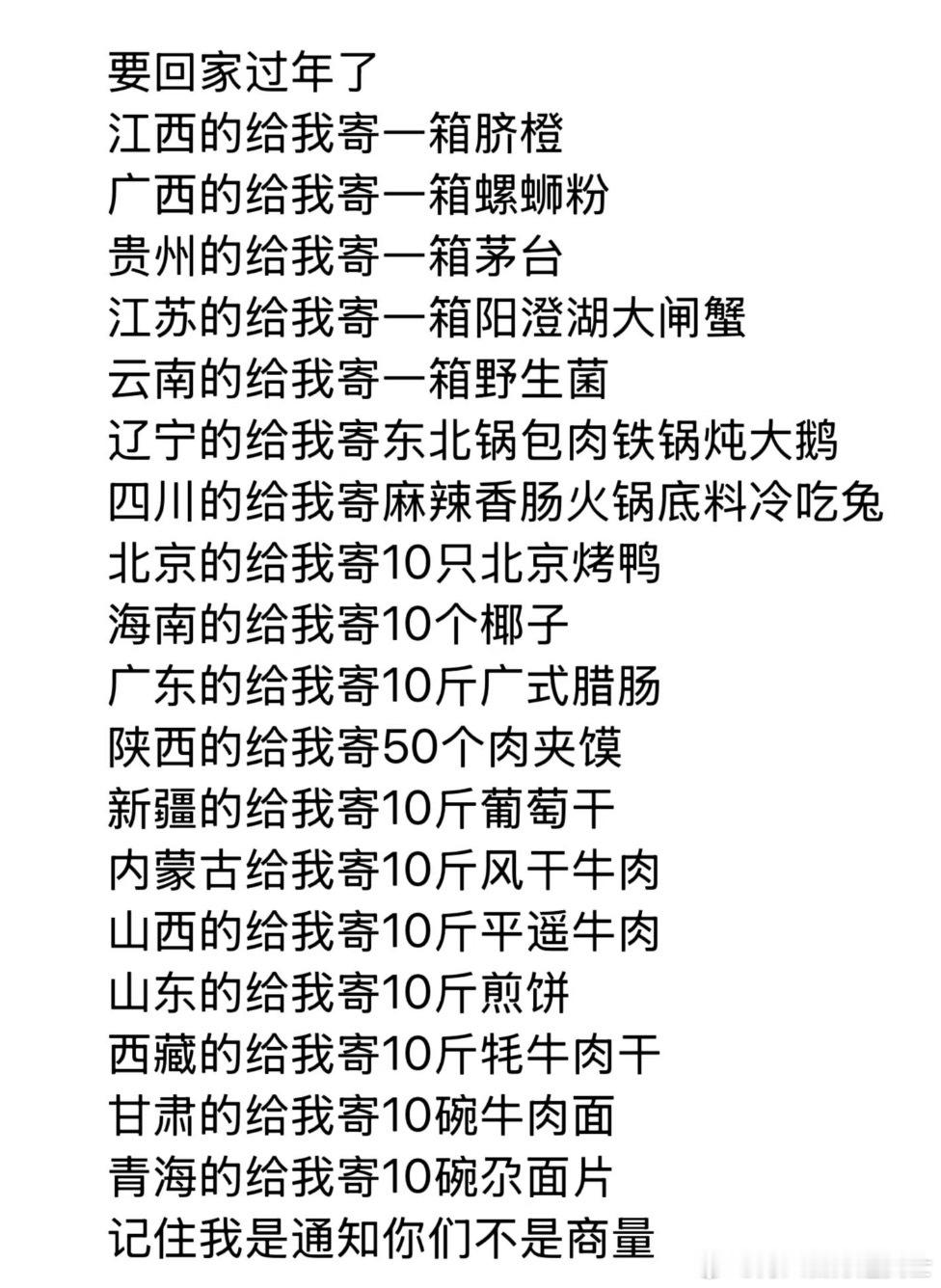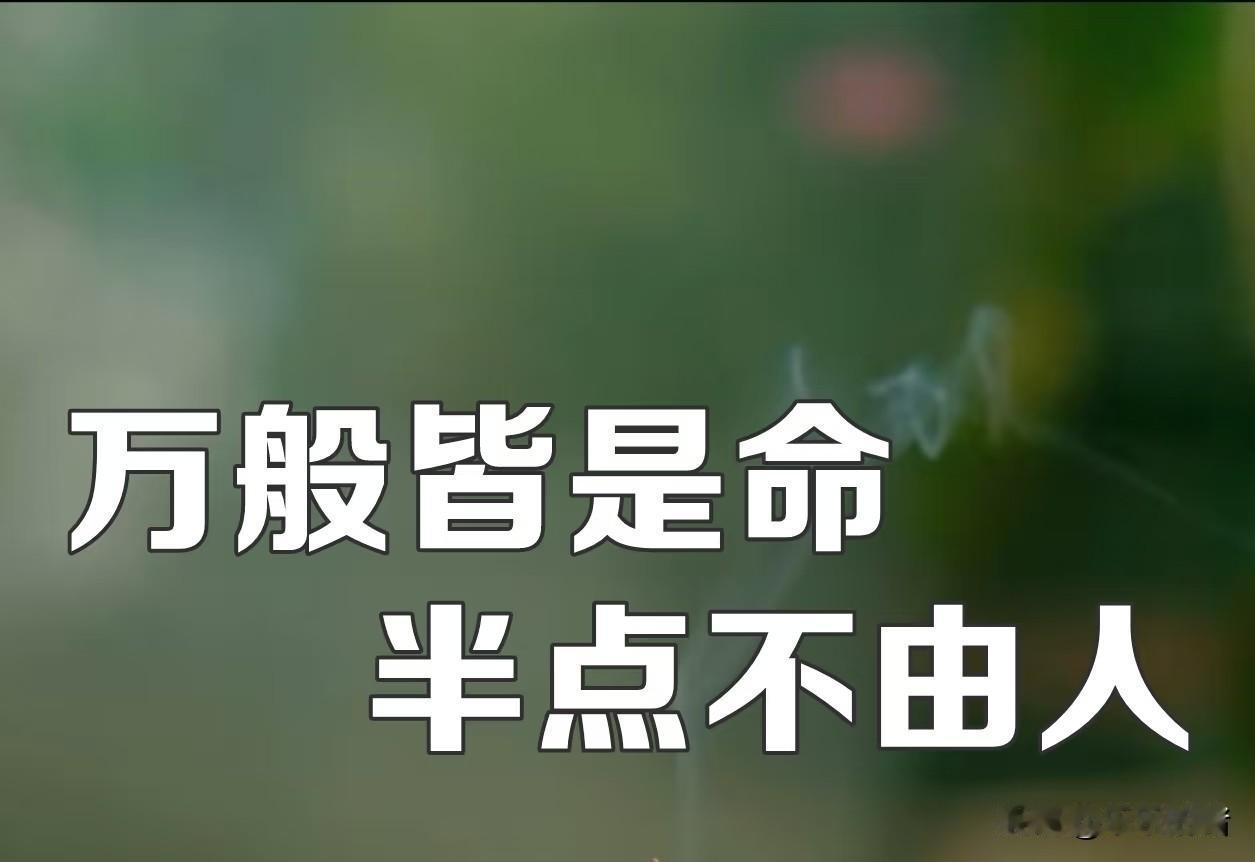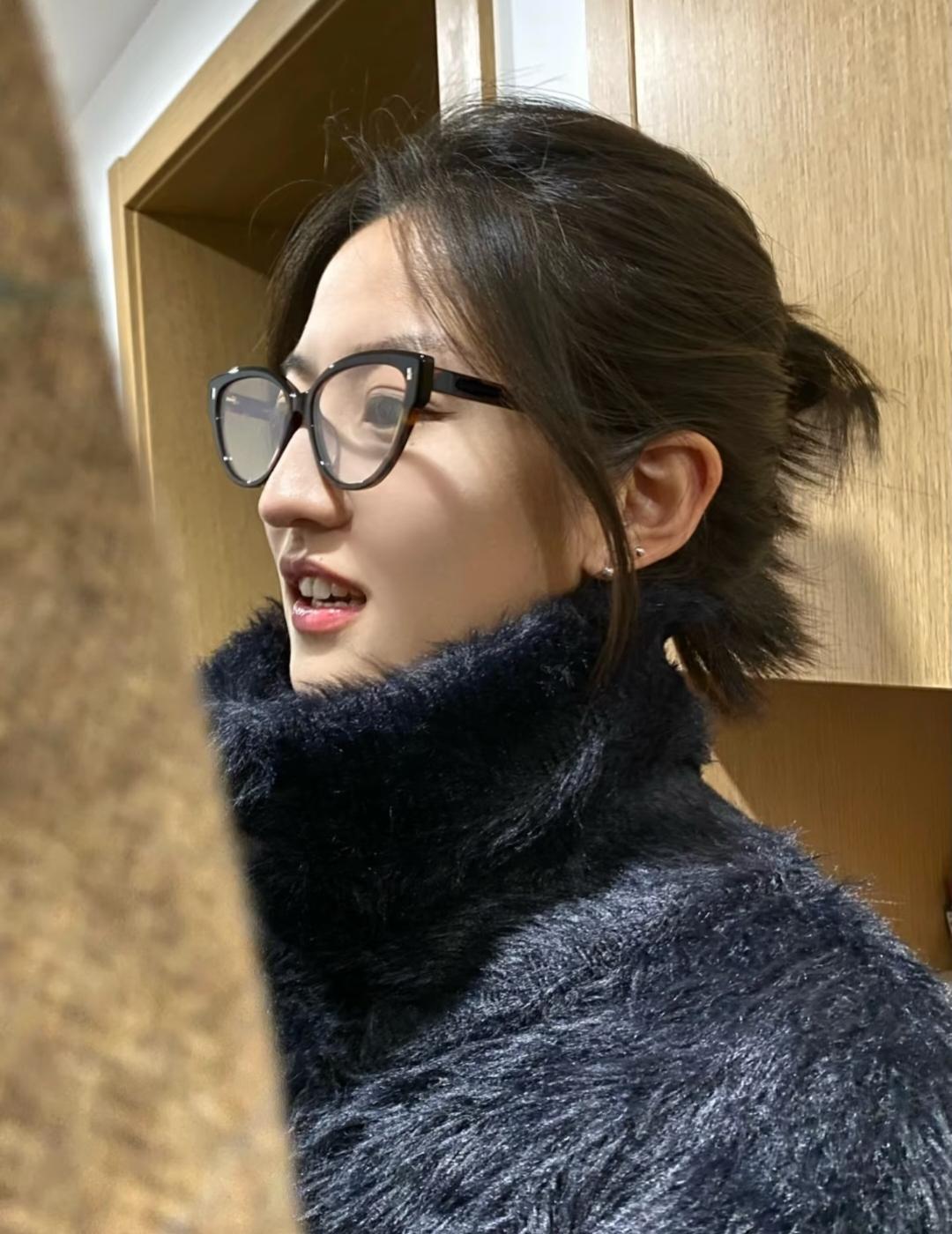前天母亲电话说,堂哥明天带新媳妇回家,正好赶上三婶家杀年猪,让我们回去帮忙。 挂了电话我心里直打鼓,堂哥在深圳开公司多年,上次回来还是三年前,听说新媳妇是城里姑娘,打扮时髦得很,能适应我们这乡下的杀猪场面吗?我赶紧给孩子请假,又跟公司调了休,心里盘算着得提前去帮三婶多准备些“体面”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出发,车刚拐进村子,就看见三婶家门口围了不少人。邻居张大爷蹲在墙根,手里捏着旱烟袋,跟旁边人念叨:“听说那城里媳妇金贵着呢,能受得了咱这杀猪的闹腾?”我刚停好车,就见堂哥穿着件熨烫平整的白衬衫,身边站着个穿米色风衣的姑娘,正是堂嫂。她手里拎着个精致的帆布包,看到我们,露出怯生生的笑,小声问堂哥:“老公,他们……他们围着猪圈干嘛?” 三婶从院里迎出来,拉着堂嫂的手不放:“哎呀我的好媳妇,快进屋坐,外面风大。”堂嫂却没动,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猪圈方向,问:“三婶,他们要杀猪吗?我能看看吗?”这下轮到三婶愣住了。 杀猪师傅已经到了,几个壮汉正把猪往案板上按,猪的嚎叫震得人耳朵疼。堂嫂非但没躲,反而凑到厨房门口,看我和三婶择菜。“嫂子,这萝卜得切滚刀块才入味吧?”她突然开口,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把菜刀,切萝卜的动作竟比我还麻利。我惊讶地看着她:“你会做饭?”她笑了笑:“我爸以前是厨师,耳濡目染罢了。” 堂哥站在院子里,看着媳妇系上围裙帮着剁肉馅,又看着我老公和邻居们一起抬猪肉,眉头渐渐舒展。突然“哐当”一声,装猪血的盆被撞翻,血溅了堂哥一裤腿。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又猛地停住,蹲下身就去收拾。“我来吧!”他对要帮忙的邻居摆摆手,笨拙地用抹布擦拭,白衬衫上沾了点点血迹,却笑得像个孩子。 中午开席,堂嫂端着一大盆杀猪菜出来,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却中气十足地喊:“大家快趁热吃,我加了点陈皮,解腻!”堂哥则被几个叔伯拉着喝酒,他酒量不好,几杯下肚脸通红,却还是仰头喝完,嘴里念叨:“我小时候……我爸也带我看过杀年猪,他说这叫‘有肉大家吃,有事大家帮’。” 回家的路上,孩子趴在后座睡着了,老公握着我的手说:“你看,城里人也不全是我们想的那样。”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田埂,心里暖烘烘的。乡情这东西,从来不是靠身份区分的,就像堂嫂切萝卜的刀工,堂哥擦猪血的笨拙,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真诚,比任何客套话都有力量。你说,是不是我们总把“城里”和“乡下”分得太清楚,才错过了那些本该热乎乎的人情味儿?
要过年回家了给我寄点特产:
【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