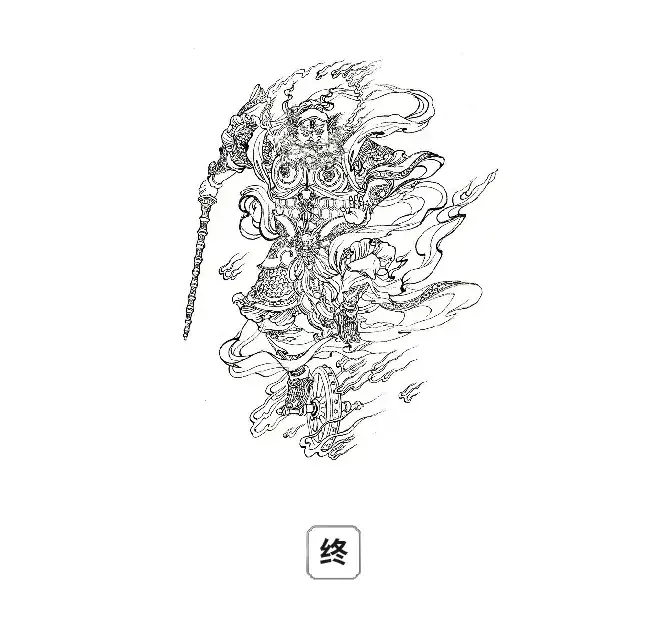本文作者:九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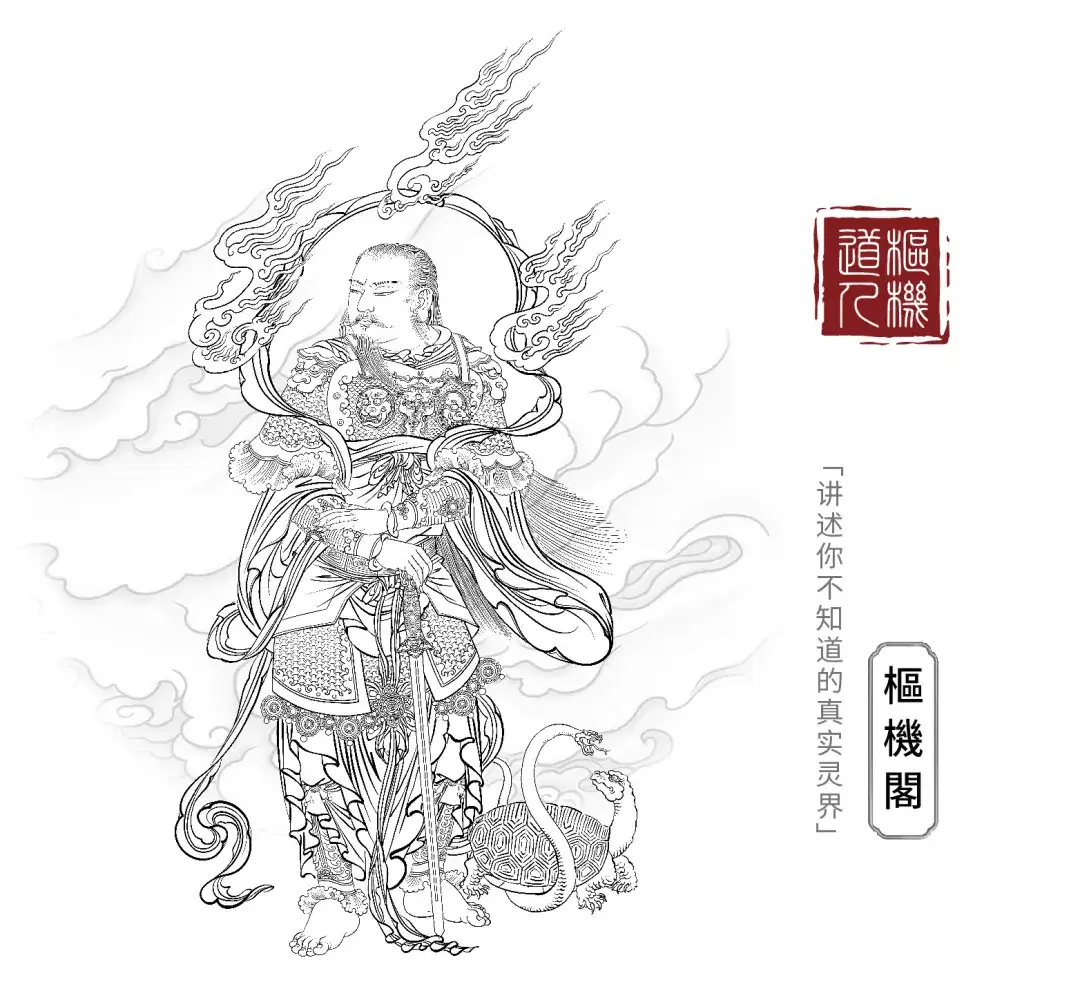

这是抬起笔又放下的第十一次,还是艰难的坐起,克服一下情绪,尝试写这一点文字。写作就像人生,特意要怎样的时候,好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曲罢终了,记不住自己究竟写些什么,付之一炬吧,还有点可惜,留着发表,换几声喝彩,也别无他用。恰似人生,生来白纸,随笔勾勒,看似锦绣,到头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到终章时,追忆珍惜,总想原来朴素的几笔如能再慢一点,再走心一点,再珍惜当时的心境,活在当下,或许就是人生的意义。
所以这一篇文章,也像画在人生画卷的最简单一笔,我想可能这篇文章写出来,会对人有什么启发?我想或者这样特殊的日子,是不是以写信的方式去传达?还是说我想写一首律诗,只做自己敝帚自珍?最后还是决定随性的写个随笔,我会请城隍庙的使者念给她听;也会发布出来,如有缘人有类似心境,自然懂大梦一场,究竟心安何处;也会自己留念,将来有一天在我死了的时候,儿孙痛哭流涕时,拿来也可做止痛灵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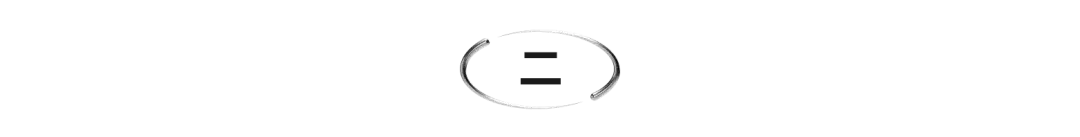
昨天我和姜心澄一起去了水族馆,看见一只鱼,它的嘴微微突出,生出一丝丝岁月的皱纹,游的速度很慢。
“它好像我姥姥啊”
我笑着讲,我的姥姥因为脑部疾病,在她人生最后的几年,下唇是无法严丝合缝的闭合,像这只鱼一样。
姜心澄打了我了一下:“哪里有这么说自己姥姥的。”
我哈哈的笑着说:“可是就真的很像啊。”
说着说着,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趴在旁边的栏杆,深埋着头,以免大庭广众之下,有碍观瞻。所幸头顶有一个巨大的过山车,掩饰着我的尴尬。好像在路人的眼里,这只是一个玩山车玩到身体不适的可怜人,在调整身体的不适。
此时头顶一车快乐的游客呼啸而过,在歇斯底里呼喊着他们的兴奋和快乐,这与我的悲伤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但我没有嫉妒他们,小时候和姥姥一起生活的岁月也是同样的快乐,若不经快乐,苦又从何来?

去年的今天,我最亲爱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实在不好意思说离开了我,因为人跑去香港,基本没怎么陪老人,实在汗颜又惭愧。
我想起一些趣事,我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在姥姥家过年,姥姥是老萨满师傅了。每到过年点香,家里总是烟雾缭绕,烟熏火燎,也就十点来钟,姥姥就手拿着一大把香去箱柜那上香磕头。我数了数里面,前排的碗不算,后排的碗就有九个,那碗都是瓷做的,每个碗都会插香。
我姥在前面磕,我就等她磕完了,咣咣的去跟着磕,磕完了大人就在笑我,问我你为什么磕头啊?我回:“那不是给老祖宗磕头吗?”我之前听大人们说是供老祖宗,具体的我也不懂啊,大人哈哈一笑,抱着我开始吃饭。
听我妈和我姨说,我姥五十来岁的时候,命悬一线,吃饭都费劲,大家都以为我姥肯定是不行了,没想到竟然过了劫难,还能活八十好几没啥事。这是在我姥姥八十多岁的生日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那时候我姥刚顶香,正赶上国家困难,家家的生活水平都不好,县城村镇有来病人,求着我姥帮忙收下自己家的供奉,给我姥一袋米,送几个水果,我姥就帮人收下,来人感激万分,有的会给我姥磕头。姥姥供奉的那九个碗,就是这么来的,谁家的香灰倒进来,就算完事。
那时候的人好纯洁,有人味儿,我扪心自问这种活儿给我我是不敢接,那时候的仙也没听说像现在这么多胡闹的,蛮不讲理的,说话不作数的。现在如果还有人敢像我姥这样乱收萍水相逢的来客香炉,一定闹的鸡犬不宁,尤其是家里的小孩一定深受其害,但是那个时候我很幸运,我得到的疼爱不只是来自姥姥,也来自姥姥的守护神,因此我和姥姥的关系除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有精神上的血脉传承关系,姥姥用终身教会我,善良或许吃一时之亏,善恶有报却如影随形。
姥姥的衣钵我是没有传承,没有做新时代的萨满,接下这个衣钵的是我妹。其他方面的传承我想是有的,姥姥年轻的时候,曾帮忙带过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生的十分古灵精怪,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个孩子。后来渐渐大了,家长自己可以带了就领走了,再后来,听说了这个小孩的不幸,精神上有些失常,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和心性,甚至经常失去意识。
后来如何得知这个小孩的消息呢?是因为这个孩子竟然是师父的亲戚,师父给这孩子控制了七年,稍微稳定住这孩子的病情,直到去年,机缘驱使之下,我带大爷去阁皂山寻求降魔之法,意外竟然找到了那小男孩虚病的命门。这难免让我感慨命运天机,彼时姥姥已经仙逝,那孩子刚出生时由我姥度,我姥去世后,我竟也能在他的病上出一份力,无心之下度他一程,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传承吧。

我小时候多次被保护,几次意外濒临死亡,都能获救,长大后跟随师傅修行多年,才后知后觉,这都是姥姥冥冥之中为我积下的福报,可惜等我懂了,斯人已逝,追悔莫及。
还有一些保护,不在冥冥之中,而是姥姥亲力亲为。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乡出了一个变态,专门骑着摩托车,手里拿着把刀捅女人的屁股。一开始这个变态只捅40岁左右女人的屁股,医院每天都会收治类似的病人,消息走漏的非常快,县城里出了一个变态!广大女性晚上一定护好自己的腚眼,少出门,不出门。
后来这个变态不知道怎么的,连小女生的屁股也捅,隔壁中学的一个女生就被他给偷袭了,再后来更加变本加厉,连男的也被捅了。就在这样人人自危的环境,我姥姥担心我也被捅,把心提到嗓子眼,要走二百米一点灯亮都没有的暗黑胡同,来到胡同口和大街交接的路口接我晚自习下课回家。
我姥会穿着米色花点点图样的丝料的衣服,佝偻着背,风吹的她黑白夹杂的头发轻轻的摆,她背着手站在那个路口,邻居跟她打招呼她点个头,就又直直看着我回家的方向,直到看见我,眼睛眯起来小小的,嘴情不自禁的笑着迎接我。接到我就会跟我讲,今天又在村口跟老太太们闲聊,夸我上个月考了第一名的事情;会跟我讲那些老婆子教唆他们的孩子,不要跟我这样一个喜欢蹲网吧打游戏的小孩一起玩,我偏要讲我的外孙学习最好,打游戏也比你们学习好。然后一把搂过我,问我今天上学是不是开心,有没有学的够好,然后颤颤悠悠的跟我说:“咱俩快点走,别倒霉碰上那个变态!”

因为当时住的也是平房,就是烧煤烧柴取暖的那种,卧室里面一张大火炕,炕头从来都是姥姥让给我睡。姥姥会早早的在太阳落下,就把被子从炕梢上的炕柜上一层一层拿下来铺好。
满族人的火炕,会把炕头留给最珍贵的客人和最被宠爱的孩子,因为东北的冬季寒冷,炕头离炉火最近,炕梢是离炉火最远的地方,一般给壮年男子去睡。满族人的婚嫁传统来讲,女儿出嫁,娘家会给打一个嫁妆柜子,放一些压箱底的钱、珠宝首饰、被子衣物等。
我现在还记得姥姥炕梢的那个红柜子上,雕工精美,雕着鸳鸯,物件太多,姥姥会把被子直接放在柜顶上面,一层一层被子叠起来后,盖上个帘子防尘。许多被子我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有一个被褥,铺在身下用,一面是那种竖条格子的布纹,一面是绿色的烫绒布料绣着一对鸳鸯在嬉戏,躺在身下别提多舒服。
我现在想,那柜子不仅见证着岁月,见证姥姥从待字闺中到嫁人为妇的身份转变,也承载着她姐姐对她的牵挂和祝福。我的大姨姥,她的姐姐,活了一百来岁,在我姥姥去世的一周内,也跟她去了,想是怕妹妹年幼,照顾不好自己,陪着一起做个伴了。

姥爷的去世,是在姥姥去世之前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很小,离开灵堂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正准备睡觉,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使我从头到脚,从四肢到牙齿都忍不住的打冷颤。
我蜷缩成一团碰醒姥姥,我说姥姥我很害怕,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很怕,我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的哭。姥姥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控制不住。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邪的经历,当时姥姥用老萨满的方法帮我摸了脉,抱紧我就对着空气一顿骂:“你要作死!你喜欢孩子你也不能这么样!”说实话姥姥对着空气在骂让我更加的害怕了,但又怕又有安全感。
在姥姥沟通完之后,带着我重新穿上衣服回到了灵堂,我见到众人关切的问姥姥怎么了,并好好检查了姥姥手腕上的红布,我自己一个人出来透透气,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狂笑。
我曾一度自责为什么会在疼爱我的姥爷葬礼上癫狂发笑,一直都是我的一个心病,直到跟随师父修行,才明白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开心之情,只是我当时太小,什么都不懂。
年岁太小,面临家人的离世,虽然也是痛苦,但对离别之事还不甚理解,相比之下,人越是年长,每每想起往事,才更懂追思如潮,离别的痛不仅是在当时抓不住的挽留,更是在日后每一个瞬间,想起那些快乐的岁月,心头一紧却无可奈何的神伤。
住在小平房的日子,无疑是非常快乐的,姥姥疼我,我也心疼姥姥。姥姥会在秋天就购买一车大煤块,或许大煤块更便宜,姥姥才没有买精细的煤产品,可大煤块需要砸碎了,才能够放进炉子里去烧。我那时候就自告奋勇去帮姥姥砸煤块,其实小时候还是挺白的,拎着大锤砸下去,煤粉扑面而来,砸完了整张脸都是磨砂黑,有汗的时候顺着汗躺下来,像石油流下来一样。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防护,连个口罩也没有,吸入肺里的情况一定是有的,那煤粉颗粒留在肺里,亦如和姥姥的快乐时光,将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拔除。
我姥会在我砸煤的时候,进里屋(老人会这么称呼卧室)去卷上一袋旱烟,逍遥的抽着,脸上美滋滋的,等我妈回来了,就跟我妈说我多么的懂事。淘气包也不是只会惹祸,平时我喜欢爬着砖墙爬到门上方的平台上晒太阳,我姥出来就骂我。
有一回烟囱漏水了,我姥给我拿了一盆水泥,给我拿了几片瓦,让我顺着墙直接爬到房子上面去把裂开的瓦片换成新的。这么有意思的淘气的活儿,我当然不辱使命的接下,在我聚精会神的换瓦片时,只听我姥在地面嗷的一声:“孩儿啊!”我这心脏跟炸了一下似得,我赶紧从烟囱处跑到另一侧靠近姥姥的房檐问:“怎么了?怎么了?姥咋的了”。我姥长舒一口气说:“哎呀,我看你半天没动静啊!”我很无奈的说:“姥啊,我在这认真的糊瓦片呢,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我没掉下来都要被你吓的掉下来了啊,你别再喊了啊,我一会儿就糊好了!”我就继续翻到另一面屋檐去糊烟囱,能糊五分钟,我姥就又嗷的一声喊:“孩儿啊!”我应了一声,赶紧糊完赶紧下来了,免得老太太一直担心。
那时候我们还养了一条大土狗,姥姥给它取名“旺财”,我当时酷爱三国,取名“阿瞒”,我姥不同意,嫌弃绕口难听:“叫它旺财!旺财!”。那狗也不理我姥,理什么理啊,出了家门,我就带着我的“阿瞒”一路狂飙,一边跑一边笑,一边喊“阿瞒!阿瞒!”
那狗跟我玩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自己“阿瞒”的名字。可怜我姥那时候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出去喊狗回家,脸憋通红,怯生生喊:“阿瞒啊!回家啊!”。等我妈回来了跟我妈告状:“给阿瞒的名字取的也太难听了,我都喊不出口!什么啊,我一出去喊对门老太太都问我喊什么”
在那个小胡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姥一生非常简约,那时候也就挂着个很细的金项链,一个金戒指。有一天一个路过的女的,跟门口溜达的姥姥说:“大娘啊,我好渴啊,我能不能去你家喝完水啊?”我姥一直很善良,说:“那没多大点事儿,你进来吧。”我姥就在前面领着那个女的,那女的在身后喊我姥,我姥一回头,那女的照着面门额头就给她拍了一下子,我姥当时就失去了意识。那天是我姥姥极其懊恼的一天,说遇到了传说中的拍花子,一辈子就这么点玩意儿全被她拍去了,我们一家人倒是只剩下庆幸,钱财事小,姥姥毕竟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丢了点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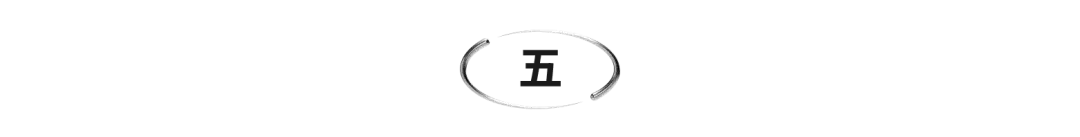
临近甲辰年春节,那时我妈来香港陪我,没想到再回东北,老人就已经在医院了,虽然摔伤了髋骨,姥姥看见我时,却在病床上神采奕奕。她在icu跟着对面床的病人和家属骄傲的说:“这是我外孙的!对我可好了!每年都会给我包1000块的大红包呢!”她的声音那么明快响亮,让我一时恍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几天就可以出重症,回普通病床养一阵子,就好了吧。
像我们这种能掐会算的,总有人问师傅能不能给自己算,能,技术上没有难度,难的是过自己心里的关。
姥姥是八字中的曲直仁寿格,一生之中遭遇劫难无数,历经几朝更迭,她会给我讲小时候毛子打来东北时候,老百姓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也给我讲日本人来了,小县城是什么样的景象;还给我讲国民政府时期,袁大头把自己的头印在了钢镚上;讲建国初是怎么吃不上饭,让我要知足常乐。她喜欢看二人转包公铡驸马的故事,电视剧就喜欢看《还珠格格》和《铁齿铜牙纪晓岚》,小时候和姥姥一起看,她每每看的津津有味,嘎嘎的笑,直到听着电视睡着打呼噜。
我来医院,特地下载了好多二人转的视频,给姥姥躺着的时候放着二人转听。家人轮番的照顾,我妈和我姨每每情绪崩溃,我安慰她们,没关系的,凶险的2022年,已经过去了,2024虽然也不好,但我觉得甲辰年毕竟没有壬寅年那么凶险,请多宽心,好好照顾一定能养好伤出院的。
知道姥姥可能在2022年就有劫难,我2022年春就从北京回到了县城,这段时间姥姥状态非常安稳,这让我精神稍有懈怠,因此在2023年秋就准备出门再深造学习,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临近过年,竟发生这种事。
师父也知我心急如焚,特地从县城跑来沈阳探病,姥姥握着师父的手,托付师傅关于仙的什么事,师父说:“你放心,你会好起来,等你好了你自己处理!大姨,你好好养病。”顺手掏了一个红包塞到了我姥的手里,我姥非常的开心,从师父的话里听到了希望。
我也在旁边听到了希望,果然,姥姥就是有福之人,有难当头自然会有帮她解的,回想2022年,我姥在大街上被车撞了一下,人直接被撞倒,怎料我姥九十岁高龄,起身拍拍灰,跟那司机说“我没事你忙你的去吧。”把全家都吓得不轻。这次虽然摔到骨折,只要有我大爷亲自过来保佑,一定会恢复的。
大爷跟我聊的非常小心,我知道他又是怕我接受不了,又想尽全力去帮我,我也知道他尽全力了,既全力以法力加持,也全力照顾我的情绪,我到最后一刻都没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

医生已经下了几次逐客令,让我们带姥姥回家养,就算这样,我还依然乐观的相信回去养会好起来,姥姥看着我又一次从香港回来看她,激动的笑逐颜开,用微弱力气叫我过去抱一抱,在我的后背拍了拍,拍我的时候十分有力。其他亲戚来看她,都说她的外孙孝顺,这么远的路几次三番回来看她,说她有福,她撑起精神露出骄傲的神情我始终难忘。
我掀开被子看了看,姥姥的腿已经紫色发黑,我还乐观的想,不行就截肢,也会好吧。姥姥最喜欢我睡在她的身旁,好在东北的房屋都是有地暖的,老平房我们早就不住了,我在姥姥床边打了个地铺,只够一个人翻身的位置,脚下是姥姥的呼吸机。
凌晨两三点,姥姥忽然非常大声音的喊出来一句:“让我走吧!”
这使得我和当值的小姨十分错愕,我不敢乱想,我得承认此时的自己是十分的自私,明白姥姥非常的痛苦,但真的是不舍。回想姥姥本就不是凡人,在我去留学之前,姥姥曾多次告诉我梦见她死去的兄弟姐妹,还认真的抓住我,告诉我“我快死了”
我都以老年人小脑萎缩,出现幻觉为由,没当回事,现在想来,一个老人如果频繁提及自己逝去的亲朋好友,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如果当时我多留心,就会在她生活的环境多一些留意,可惜我看似学的多懂的多,在面对自己家的事情,连最基本的事情也都想不明白。不愿意去相信,这六个字害苦自己和家人。
这类的提示不仅有姥姥直接的求救,也有我自己的第六感。就是在我开车南下的那一天,我坐上驾驶位,我开车走出三公里,心里有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姥姥?”
这个念头产生的极其莫名其妙,我害怕去相信,我赶紧心里打掉这个念头:“不可能,不会。”
写到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吞噬着我,因为在我姥爷去世的前一个月,我每天心里有声音:“你姥爷快死了。”我压制不掉那个声音,任由它去吵,不久我姥爷真的没有了,我一度以为是我给丧门死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以后就给打掉,可能姥爷就不会走那么早。
所以这次我就毫不迟疑的打掉了这个不好的念头,可还是于事无补,也许老仙真的已经尽力了,大爷说,姥姥早就该走的,生死簿上早就过期了,全凭老仙护着,才走到现在。
我何尝不知姥姥早应在2022年有意外,只是人毕竟无法与天抗衡,多出来的几年本就是恩赐,可能是老天赐我的时间,而我没有珍惜,跑去了南方,老天一看我都走了,不看姥姥了,于是就给姥姥带走修行去了。
再见到姥姥时,姥姥已经躺在冰冷的冰棺之中,摆在面前的是她一贯慈祥的笑容,等我返回山城的火葬场已经是后半夜三四点,我疯了一样跪在棺木前面,我鬼哭狼嚎的喊:“姥啊,我回来了。姥啊,我回来了。”山谷传来阵阵回音,我感觉灵堂外山上的雪也在振动,农历二月,云彩夹杂着雨和雪一起飘落,山谷可以回应我,但姥姥无法回应我。我感觉到火葬场周遭的孤魂也被我喊叫的过来看热闹,但是我感觉不到我姥姥,此时此刻到底在哪里。
家里的丧事来了很多人,师父全程陪伴护佑我,还因为我的事把别的事情全部推了,因为火葬场这种地方极其阴森,师父这种人,到火葬场就像一个磁铁掉进了铁钉盒子,浑身都被吸附着负能量,导致师父回去难受了很多天,这个恩情我会一直铭记。
有师父在,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火化完毕,工作人员将姥姥的白骨放置在木棺,散发着阵阵香气的同时,我的目光逐渐呆滞。我不知道是悲伤过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浑身无法动弹,我只能脑袋动,眼睛望着前方,话都艰难说不出口,我妈赶紧叫了大爷过来帮忙,还好大爷略一施法我就好了。
我把前一夜去给姥姥买的上好的一条烟交给了出黑的先生,那先生把我的烟,我姥平时喜欢的衣服,还有这几日烧的纸灰包好了放在棺木之中,姥姥昔日骂我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两年前:
“孩儿,姥求你点事儿”
“啥事儿?买烟!”
“嗯,我给你钱,我给你跑道费,你去给姥买一盒就行!”
“不行啊,你咳嗽,她们都不让给你买烟,不然就骂我了。”
“我不说是你买的,你去给姥买一包吧!”
“我不去,医生也不让你抽烟。”
“你就不能帮我去买一下!”
我不作答
“操你个妈的,还说你孝顺!帮我买个烟都不行!”
我还是不做声
“你孝顺你妈个b”
这回好了,姥,我买了最好的烟给你,你应该不会骂我了,可也听不见你的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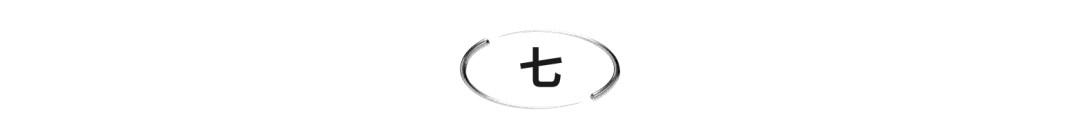
下葬那天,车队拉着姥姥的子侄孙辈一起上了车,常年伺候姥姥的妈妈,每周都要陪姥姥的姨娘没有被准予去参与下葬。出黑的先生说,女人的阴气重,会坏了阴宅的风水,对活人多有不利。
多么可笑的规矩,常年伺候陪伴的不可以去送最后一程,常年不见的亲戚,只因为长个屌就可以为逝者的人生画个句号。
那要是从我和师父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破坏风水是没有的,但下葬时阴气极重,对女人多有不好,这个确实存在,但这应当给妇女朋友一个选择权,就像知道有细菌的环境,人可能会致病。一是致病的概率问题,如果免疫力足够强,那做好防护也不是不行;二是事件的必要性,无必要当然最好别得病,但这么重要的时刻,即便有得病的风险,也应该由当事人决定,而不是由腐朽的落后的,不讲人伦的,丑陋的规矩来道德绑架本就伤心欲绝的逝者女儿。
在姥姥弥留之际,我握住病床前姥姥的手,我说我会坚持写作,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篇文章其实没有什么目的,然而写作这件事本身意义很大,灵界的规矩也该改改了,任何人都有权选择最亲的人送自己最后一程!我必将和师父一道把另一个世界要去调整的规则跟大家讲明白;必将告诉大家如果要去改变这些陋习,要去准备好哪些事情;必将和封建陋习斗争到底。
姥姥的离世,对我的刺激极大,盲目自信的我受到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也让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功成名就?是光大门楣?是学富五车?是人前显耀?是家财万贯?是威名显赫?是执掌权柄?都不是,我只想多陪姥姥呆两天。
只有在面对生死课题时,才懂得平时追求的事业学业有多么可笑,至亲之人不在,身外之物死后也带不走。我们人生的过程,是不是做了我们认为值得的事情,是不是给了最亲的人付出了最好的自己可以付出的,这比较重要。我现在觉得陪师父写东西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义,让更多的人明白善恶因果,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些故事明白生命中的无常,去认识到苦是什么,去珍惜现有的一切,去愿意试着领悟佛法道法,看到生命的本质真谛在于离苦得乐,如此就善莫大焉,姥姥也会为我欣慰的。

因为我姥是一个老萨满,我姥是不会投胎了,因此借我姥入梦考验我的情况非常多。姥姥当你看到这个故事,你肯定又要骂我了。
正是我在香港斗法很激烈的那段日子,也是邪崇知道我意志力最为薄弱的阶段。逐渐沉睡,只见我姥漂浮在半空,就像平房那样的空间,我姥邀请我去她身边躺着,我小心翼翼的过去躺在她的身旁,但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我冥冥之中告诉自己,姥姥已经死了,这只是个梦。
她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回:“嗯我知道,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问:“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你的爹!”
只见梦里我这个姥气的面红耳赤,一溜烟就没有了,就像白骨精的气一样飘走的感觉。
醒来我哈哈大笑,我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呢,第二天又做梦梦见一个算卦的女子在街边摆摊,我路过她的卦摊子,她前后说我的信息都对,我认真的给她作了个揖说道:“之前多有得罪!”
然后梦就醒了,哈哈,这是假托我姥的名义入梦来搞我,被我识破被我羞的不行,第二天换个方式要我道歉。
这人生啊,真是艰难,阳间的苦痛要逐渐抽离,认识到真道,晚上要践行真道,彻底升华,突破自我,突破亲情的思念,才能突破阴阳两界的隔阂,姥姥,我会好好保护自己,你放心,被你搂在怀里护着的孩子长大了,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那最后这个故事不是讲给姥姥,是讲给看到这里的有缘人,希望你能破除幻象,打破心魔,珍惜眼前。愿大家都能在各自的苦中得到解脱,都能得真自在,大圆满。
福生无量天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