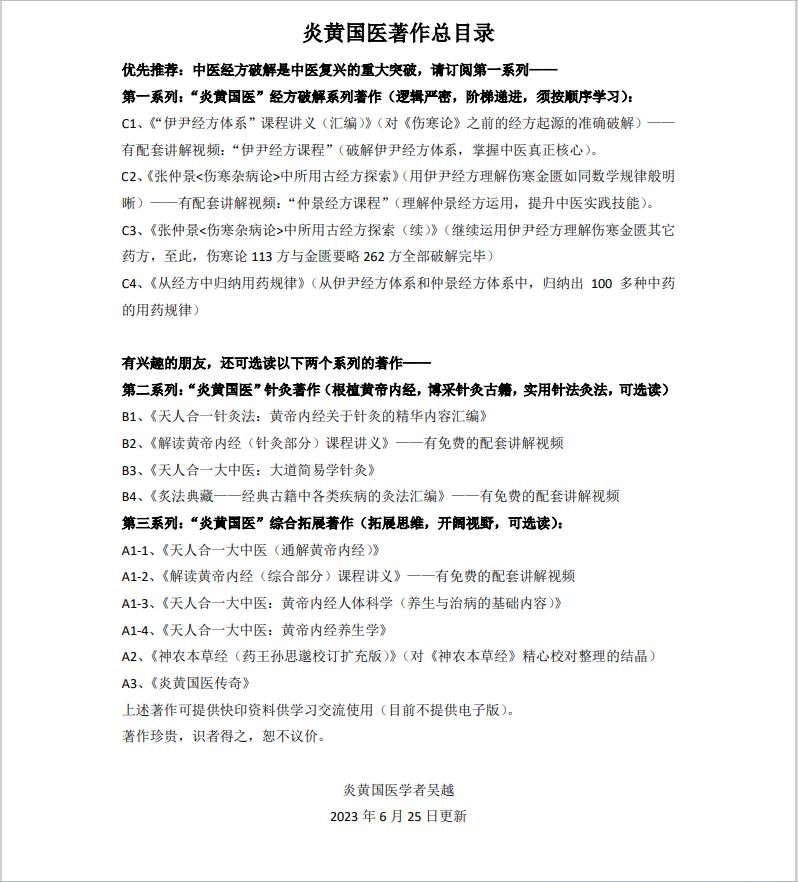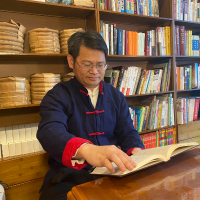原文:
38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燥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 六两(去节) 桂枝 二两(去皮) 甘草 二两(炙) 杏仁 四十枚(去皮尖) 生姜 三两(切) 大枣 十枚(擘) 石膏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注解:
太阳中风,脉浮紧——风邪夹寒,束表,所以脉紧、不出汗。此时不能因“中风”两字而用桂枝汤,而要用《伤寒论》中的大青龙汤。
大青龙汤证涉及的热不重,只是“烦燥”,烦躁是轻微的里热,没有热到汗出而喘和大烦渴的地步,而且还有表部的风或寒需要宣散,所以不能用白虎汤除热。
此条说“太阳中风”,紧接着讲的却都是伤寒的证:“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这是为什么呢?张锡纯认为这是“风温”——柔和的风温。后面多出一个证“烦躁”。更证明是温病。
大青龙汤是从麻黄汤演化而来的,炙甘草加倍,加上生姜、大枣和生石膏;或者说,大青龙汤是麻黄汤和桂枝汤合方加生石膏。加一点生石膏是为了去热。石膏用量,鸡子大,古时候鸡蛋小,应该是几十克。中风用桂枝汤,伤寒用麻黄汤,有内热(多数是患者的伏热所致)加生石膏。
这个方子里的麻黄的剂量是六两,也就是90克(当时可能是生品),而石膏的用量却很轻。因为此时的里热是毛孔不开郁在里面了,而不是真的有多热,所以石膏的用量是较轻的,而重用麻黄打开毛孔。
后面说“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如果已经脉微,就不能服用大青龙汤,脉微是虚证,毕竟大青龙汤还是发汗剂,若再发汗的话,势必会有“厥逆”,就是四肢冰冷,四逆证了;还会有“筋惕肉瞤”,筋脉和肉都会有瞤动不灵活的反应,这就是逆治了。“汗出恶风”是桂枝汤证。
据研究,除了外感病外,很多头部的疾患都可用到大青龙汤,比如五官疾患、颅内疾患、癫痫之类神经科疾患等,包括治现代医学所谓的“中风”,也就是高血压中风也可以用到。治中风瘫痪的古方“续命汤”,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方子的变化方,加了一些去淤血的药而已。头部疾患常常是因为表不解,邪不能出表,上冲于头而造成的。
附张锡纯论“太阳病大青龙汤证”
属性:有太阳中风之脉,兼见太阳伤寒之脉者,大青龙汤所主之证是也。
《伤寒论》原文∶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大青龙汤方】麻黄六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二两炙,杏仁五十个去皮尖,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石膏如鸡子大碎(如鸡子大当有今之三两)。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此大青龙汤所主之证,原系胸中先有蕴热,又为风寒锢其外表,致其胸中之蕴热有蓄极外越之势。而其锢闭之风寒,而犹恐芍药苦降酸敛之性,似于发汗不宜,而代以石膏,且多用之以浓其力,其辛散凉润之性,既能助麻、桂达表,又善化胸中蕴蓄之热为汗,随麻、桂透表而出也,为有云腾致雨之象,是以名为大青龙也。至于脉微弱汗出恶风者,原系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固摄卫气,即使有热亦是虚阳外浮,若误投以大青龙汤,人必至虚者益虚,其人之元阳因气分虚极而欲脱,遂致肝风萌动而筋惕肉瞤也。夫大青龙汤既不可用,遇此证者自当另有治法,拟用生黄芪、生杭芍各五钱,麻黄钱半,煎汤一次服下,此用麻黄以逐其外感,黄芪以补其气虚,芍药以清其虚热也。为方中有黄芪以补助气分,故麻黄仍可少用也。若其人已误服大青龙汤,而大汗亡阳,筋惕肉瞤者,宜去方中麻黄加净萸肉一两。
《伤寒论》原文∶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细思此节之文,知所言之证原系温病,而节首冠以伤寒二字者,因中风、温病在本书之定例,均可名为伤寒也。凡外感之脉多浮,以其多兼中风也。前节言伤寒脉浮紧,是所中者为凛冽之寒风,是中风兼伤寒也。
后节言伤寒脉浮缓,知所中者非凛冽之寒风,当为柔和之温风,既中柔和之温风,则即成风温矣。是以病为伤寒必胸中烦躁而后可用石膏,至温病其胸中不烦躁,亦恒可用石膏,且其身不疼但重,伤寒第六节温病提纲中,原明言身重此明征也。况其证乍有轻时,若在伤寒必不复重用石膏,惟温病虽有轻时,亦可重用石膏。又伤寒初得有少阴证,若温病则始终无少阴证(少阴证有寒有热,此言无少阴证,指少阴之寒证而言,少阴寒证断不可用大青龙汤,至少阴热证,原为伏气化热窜入少阴,虽在初得亦可治以大青龙汤,此又不可不知),此尤不为伤寒而为温病之明征也。由此观之,是此节原为治温病者说法,欲其急清燥热以存真阴为先务也。至愚用此方治温病时,恒以薄荷代方中桂枝,尤为稳妥。
凡发汗所用之药,其或凉或热,贵与病适宜。其初得病寒者宜用热药发其汗,初得病热者宜用凉药发其汗。如大青龙汤证,若投以麻黄汤则以热济热,恒不能出汗,即或出汗其病不惟不解,转益增烦躁,惟于麻、桂汤中去芍药,重加石膏多于麻、桂数倍,其凉润轻散之性,与胸中之烦躁化合自能作汗,矧有麻黄之善透表者以助之,故服后复杯之顷,即可周身得汗也。
曾治一人冬日得伤寒证,胸中异常烦躁,医者不识为大青龙汤证,竟投以麻黄汤,服后分毫无汗,胸中烦躁益甚,自觉屋隘莫能容,诊其脉洪滑而浮,治以大青龙汤,为加天花粉八钱,服后五分钟,周身汗出如洗,病若失。
或问∶服桂枝汤者,宜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服麻黄汤者,复取微似汗,知亦不可令汗如水流漓也。今于大青龙汤中加花粉,服汤后竟汗出如洗而病若失者何也?答曰∶善哉问也,此中原有妙理,非此问莫能发之。凡伤寒、温病,皆忌伤其阴分,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禁过发汗者恐伤其阴分也。
至大青龙汤证,其胸中蕴有燥热,得重量之石膏则化合而为汗,其燥热愈深者,化合之汗愈多,非尽量透发于外,其燥热即不能彻底清肃,是以此等汗不出则已,出则如时雨沛然莫可遏抑。盖麻黄、桂枝等汤,皆用药以祛病,得微汗则药力即能胜病,是以无事过汗以伤阴分。至大青龙汤乃合麻、桂为一方,又去芍药之酸收,益以石膏之辛凉,其与胸中所蕴之燥热化合,犹如冶红之铁沃之以水,其热气自然蓬勃四达,此乃调燮其阴阳,听其自汗,此中精微之理,与服桂枝、麻黄两汤不可过汗者,迥不侔也。
或问∶大青龙汤证,当病之初得何以胸中即蕴此大热?答曰∶此伤寒中伏气化热证也(温病中有伏气化热,伤寒中亦有伏气化热)。因从前所受外寒甚轻,不能遽病,惟伏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塞升降之气化,久而化热,后又因薄受外感之激动,其热陡发,窜入胸中空旷之府,不汗出而烦躁,夫胸中原为太阳之府,为其犹在太阳,是以其热虽甚而仍可汗解也。

附张锡纯论“麻黄加知母汤”
属性:治伤寒无汗。
麻黄(四钱) 桂枝尖(二钱) 甘草(一钱) 杏仁(二钱,去皮炒) 知母(三钱)
先煮麻黄五六沸,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一茶盅。温服复被,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麻黄汤原方,桂枝下有去皮二字,非去枝上之皮也。古人用桂枝,惟取梢尖嫩枝折视之,内外如一,皮骨不分。若见有皮骨可分辨者,去之不用,故曰去皮。陈修园之侄鸣岐曾详论之。
《伤寒论》太阳篇中麻黄汤,原在桂枝汤后。而麻黄证多,桂枝证不过十中之一二,且病名伤寒,麻黄汤为治伤寒初得之主方,故先录之。
伤寒之证,先自背受之,背者足太阳所辖之部位也。是以其证初得,周身虽皆恶寒,而背之恶寒尤甚,周身虽皆觉疼,而背下连腿之疼痛尤甚。其脉阴阳俱紧者,诚以太阳为周身外卫之阳,陡为风寒所袭,逼其阳气内陷,与脉相并,其脉当有力,而作起伏迭涌之势。而寒气之缩力(凡物之体热则涨,寒则缩),又将外卫之气缩紧,逼压脉道,使不得起伏成波澜,而惟现弦直有力之象。甚或因不能起伏,而至左右弹动。
凡脉之紧者必有力。夫脉之跳动,心脏主之。而其跳动之有力,不但心主之也;诸脏腑有热皆可助脉之跳动有力,营卫中有热亦可助脉之跳动有力。特是脉之有力者,恒若水之有浪,大有起伏之势。而紧脉虽有力,转若无所起伏,诚以严寒束其外表,其收缩之力能逼营卫之热内陷与脉相并,以助其有力;而其收缩之力又能遏抑脉之跳动,使无起伏。是紧脉之真相,原于平行中见其有力也。至于紧脉或左右弹者,亦蓄极而旁溢之象也。仲师治以麻黄汤,所以解外表所束之寒也。
方中用麻黄之性热中空者,直走太阳之经,外达皮毛,借汗解以祛外感之寒。桂枝之辛温微甘者,偕同甘草以温肌肉、实腠理,助麻黄托寒外出。杏仁之苦降者,入胸中以降逆定喘。原方止此四味,而愚为加知母者,诚以服此汤后,间有汗出不解者,非因汗出未透,实因余热未清也。佐以知母于发表之中,兼寓清热之意,自无汗后不解之虞。此乃屡经试验,而确知其然,非敢于经方轻为加减也。
或问∶喘为肺脏之病,太阳经于肺无涉,而其证多兼微喘者何也?答曰∶胸中亦太阳部位,其中所积之大气,原与周身卫气,息息相通。卫气既为寒气所束,则大气内郁,必膨胀而上逆冲肺,此喘之所由来也。又风寒袭于皮毛,必兼入手太阴肺经,挟痰涎凝郁肺窍,此又喘之所由来也。麻黄能兼入手太阴经,散其在经之风寒,更能直入肺中,以泻其郁满。所以能发太阳之汗者不仅麻黄,而仲景独取麻黄,为治足经之药,而手经亦兼顾无遗,此仲景制方之妙也。
凡利小便之药,其中空者,多兼能发汗, 蓄、木通之类是也。发汗之药,其中空者,多兼能利小便,麻黄、柴胡之类是也。太阳经病,往往兼及于膀胱,以其为太阳之腑也。麻黄汤治太阳在经之邪,而在腑者亦兼能治之。盖在经之邪,由汗而解,而在腑之邪,亦可由小便而解。彼后世自作聪明,恒用他药以代麻黄汤者,于此义盖未之审也。
大青龙汤,治伤寒无汗烦躁。是胸中先有内热,无所发泄,遂郁而作烦躁,故于解表药中,加石膏以清内热。然麻黄与石膏并用,间有不汗之时。若用此方,将知母加重数钱,其寒润之性,能入胸中化合而为汁,随麻、桂以达于外,而烦躁自除矣。
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为其始异也,故伤寒发表,可用温热,温病发表必须辛凉。为其终同也,故病传阳明之后,无论寒温,皆宜治以寒凉,而大忌温热。兹编于解表类中,略取《伤寒论》太阳篇数方,少加疏解,俾初学知伤寒初得治法,原异于温病,因益知温病初得治法,不同于伤寒。至于伤寒三阴治法,虽亦与温病多不同,然其证甚少。若扩充言之,则凡因寒而得之霍乱、痧证,又似皆包括其中。精微浩繁,万言莫罄,欲精其业者,取原书细观可也。
伤寒+身重:《伤寒论》大青龙汤原文:
39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大青龙汤发之。
注解:
本条,请参阅张锡纯的讲解。
此条的身体重,张锡纯认为是“身重者身体经热酸软也”(见麻杏石甘汤证)。
本条虽然没有明显的热象,但接着上一条来理解,属于温病,所以要用石膏清热,只是多少的量不同而已。
上一条脉紧身疼用大青龙汤,这一条脉缓身不疼也用大青龙汤,每个“六合方”,包括大青龙汤,都是能调整人体某种困局,所以能治这种困局造成的一切病。有时候方证不相对,因为疾病复杂,总有对不上的时候,要抓住药方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