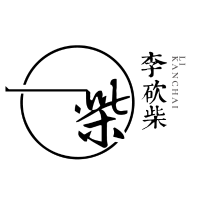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罗米亚州,生活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博拉纳族(Borana)。
关于他们的起源,历史记载寥寥,尽管缺乏明确的起源神话,博拉纳人却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民族的历史:盐。
千百年来,他们依靠一座火山口的盐湖,将采盐发展为全族的生存命脉,甚至因此被称为“盐的部落”。
距离博拉纳村庄约2.5公里的死火山口内,隐藏着一片直径1.8公里的盐湖。湖水因高浓度矿物质呈现深黑色,散发着刺鼻的硫磺味。
然而,这片看似“死亡之地”的湖泊,却是博拉纳人的“黄金矿场”。

虽然现在的博拉纳人凭借着采盐成为了“定居民族”,但有学者推测,博拉纳人可能是非洲古老的游牧民族后裔,与东非的奥罗莫人(Oromo)有密切关联。
他们的语言属于库希特语系,文化中融合了伊斯兰教与传统泛灵信仰,形成独特的生存哲学。
每年雨季过后,湖水浓度被稀释,200多名男性村民便赤膊踏入湖中。他们用长棍探测深浅,徒手挖掘湖底富含盐分的淤泥。
由于湖水腐蚀性极强,长期浸泡会导致皮肤溃烂、耳聋甚至失明。尽管村民用黏土和塑料自制耳塞、鼻塞,但健康代价依然不可避免。

博拉纳人的一天从凌晨开始。男人们徒步一小时抵达火山口,再攀爬340米陡坡下到湖边。他们必须在烈日最毒的中午前完成采盐,否则淤泥会在高温下板结。
采得的盐分为三种:黑盐:用于喂养牲畜;白盐:日常食用;结晶盐:最珍贵的品种,可高价出售。
一头驴每次可驮运50公斤盐,往返村庄需一小时。一名采盐人日收入约8欧元(约合人民币60元),在埃塞俄比亚已算“高薪”,但背后是无数人用健康甚至生命换取的微薄回报。

采盐仅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将盐卖到远方。博拉纳人需要徒步7天、穿越200公里荒漠,将盐运至索马里或肯尼亚的集市。
这条“盐路”危机四伏,先是自然威胁:沙漠高温、野兽袭击、水源匮乏,都有可能导致盐贩死在路上。
当然,更危险的则是人为风险,遭遇劫匪或边境冲突,死亡率更是高的吓人。
纪录片《成为波拉纳的男人》记录了一名12岁少年瓦里奥的成年仪式:父亲带他踏上贩盐之旅,学习辨识方向、谈判价格,甚至如何在沙暴中求生。
对博拉纳男孩而言,完成这段旅程,才意味着成为真正的“男人”。

博拉纳人曾以游牧为生,如今虽定居采盐,但传统习俗仍深刻影响生活。例如,他们根据生肖为孩子取名,男性名字以“扎”(意为勇敢)开头,女性以“娜”(意为温柔)开头。
有趣的是,部分博拉纳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采盐时不再赤身裸体,而是穿着内衣下水——这一细节成为文化融合的缩影。
尽管采盐支撑着整个族群的经济,博拉纳人的生活条件却仍然极其艰苦:
首当其冲的就是水源,博拉纳村庄没有自来水,取水需步行数公里。其次是医疗资源匮乏,耳聋、失明等职业病普遍。最后是儿童被迫参与采盐,教育机会几乎为零。
更令人唏嘘的是,国际市场上的工业盐冲击了传统盐业,博拉纳人的收入逐年缩水。年轻人开始逃离村庄,千年传承的采盐技艺面临消亡。
近年来,随着博拉纳人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人专门去他们的栖息地旅游。
若你想探访博拉纳村落,要注意安全第一:盐湖周边地质脆弱,最好有当地向导陪同,其次注意文化禁忌:未经允许不得拍摄采盐过程,尤其是对女性。

近年来,博拉纳人的故事通过纪录片(如《博拉纳人采盐》《成为波拉纳的男人》)走入公众视野。
网友既惊叹于他们的坚韧,也争论“苦难是否该被消费”。或许,更重要的不是猎奇,而是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为这样的族群保留生存空间?
博拉纳族没有宏伟的宫殿或华丽的传说,他们的史诗写在每一粒盐中:少年瓦里奥第一次贩盐归来的笑容;父亲为女儿婚礼攒下的8欧元硬币;湖水中那些逐渐模糊的眼睛与耳朵……
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
当我们在餐桌上随手撒下一撮盐时,或许可以想起: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正用生命为它标价,这就是属于博拉纳族最真实最原始的生活和故事,时至今日,仍然在非洲大陆上上演。
本文作者 | 老A
责任编辑 | 蓝橙
策划 | 蓝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