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分部编纂的《笑府》,奠定了日后其他笑话书的分类基础。《笑府》各部开篇小序交待该部之缘由和要旨,使读者明了该部的主题,本文要讨论的三则笑话见于卷六《殊禀部》,其序云:

和刻本《笑府》
墨憨子曰:人之情性不同,好尚亦异,至于蜻蜓与游,疮痂为饭,则几于非人矣!吾独取夫騃子者,一团天趣,可矜可喜,世人皆笑其騃,而孰知其自谓不騃者,大騃人也。悲夫!集殊禀部。[1]

人有千百种,冯梦龙在此专门讨论“騃子”,这些呆子或因行径与人殊异,或因特殊癖好,而成了“笑柄”。
该部收录三则乡人观赏《琵琶记》时所闹的笑话,聚焦于“入戏”太深之行径,体现了乡人不明演剧习俗的可笑现象。前两则以“找戏”为致笑缘由,第三则刻划乡人好俗的观剧品味,致使演出凭添打闹场面。[2]
本文集中探讨“找戏”一词,第三则于此无关,不多赘言。往下分作两小节,以《笑府》两则笑话为发轫,试还原笑话所涉及的戏曲知识,并追踪笑话转手引用的多元意义。第二节考证“找戏”之演剧习俗,借由明清两本小说之勾勒,厘清所谓“找戏”即是今日所言的“饶戏”。

一、《笑府》以“找戏”发噱

《笑府》有两则《看戏》笑话,都在刻画乡人入戏太深,将正剧《琵琶记》和戏班加演的赠戏情节混淆了:

周越然旧藏《琵琶记》
有演《琵琶记》者,找戏是《荆钗》《逼嫁》,忽有人叹曰:“戏不可不看,极是长学问的,今日方知蔡伯喈母亲就是王十朋的丈母。”[3]

第十出演钱母与替孙家说媒的姑母(丑)一起逼嫁,姑母挑拨生事,两人沆瀣一气,执意要将玉莲嫁进豪门,由净、旦来演母女的冲突。[4]
对照《琵琶记》虽无母女矛盾,却有婆媳问题:蔡母(净)不满赵五娘,见于第十出《蔡母喈儿》因溺子而怪罪赵五娘;第二十出《糟糠自厌》蔡母先是怀疑媳妇背地里吃好东西,于得知五娘吃糠后,蔡母愧悔而亡。 而第二十二出《代尝汤药》,五娘好不容易买来汤药,蔡父心知大限不远,要张大公代写遗嘱,叮咛五娘改嫁,才是《琵琶记》中提及的“改嫁”情节。

昆曲《琵琶记》剧照
因两出戏中皆有两代女角之矛盾冲突,而且皆属净脚、旦脚的对手戏,因此蔡家家母和钱家继母之口吻态度,在乡人看来并无二致!
因为同一位演员先后扮演不同角色,导致观众如此反应,其背后意义有两层,就演员的立场来说,不论剧本为何,净脚扮饰年长妇人时旨在突显角色的声口动作,演员只要能表现出自身行当与剧中角色应有的艺术修为,便算合格出演了;而从观看的角度来说,观众却有可能将两出戏混为一谈,若不是中途入座,不知正在上演为何戏,便是连剧情故事都不清楚,也听不懂所唱之戏词,便会产生笑话中的谬误。
《笑府》第二则笑话一样是主演《琵琶记》,而加演《关公斩貂蝉》,导致观众评点讹谬:
有演《琵琶记》而找《关公斩貂蝉》者,乡人见之泣曰:“可惜好个孝顺媳妇,辛苦了一生,被红脸蛮子害了。”[5]

乡人的叹息是出于怜悯,却因搞不清楚前后两出戏有别,把赵五娘和关公糊里糊涂的牵扯在一起,反而白伤心了一场;旁观者清,乡人的行径就沦为笑话了。
据洪淑苓研究,元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已亡佚,而明传奇演关公斩貂蝉则见诸明代散出戏曲选集《风月锦囊》所收《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和《群音类选》所收《桃园记》第一折《关斩貂蝉》。[6]
洪氏说明小说与戏曲之所以有出入:“《三国演义》未收,而明传奇盛行者。可见其事荒诞不合理,文人雅士不予采纳,不过却受到一般民众的喜爱。寻思这则故事对关公‘不好色’的正直形象有增强的作用,而借美人之口来颂赞关公,也能传达庶民百姓‘敬英雄’的心理,因此得以流传下来。”[7]

《风月锦囊笺校》
与冯梦龙生卒相近的许自昌(1578-1623),其《樗斋漫录》卷三亦收此则笑话,几可作为注脚:
富家召客,命优作剧,先正衍《琵琶记》,后续衍《关云长斩貂蝉》故事,一乡人在坐,对众太息曰:“赵五娘吃了一世辛苦,临了被红脸醉汉杀了。”盖扮貂蝉者,即扮五娘之旦脚耳,人俱笑之。呜呼!今之秀才,看书不分段落,岂止如此。[8]

这段记载和《笑府》的笑话不同,冯梦龙并不说明乡人评论之所以犯错,系因演赵五娘者,又饰貂蝉,所以予人主戏和续演之戏是同一出,才会使观众误评讹谬。
因为戏班人手有限,每一行当只有一人,故由同一位旦脚先扮赵五娘,后演貂蝉,乡人不察戏班演出先是正戏,再加演赠戏,误以为是同一故事因而闹出笑话;而许自昌引述笑话之余,补上了关键性的说明,区分出前演《琵琶记》,后赠《关云长斩貂蝉》是演剧活动中的两个段落,由此再引申来感慨士人囫囵吞枣的读书陋习。
以上,冯、许两人生活时间几乎重叠,不约而同地载录该笑话,足见此则笑话流传甚广。

《徧行堂集》
此外,明末清初金堡(1614-1680),1620年参与抗清失败,出家为僧,《徧行堂集》卷之四十五《法语卷一·语录》亦以“邨汉进城看《琵琶记》、《关云长斩貂蝉》”来申说佛法:
上堂:今日中秋佳节,举两则看戏因缘,少伸供养。……有一邨汉进城看戏,看了一本《琵琶记》,一出《关云长斩貂蝉》,他便逢人叹惜道:可怜赵五娘一生行孝,到头来被个红脸蛮子杀了。大众,者邨汉便是十分糊涂,却也拈了脑后三斤铁,只添了眼里一重花,……[9]

纯朴的村汉一方面入戏太深,二方面又分不清楚前后两出戏是独立的故事,糊里糊涂的就同情赵五娘的遭遇。
澹归禅师从庶民熟悉的戏曲说起,信众一听便晓,而背后要传达的佛理是:把假戏当真的村汉固然糊涂,但其良善悲悯的秉性并非坏事;只是眼前所见的众生相是如此的眼花撩乱,常使人惑乱于表相,而忘记万相皆空。禅师以“脑后三斤铁”比喻村汉的偏执认真,正是呼应了冯梦龙将此笑话编于《殊禀部》的考虑。
以上两则笑话,皆是从《琵琶记》滥觞,一方面可让我们了解明代《琵琶记》盛演不辍的景况,另方面也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戏曲笑话的取材是随机聚拈,抑或有迹可循的呢?
如第一则笑话提及《荆钗记》和《琵琶记》,前者是宋元人所作,[10]后者成于元末高明之手,对明代人而言同属宋元旧编的南戏,入明以来更是版本纷见,传播广远,民间演剧用作正戏与找戏,尚属合理范围。

暖红室刊本《荆钗记》
至若第二则笑话,《关大王月下斩貂蝉》首见于元杂剧,后复见于明代戏曲选集,闽北建阳书商出版的《风月锦囊》,配合传唱的声腔是青阳腔、徽池雅调一类的弋阳腔系统,江南刊刻的《群音类选》则以昆腔为主。
将关云长斩貂蝉和赵五娘罗织成一个笑话,乍看有点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而笔者意外检索到诸葛味水的《女豪杰》杂剧,或许可提供一些线索。
明人祁彪佳(1602-1645)的《远山堂剧品》是著录明人杂剧的专书(其中元杂剧占极少数),分出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品,六品共二百四十二种,“能品”下著录诸葛味水作明杂剧《女豪杰》:
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近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是认煞《琵琶》,正所谓弄假成真矣。乃其为词尽可观。[11]

因该剧本亡佚,无从确知情节为何,从祁彪佳所记,该剧将貂蝉和赵五娘相提并论,同视为“女豪杰”。

《晚明曲家年谱》
又裴喆《明曲家诸葛味水考》指出,诸葛味水即诸葛元声,生卒不详,约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1522-1620)。[12]
由上则引文可知,诸葛元声创作的《女豪杰》,貂蝉修道成仙,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齐聚一堂,就是入戏太深,“弄假成真”了。兴许就是诸葛味水的《女豪杰》,将貂蝉和赵五娘绾合成剧,才触发了笑话的出现;而笑话捕捉的是乡人观剧时评论谬误的趣味,许自昌、金堡则再引申为一己之用。
总括上述,以《琵琶记》和《关云长斩貂蝉》作为谈题话头,其渊源与流衍可说是历经了各式文献的辗转沿用,或以讹传讹,或加油添醋,各为其用:

诸葛味水的明杂剧《女豪杰》是在剧本创作阶段就让貂蝉和赵五娘同台,是否成为冯梦龙《笑府》的直接来源,暂时无法妄下断言;而笑话刻划的是观众的反应,从观赏的角度来品评“赵五娘(貂蝉)被杀”。

《晚明曲家及文献辑考》
戏班演出常是正戏连带赠戏,由各门的行当脚色来充任不同戏出的角色人物,而看戏的常比演戏的还较真,冯梦龙收录该则笑话,将其归类在《殊禀部》,彰显乡人观剧太沉迷,将前后两出戏混为一谈;而许自昌以此笑话为引子,嗟叹士人读书也常有段落不分的毛病;金堡抗清失败遁入空门,上堂讲经时从佛家立场诠释村汉看戏,欲借此点醒执迷表相而不悟的信众。
类似的事例,因收录在不同性质的书里,笑话便衍生出多元的意义。[13]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从创作及观赏两个面向来理解戏曲笑话背后丰富的蕴义。[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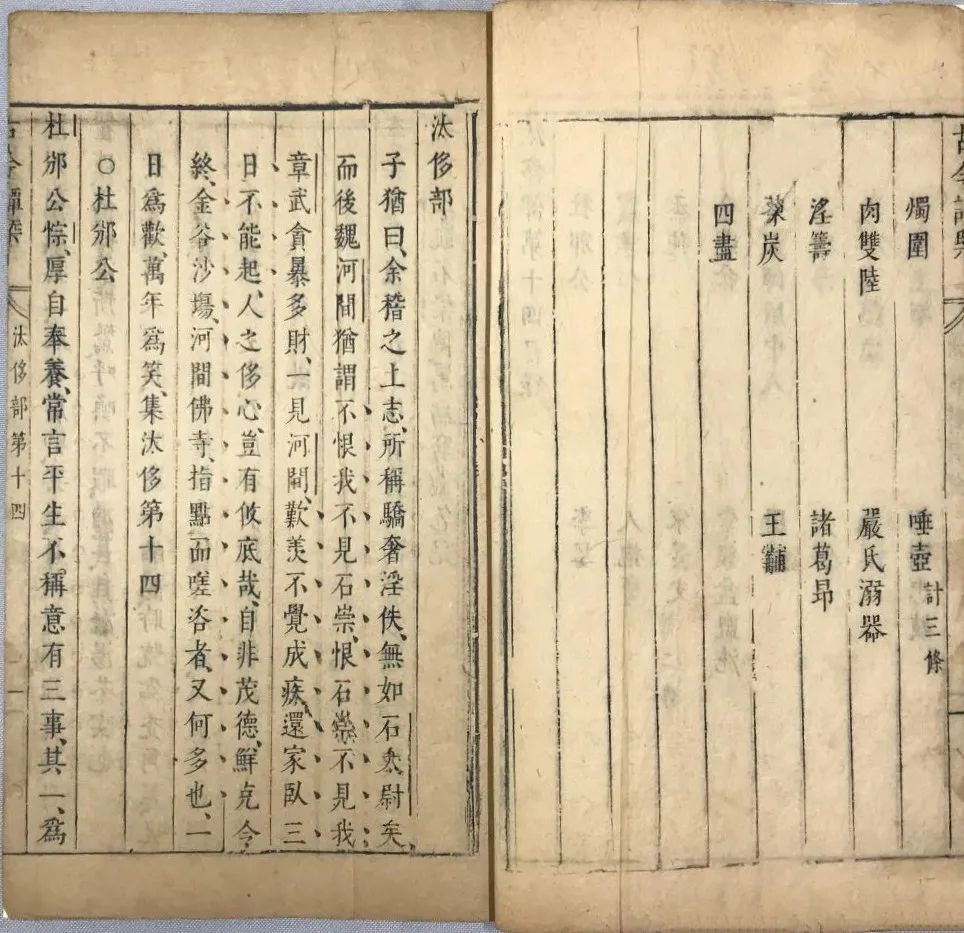
《古今谭概》


前文所引两则笑话中有“找戏”一词,第二则更把“找戏”的“找”当作动词。冯梦龙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卒于清世祖顺治三年(1574-1646),苏州府吴县人。
李昭鸿比较《古今谭概》和《笑府》二书的选录标准,指出冯梦龙对雅俗笑话分判的原则及意涵,《笑府》从社会民情寻找可乐之事,自然不乏吴语吴俗之记载;[15]“找戏”必然是当时习见的口语,然从笑话的上下文推敲,似乎不能以现代汉语理解为“寻找的戏”,本小节试析究之。
“找戏”一词亦见于两本明清的白话小说,有助于厘清其义蕴。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梼杌闲评》[16]出现了两次:
吴益之道:“今日戏做得好。”王公子道:“只是难为云卿了,一本总是旦曲,后找的三出又是长的。”吴益之道:“也罢了,今日有五六两银子赏钱,多做几出也不为过。”……吴益之道:“后头找戏可是大娘点的?”小厮不言语,只把眼望着公子,公子道:“但说何妨。”小厮才说道:“一出是杨小娘点的;一出是大娘点的;一出是做把戏的女人点的。”吴益之拍手笑道:“我说定是这些妖精点的。”(第三回)
“到了城外,戏子已到,正戏完了,又点找戏。”(第四十三回)[17]


清刻本《梼杌闲评》
根据前后语境,“点戏”应如同今日的“点歌”,是动词加宾语的复词结构,而“找戏”应该是一个名词词组,且是“后头”、“多做”的、“正戏完了”才上演的,进一步分析,应当也属动宾结构。
《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即释意《梼杌闲评》卷四十三回的“找戏”为“加演的戏”。[18]
又可参见清人西周生所著《醒世姻缘传》,[19]第六十九回《招商店素姐投师·蒿里山希陈哭母》所述:
在厂棚里面男女各席,满满的坐定,摆酒唱戏,公同饯行。当中坐首席的点了一本《荆钗》,找了一出《月下斩貂蝉》,一出《独行千里》,方各散席回房。素姐问道:“侯师傅,刚才唱的是甚么故事?怎么钱玉莲刚从江里捞得出来,又被关老爷杀了?关老爷杀了他罢,怎么领了两个媳妇逃走?想是怕他叫偿命么?”众人都说:“正是呢。这们个好人,关老爷不保护他,倒把来杀了,可见事不公道哩。”[20]

《醒世姻缘传》的“点”和“找”都做动词用,袁世硕、邹宗良注解“找”字为“不收费用而附带演出。”(页939)“点”的是主场,“找”的是主场之后加演的折子戏。

清同治九年刊本《醒世姻缘传》
更有意思的是,《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九回与前述《笑府》笑话相似,也铺写了素姐错解前后剧情的桥段,小说以《荆钗记》为正戏,钱玉莲(旦)不愿嫁给富豪孙汝权,投江全节,最终获救并与王十朋团圆;而旦脚旋即又上场演出《月下斩貂蝉》和《独行千里》,于是素姐一如前述乡人,质疑:“怎么钱玉莲刚从江里捞得出来,又被关老爷杀了?关老爷杀了他罢,怎么领了两个媳妇逃走?”
这位上场加演“找戏”的旦脚,自然就是被斩的貂蝉,又是被千里护送的兄嫂!职是之故,同一位演员好不容易大劫归来,就被关公“所杀”,又被关公“领送”,把不谙演剧习俗的百姓都搞迷糊了,七嘴八舌的解读一番,又心满意足的一哄散去。这段情节正是化用民间流传的笑话。
小说细腻的描写大大的补充了我们对“找戏”的认知,综合上引文献,可以归纳出三点:
其一,搬演的顺序是先演正戏,再演找戏。
其二,不论是索费的正戏或免费的找戏,都是由观众来决定剧目。
其三,戏曲有分折、分出的段落概念,乃是受到明嘉靖以后南曲戏文蜕变为传奇,以及明中叶戏曲的刊印之影响,[21]因此搬演全本戏或单独演出某出是有所分别的。
“正戏”多是全本搬演,“找戏”则只演单出,如《笑府》第一则笑话以《荆钗记》第十出《逼嫁》作为“找戏”,第二则笑话的“找戏”是《关公斩貂蝉》,即《桃园记》的第一出,而《醒世姻缘传》所“找”的是《桃园记》的第一折《斩貂蝉》和第三折《独行千里》。[22]
而戏曲有一行话“饶头”或作“饶戏”,与“找戏”的概念十分雷同。

《昆曲辞典》
《戏曲行话辞典》有“饶头”一条:“指戏唱完后,要让女主角唱时调小曲。饶:另外添加。”[23]
其次,《昆曲辞典》收有“饶头戏”:“宁波昆曲表演俗语。在正戏演出前后,插演其他节目。统称‘饶头戏’。这类戏的名目繁多,形式各别,以吉祥戏为主。演出目的在于适应观众之需要,奉承主家,讨取吉利。”[24]
李静《明清堂会演剧史》主要是介绍京昆的堂会演出型态,从开场戏、正戏到最后的送客戏有一套习俗,所谓“送客戏”是用来“调节气氛,送走观众,因此又称之为‘收锣戏’。在昆剧堂会中,这类戏一般为带有滑稽色彩的对子戏或玩笑戏,用以在堂会演出结束前调笑耍乐、调节过于规矩的礼仪氛围。”[25]
综上所述,名称上或有不同,但就戏班演出之惯例,“安可”加演一来可让演员答谢观众的热情,二来可释放观众澎湃亢奋的情绪,为每一次的演出划下完美的句点。笑话和小说的记载,使我们了解明代之“找戏”,即与今日的“饶戏”、“送客戏”异名同实。

《明清堂会演剧史》
并列观察正戏、饶戏、点戏、找戏这四个戏曲行话,可发现属于偏正结构的“正戏/饶戏”,仍存留在现代汉语的词频之中,而“点戏/找戏”则形成另一组与之呼应的动宾复词。
前文引述的两本小说,将“点戏/找戏”的动词运用的十分灵活,对照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点选”之意的“点菜”、“点歌”尚且通行;而“找”这个动词,则需要从“寻找”引伸到“找到”、“找来”,才能推扩到“多出来”、“多加上”的用法。



本文以《笑府》两则《看戏》笑话为核心,辅以戏曲史相关背景为佐证。要读懂古人的笑话并不容易,合此三则笑话为例,虽然不到百余字,但牵涉到各出戏的剧情大意,正戏与找戏的演剧习俗,以及腔调剧种崛起,台本改动墨本的情节,形成各地演出内容五花八门等诸多有趣的戏曲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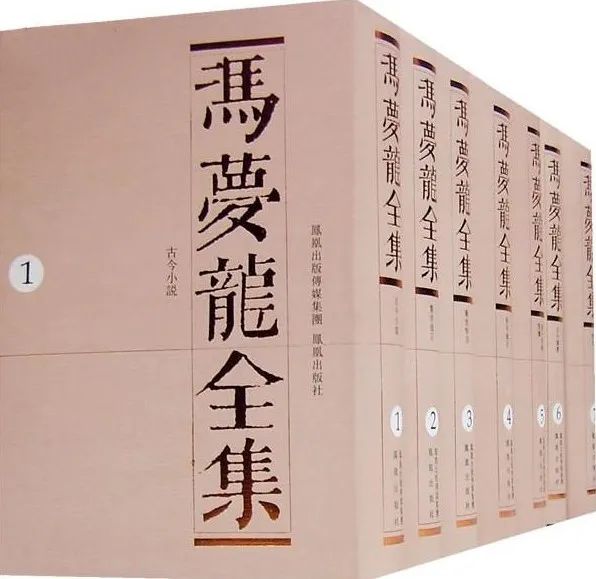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版《冯梦龙全集》
冯梦龙所使用的“找戏”一词,应是明清的吴地俗语,竹君校点的《笑府附广笑府》并未注解说明,且鲜少见于其他戏曲文献;《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解释“找戏”意为“加演的戏”,本文参见两本明清小说《梼杌闲评》和《醒世姻缘传》之叙述,考证明清“找戏”之演剧习俗,即与今日的戏曲行话“饶戏”意义相同。
注释:
[1] 〔明〕冯梦龙:《笑府》,收于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161。〔明〕冯梦龙编纂,竹君校点:《笑府附广笑府》(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页101。
[2] 〔明〕冯梦龙《笑府》:“或款乡下亲家,而演《琵琶记》者,既十余出,乡人谓其无杀阵也,怒见声色。主家阴嘱优使为之,战甚酣,乡人大喜,顾主翁曰:这才是,我不说也罢,只道我不在行了。(冯注:行,音杭)(冯评:)曾见弋阳腔搬《伯喈》里正妻与赵五娘跌打,则相杀亦未足奇。”(总页178-179)又〔明〕冯梦龙编纂,竹君校点:《笑府附广笑府》,页111-112。此则笑话写乡人爱看闹腾场面,主家为了迎合亲家所好,令优人加入武场,战况激烈,宾主尽欢。乡人自得之余,更炫耀自己对戏曲甚为在行。如是传达了常民之观剧品味,无论剧本为何,民间艺人可随时顺从民意,增添打斗的戏份。以《琵琶记》而言有42出,一个晚上决计无法演完,倘若又没有冷热排场之调剂,升斗小民难免会觉得沉闷,是以戏曲的“台本”面貌多样,完全是为了服务观众。冯梦龙所录笑话,及其评语“曾见弋阳腔搬《伯喈》里正妻与赵五娘跌打,则相杀亦未足奇”,正是呼应了明代南戏四大声腔崛起,形成海盐腔、昆山腔一路雅化的腔调剧种,和余姚腔、弋阳腔的俚俗路线,乱添枝节,滥改剧本,见怪不怪。
[3] 〔明〕冯梦龙:《笑府》,页177-178。〔明〕冯梦龙编纂,竹君校点:《笑府附广笑府》,页111。
[4] 〔明〕柯丹邱:《荆钗记》,收入〔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据上海开明书店原版重印),第十出《逼嫁》,页27-31。
[5] 同前注。〔清〕游戏主人纂辑,〔清〕粲然居士参订,廖东校点:《笑林广记》(济南:齐鲁书社,2003),卷五《殊禀部》收“看戏”、“演戏”两则,与引文文字完全一样,不再赘引,页102。
[6] 洪淑苓:《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台北:台大出版委员会,1995),页97、105。〔明〕徐文昭编:《风月锦囊》,收于《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第1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1月,据明嘉靖癸丑(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本影印),“貂蝉见关羽”、“夜读春秋”、“关羽问貂蝉”“貂蝉夸关张”、“关羽斩貂蝉”,页426-429。〔明〕徐文昭编,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591-596。〔明〕胡文焕编:《群音类选》,收于《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第2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据明万历文会堂所辑刻“格致丛书”之一种影印),卷12,《桃园记》第一折《关斩貂蝉》,页550-554。洪氏:“这两本剧作的布局情节大体相仿:关公月下读《春秋》,感叹吕布一世英雄却毁于貂蝉之手,此时刻意妆扮走出闺房的貂挥,曲意讨好关公,盛赞其桃园三结义,并贬责吕布弄权,不料却惹恼了关公,反被斩首。”(页106)
[7] 洪淑苓:《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页106。
[8] 〔明〕许自昌:《樗斋漫录》,《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卷3,页17,总页77。
[9] 〔明末清初〕金堡《徧行堂集》,收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据清乾隆五年刻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页10,总页222。1620年金堡参与抗清失败,出家为僧,法号澹归、今释,参见〔明〕今释说,今辩重编:《丹霞澹归禅师语录》,收入《明版嘉兴大藏经》第38册(台北:新文丰书局,1987),编号第409部经书,卷一,页9-10,总页284-285。
[10] 关于《荆钗记》的作者问题,笔者采用俞为民:《南戏〈荆钗记〉考论》的考证,见《宋元南戏考论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9-191。
[11]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页188。
[12] 裴喆:《明曲家诸葛味水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2010年9月),页91-94。
[13] 参见黄庆声:《解颐编:中国古代笑话专题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第一章《弁言》,页1-33。
[14] 本节承蒙匿名审查提供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15] 李昭鸿:《从〈笑府〉、〈古今谭概〉的选录标准论冯梦龙对雅俗笑话分判的原则及意涵》,《真理大学人文学报》第13期(2012年10月),页1-26。
[16] 考察陈大道《梼杌闲评硏究──魏忠贤时事小说》之作者、成书时间和刊本时间等问题,同意《清史稿》总纂缪筌孙提出“《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一说,陈大道认为“作者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其次,确切成书时间不详,但从“书中同时出现了清人立场与明人口吻”,是以陈大道“揣测此乃明末清初的作品”;而目前所见最早刊行本“为康熙年间(1661-1722)出版”。陈大道:《梼杌闲评硏究──魏忠贤时事小说》(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页41-55。
[17] 《梼杌闲评全传》,《古本小说集成》第2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淸刊本影印),第三回页3-4、第四十三回页2,总页78-79、1436。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中国小说史料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页26-27、480。
[18] 吴士勋、王东明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页1266。
[19] 关于《醒世姻缘》的作者生平、成书时间颇有争议,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考证为崇祯十二到十七年间(1639-1644),(长沙:岳麓书社,2003),页70;夏薇《〈醒世姻缘传〉研究》推论成书上限是雍正四年,下限是乾隆五十七年(1726-1792)(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34。本文采用后说。
[20] 〔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古本小说集成》第3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版,据同德堂刊本影印),第六十九回页9,总页1885-1886。〔清〕西周生辑著;袁世硕、邹宗良校注:《醒世姻缘传》(台北:三民书局,2000),页939-940。
[21] 曾永义《宋元南戏体制规律的渊源与形成》曾谓:“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原来都不分出(齣)也不分折(摺),前者如最早的抄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陆贻典影钞本《琵琶记》、后者如最早的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都是如此。”又指出:“齣”固不见于字书,其本字应作“出”;“”字太生,未见其例;“折”与“摺”音同义近。明中叶以后刻本,“出”、“齣”、“折”、“摺”四字皆可应用。……齣最后取代“出”、“折”、“摺”而定于一尊,盖在明嘉靖以后南曲戏文蜕变为传奇之后。氏著:《戏曲源流新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11-212。
[22] 可参见〔明〕胡文焕编:《群音类选》,收于《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第2册,卷12,《桃园记》第一折《关斩貂蝉》、第二折《五夜秉烛》、第三折《独行千里》、第四折《古城聚会》,页550-560。
[23] 蔡敦勇编著:《戏曲行话辞典》(台北:国家出版社,2012),页699-700。
[24] 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页1076-1077。
[25] 李静:《明清堂会演剧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