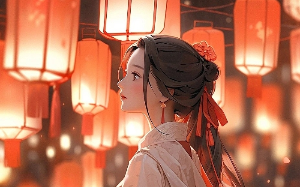我再次见到纪濡时,他全身佝偻着缩在角落里,头发和衣衫上全是污渍。
每走近一步,他的叫喊声越发大,充斥着强烈的恐惧、不安、惧怕。
“你是纪大才子?”我迟疑问。
像是触发到什么机关一般,他开口,声音不似常人。
“不,不是。我不是什么才子。滚!滚出去!”
我呼出一口气,至此才相信,连中三甲的状元郎纪濡是真的疯了。
1
我是在破城后的一件地牢里找到的纪濡。
他手脚都锁着链子,能活动的地方不足半尺。
披头散发比街上的乞丐更不堪。
我走过去,托起他的下巴看着面容姣好的那张脸。
是的,即便在这种境遇下,这张脸依旧如十年前那样动人。
我嗤笑一声:“纪濡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原是我心仪之人,是我的未婚夫,也是众人眼中可望不可求的良配。
我不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变成这样。
当年睥睨众人掷果盈车的才子变成现如今这样,不人不鬼。
他蜷缩在我的脚底,手指想触碰,又不敢。
声音沙哑地问:“容容,我不想当人了,让我当你的狗吧。”
2
我和纪濡是青梅竹马。
他是国舅爷的独子,本可以做个闲散公子爷,一生无忧无虑。
偏偏学着玩的书经给他学出了模样,成了风头无两的状元郎。
被封翰林院的那一天,朝中两大势力向他抛出橄榄枝,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招婿。
可令人着实吃惊的是,他谁也没娶,全都拒了。
是时,我还是冷宫中一个不受宠的公主。
还是十来岁孩子的我会甜甜的叫他“纪哥哥。”
“等我长大了,你来娶我好不好?”
不曾想,我有机会长大,却没等到纪濡的聘礼。
3
纪濡被我安置在内室。
我的幕僚谋士纷纷表示不妥。
“殿下,您不能留一个罪人在您殿里。陛下,天下人该怎么看您?”
岑虑跪在面前,声嘶力竭地劝告。
“我不过捡到一条丧家之犬罢了,岑卿言重了。”
朝局不稳,五年前,原本要继承皇位的太子突然发疯冲进三四皇子的殿中,将尚在昏睡的皇子赐死,随后自杀。
天亮时,血浸了满殿,皇城中哭声经久不衰。
朝中只剩一位堪堪弱冠的二皇子,以及唯一的公主。
二皇子先天不足,是个药罐子,从小到大吃过的药比饭还多,一副随手就要撒手人寰的样子。
朝臣的目光一直在我和二皇子中逡巡。
像是我们之中稍稍犯点错,在他们的心中的份量就少一分似的。
我懒得计较这一星半点的份量,悄悄联系了军营中的同窗好友岑虑。
不为其他,只想在二皇子继位时留条性命,回封地做个逍遥长公主。
4
纪濡半点东西都吃不下去。
只是简单的糖水都会吐到昏厥。
我烦不胜烦,好不容易救回来的人居然会饿死在我殿里。
医师说这是心病,怕是不好治,只能徐徐图之。
我却没耐心,将一碗参汤灌进他的喉咙里。
“敢吐出来,我阉了你”
然而半柱香后,东西怎么进去的还是原样吐了出来。
小厮胡祥左右为难问:“殿下,真阉啊?”
我着人去问纪濡的情况。
才知道自从他被送去匈奴,日日都是与猪马同睡。
不能直立行走,每日戴着链子供人观赏。
匈奴人并没有将他当人看。
本也是作为敌方的战败品掳过来的,自然没有好待遇。
我轻抚着他削瘦的脸,他眼睛紧紧闭着,像是陷入某种噩梦当中。
5
下朝后,丞相张则拦住了我的去路。
“殿下,江南水患二皇子因身子不适不能前行,殿下为何不请令前去?”
我稍稍挑眉。
“张丞相不是一贯主张立长的吗?虽然我二皇兄去不了,这风头又怎么能被我抢了?”
张则被此话气得吹胡子瞪眼。
“水灾是民生大事,殿下怎么能淡然处之,毕竟不为那个位子,也该为受苦受难的百姓尽一份力。”
我摆了摆手,“我不是举荐了今年的榜眼朱青前去吗?那既是他家乡,师长也是专修水利的。”
“你是因为新得的那个的男宠所以才不远行?糊涂啊!”
七十多岁的老人哀叹一声。
6
我不去治理水患,一方面自然是避嫌不去,另一方面则是父皇近日身子有些状况,我怎么能让皇兄独自留在皇城。
刚回到府就听见一声怒斥:“滚!”
声音虽有气势但却十分低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猫。
胡祥迎上来。
“殿下,公子不让人进去,已经两个时辰了,这......”
我摆了摆手,撩起裙摆走进去。
里面一片昏暗,帷幕拉得死死的,自窗沿缝隙中透过几缕光看见石砖地上一个朦胧的人影。
我看着不远处的床榻,轻轻叹了口气。
“纪濡,你要糟蹋自己到几时?”
我想将人拉起来,男人却抗拒地避开我的手。
“不,放开我,走开,滚!”
他手足舞动着,我拽住他一只胳膊将人拉到榻上,手心托着他的脸说:“我是穆容,你不记得了吗?”
“穆容?不,你不是......穆容怎么会在这?!”
他声音颤抖,前臂捂住自己的脸,像是堪于见人,另一只手臂却死死抓着我的衣角。
我使了些劲拉下他的手,男人的眼角已有了些湿意。
“我是穆容......”
话还未说完,男人突然放声大叫起来,身形不停地往后退。
“你不是,你们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他头颅后仰,露出青筋暴起的一段白皙脖颈。
我一手环住他,使他不得逃脱。
他害怕到了极致,叫声越发凄厉,双目圆瞪,背脊向后弯曲像是要折断一般。
终于沙哑的叫声戛然而止,男人软在我怀里。
7
纪濡真得了失心疯,说是认不得人了,记不清事。
他的脸色是常年不见光的白,眼下发青,唇色暗淡。
眼睛紧紧闭着,连睡梦中都皱着眉,似乎在忍受什么极大的痛苦一般。
给他盖好被子,我坐在榻边愣神。
胡祥缓步走进来,微一躬身。
“殿下,该起身了,不然宫宴该迟了。”
卢州一战大胜,班师回朝后皇帝摆了庆功宴。
我略一颔首,吩咐说:“好生照顾他。”
席上觥筹交错,我本是一介女子,本是没有资格争那个位置,但三年前那件事后,我请命前往边疆,花了近三年时间大破匈奴两地,将外姓人赶出了故土,这才摸到了继承人的边线。
“朕听说寻到了纪濡。”
酒过三巡,尊位上那位发了话。
阉党大太监服侍左右,闻言恭敬上前接话:“是,容公主着人带了回去,陛下是要召人见见吗?”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我身上。
我上前行礼。
“是,不过纪濡身染重病,臣本想着待他好些再带过来面圣。”
人群里有人嗤笑。
“一个罪臣还给治什么病?活该千刀万剐的下贱民。”
听到这,不知怎么的,父皇的脸色沉了一分。
“闭嘴。”
他怒斥一声。
我有些愣住,三年前,纪谦谋反,锦衣卫镇压赐了凌迟之醉,纪家三十余口皆被贬为娼妓。
纪濡本该流放,正遇上匈奴来袭,连破十城,签下丧国辱权之约,并在最后谈判时加上了纪濡的名字。
匈奴王要了安国风头正盛的状元郎,不为其他,仅仅只是为了让父皇不痛快罢了。
有什么比羞辱安国不世而出的才子更打安国的脸呢?
至于纪濡,从天之娇子到阶下囚,甚至他国玩物,也不过一月之事,当真半点不由人。
8
我到府时,纪濡正在内室昏睡,帷幕拉得紧紧的,半点不见日光。
他眼睛紧紧闭着,神情慌乱得不行,像是陷在某种噩梦中。
医师说他中了毒瘾,对神智有损,需得慢慢戒。
我脱了鞋,掀开一小块被子钻进去。
那人的手试探性地触摸我的肌肤,随后像是八爪鱼似的缠在我身上。
阳光透过缝隙一点点照射进来。
我轻轻抚过趴在我身上,头靠在我颈窝的男人的后脑勺。
“没睡着?还是醒了。”
“你怎么知道?”
他转过头去寻我的眸子。
我摸了摸他的脸 ,“呼吸平稳了很多。”
只一瞬,他顿了顿说:“你不该留我,我是个祸害。”
许久没和他如此平静地聊过天,我不想破坏这样的好气氛。
“饿不饿?想吃东西吗?”
我静静问他。
纪濡摇了摇头。
“你把我扔出去。”
我笑了一声,点点他搂着我青筋毕现的手。
“你抓得这么紧,我怎么扔?”
他挣扎了一番仍旧舍不得放手。
我环住他的腰,将他抱了起来。
他紧紧环住我的脖子。
“轻点,还有你太瘦了,好轻。”
他贴着我的脸似哭非笑地说:“让我死在你怀里吧。”
我压着他的后颈,在他耳边近乎缱绻地说:“你不想当人了,那就当我的情夫,当我的帐中鬼,什么都行。但我不准你死。”
他小声地啜泣起来。
9
我赶到丞相府时,纪濡的尖叫声生生拔高了一个度。
随后骤然断开,昏死过去。
他双臂吊着浑身赤裸,我的侍卫和丞相府的侍卫黑压压围成一个圈。
我脱下披风,砍断绑着他手腕的绳索。
“张则,这事咱们没完!”
他高热久久不退,陷入昏迷中。
我不敢离开他身边,贴身照顾着。
刚给他哺过一口粥,他就醒了。
墨色的眸子中还有几丝迷茫,看见我才亮了亮。
细长的手骨拽住我的手腕。
“张则......张则是二皇子那边的......是......”
我将食指贴在他唇上。
“别说话,好好修养。有我呢。”
我贴着他的额头,心碎得不行。
“我的事可以好好利用一番,我虽是罪人,但他们当众处私刑,于礼于法不合。”
我抱着他,气得牙痒痒的。
“你怎么会是罪人?我已请旨迎你为驸马,他们敢当众这样对我的人,是真当我好欺负吗?”
纪濡一阵呛咳:“不,我不当驸马.....不......我不配......”
他情绪越发激动,眼看着不支过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抚过他心口:“好,你别急。你不想当便不当了。”
10
父皇着人宣布了治理水灾的人选。
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纪濡。
他一身青袍跪在地上谢恩。
从袖袍中伸出瘦得脱相的腕骨骨节凸出。
我说要一同去,他终于笑了笑。
“你糊涂了?皇上还在病中,此时你怎能离京?”
他搭着我的手起身,一副病骨支离的样子。
“我去去就回,你在京中等我。”
“为什么?”
纪濡垂下眸子,“我总得证明自己还有些用处,配得上惊才艳艳的公主。”
我心肝胆颤,他本就体弱,水患之乡易生疫,他怎么受得住。
“名动一时的才子,怎么不配?”
他犹豫一瞬,像是鼓起勇气般印上我的唇。
“别怕,我会好好地回来。”
他已病得不能行走,被两个小太监架着上了马车。
我看着远走的马车,心一点点吊了起来。
小厮胡祥弓着身子问:“殿下,都安排好了,现在就去吗?”
我点了点头,随着胡祥带路到了二哥府上。
二哥自小重病缠身,养得矜贵,此时正在院中晒太阳。
我越过屏风,看着我握瑾怀瑜的哥哥。
谁也想不到他清风朗月的外表下是一副蛇蝎心肠。
“纪濡走了?”
他声音微弱,像是不久于人世,但却实实在在挺了二十来年。
“二哥,此间只有你我二人,何必再装?”
我对他这样一副要死不断气的样子厌烦得不行。
只见那人轻笑一声,从椅上起来,撩过帘子出了内室。
“二哥装得不像吗?朝中上上下下都被二哥骗过去了。”
大冬天的,他附庸风雅手上拿把扇子,轻轻点在我的鼻尖。
“太子都被你斗下去了,你还使这些手段做甚?难道真怕我抢了你的皇位,要等我死了后才露出你的青面獠牙?”
我这二哥虚伪得可怕,明明心里想那个位置想得发狂,面上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看着实在让人作呕。
“不把弱点暴露出来,怎么引背后那些莺莺燕燕登场?”
撑开的扇面掩住他的半张脸,狐狸般狡黠的双眼露出来,说不出的诡异。
“你想如何我不管,张则我要了。”
“呵,纪濡当真是你的心尖,七日前你还在拉拢丞相,不足半月,你就想要他的命。”
“我不会让人欺辱到我头上,一些小利让便让了,动我的人是当我死了吗?”
11
我退出殿外,见一名女子立在门边,身边带着一个托着吃食的婢女。
女子朝我福了福。
我回了个礼。
“许久不见,嫂嫂又丰腴了些。可见二哥待你确实不错。”
女子芙蓉面,窈窕身姿。赛若西子的面容上有一瞬间的凝滞。
随即眉目舒缓,弯眼笑了笑:“多谢公主,若非公主,不会有星瑶此日。”
纪星瑶是纪濡的堂妹,五年前那场谋反案中纪星瑶原本是要被塞入军中沦为军妓。
被我救了下来,安了个名目说是去军中的途中病逝,实则化名送进二皇子府中。
“当初送你过来,不知道是对你好,还是害了你。”
我轻声说。
纪星瑶手指缓缓划过腹部,目光中散发着慈爱的光芒。
“殿下言重了,当初是我选择进府,若是我不愿,即便一条白绫吊死,您又能奈何。况且我已怀了二殿下的孩子。”
我心猛地一跳,稳下情绪说:“如此,恭喜二哥二嫂了。”
说完,我刚要退下,又被叫住。
纪星瑶捏着手绢,抵住唇口,面目沾染些许哀愁:“殿下,我堂哥,他还好吗?”
算来两人已经整整五年未见一面。
“陛下刚派了他去治理水患,回来后必定是要给个官职的。”
闻言,女人眸中有片刻欢喜,朝我深深一拜。
“殿下救我兄妹二人,如此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我匆匆离开,出了府门,立即让人往宫里递了消息。
若纪星瑶腹中胎儿是个皇子,那将会是父皇的第一个皇孙。
我的筹码就失了一分。
不能再拖下去了!
12
张则处刑的那天,我乔装打扮在刑场正对的酒楼上小酌。
“世人都说四公主胸襟若海,不拘小节,由此看来,世人皆看走了眼。”
岑虑坐在一旁冷不丁地刺一句。
丞相一党的衰败自从书房的下人发现一封谋反信开始。
信是写给太子的,说他是血脉正统,是要继承大统的人。
父皇拿到信后,问也不曾问一句,直接着人将其下狱。
五年前那桩谋反案一直是父皇心中的一根刺。
刑场上头发花白的老人还在不住地哭诉喊冤。
“天纲伦常是为正统,太子冤啊!”
我冷笑一声,太子确实冤,可张则却一点也不冤枉。
他绑纪濡并不如他口中说的那样冠冕堂皇,为了我和二皇子不起纠纷。
而是为了泄愤。
那桩谋逆案源于太子常年流连花坊柳巷,错将当时微服游玩的小郡主带回宫中,一夜风流。
醒后,小郡主上告到了父皇那,朝野震惊。
父皇勒令太子禁足。
百般慌乱中,头上悬着一把即将被废的刀,太子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杀掉所有其他皇位继承人。
但是太子太慌了,他没看清他身边躺着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当朝的小郡主。
这本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嫁祸,但在太子动刀后成了一桩尘埃落定的罪名。
而纪濡是这场罪名中最最紧要的人。
这场祸事本烧不到纪家的身上,但恰巧那日纪濡入宫来见我,见三皇子宫门渗血,目睹了这桩惨烈事。
他成了大殿上亲口指认自己的堂兄杀亲的罪证。
即使他在堂上未着一言,身边的小厮已为他说尽一切。
此后他在纪家门楣中也人人喊打了。
13
“天道不公,忠义误我啊!!!”
话音未落,刽子手手起刀落砍下了人头。
听到这句叫喊声的我笑得呛了酒。
好个忠义误我。
在纪家获罪的那天,我在父皇殿外整整跪了一夜。
可那零星的父女情换不回纪濡的命。
酒饮尽,我起身回府,用了晚膳后宽衣入睡,不知怎么的,梦到些陈年旧事。
梦里太子哥哥和印象中别无二致。
我那时才十一岁左右,因为小时营养不好,总是面黄肌瘦的。
太子哥哥的脸上染了血,眸中有化不开的癫狂之色。
“容姐儿,哥哥给你扫清障碍,你还给哥哥一个清平盛世好不好?”
他衣衫上有深色暗渍,袖口处被刀剑划破道口,右脸上一道血痕,连玉冠都是歪的。
“那些人不让你太子哥哥活,我便拉着他们一起死!但咱们容姐儿是不一样的,咱们容姐儿是有福之人......”
他的面容越发可怖,目光停在虚无某处,眼角泛出一抹血色,凶恶得竟像是要将虚空中的某个人削皮拔骨似的。
我猛然惊醒,随即小厮推门而入带来纪濡回京的消息。
我起身披衣刚踏进门槛,胡祥迎过来。
“殿下,纪廷尉到了。”
“旨意这么快就下来了?廷尉?”
说着便进门。
心心念念的人坐在主座上。
不过两月余,在我这养的一点肉丝毫不剩地还了回去。
人瘦得几乎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见到我的身影,纪濡的眼睛亮了亮,起身走了两步,没了力气,眼瞅着要摔倒,被我踏踏实实接住了。
“回来得好早!纪廷尉着实心疼我。”
纪濡勉强笑了笑,神色肉眼可见地沉下去。
“容容,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心中一顿,近日里京城中冒出许多传闻。
说是纪濡在边塞被匈奴人一边又一边地玩弄,卑躬屈膝,极尽不齿之事才能忍到如今回来。
且在边塞时匈奴人首领的女儿十分宠信他,时时带在身边,金银珠宝享之不尽。
“你是因为这事才加快了进度,日夜不分赶回来的?”
我五指并拢轻轻捋顺他的发丝。
纪濡闭着眼将下巴搭在我的肩上。
“不……我很想你,但也怕……”
我嗤笑一声,抬起他的下巴:“怕什么?”
拢在我腰上的手紧了紧:“怕你不要我……”
我点了点他的唇:“所以那些谣言几分真几分假。”
纪濡的脸色白了一层,和刚暴毙的死人没什么两样。
他声音不可抑制地颤抖:“我没有……我的身子还是干净的。”
我挣开他的手,扶着他上了榻。
“我信,所以软玉为什么放过你?”
我是在一所王府中找到的纪濡,女真人为他所建的王府。
他就那样直挺挺地躺在一间陋室里,像是躲着破城而入的军兵,又像是在等期待已久的死亡。
他凄凉一笑:“软玉不知道你真的会亲身来前线,你可是金尊玉贵的公主殿下,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本不该是我,只是当时我已被皇权压得喘不过气来,自请去边疆打战。
即便如此,父皇依旧怀疑我狼子野心,不仅兵不肯让我多带兵,还隐瞒了我的身份,对外只说是一位不受宠的王爷。
我点点头,恰好胡祥送来一碗药。
纪濡看了看黑糊糊的药碗,没问什么,仰头吞了下去。
“不怕我下毒?”我起心思调戏他。
他定定地看着我:“你就算下鹤顶红,我都喝。”
我看着他的眸子越发幽深,竟再说不出什么。
“连日赶车,应是累坏了,闭眼休息会吧。”
他恋念地去蹭我的手。
“你陪我,好不好。”
我钻进被窝,他紧紧贴过来,眼角落下一滴泪。
和我在一起时,他总是哭,像是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都一一数尽似的。
“陛下赐了我宅子,明日得住过去。”
我摸着他凸出的脊骨,问:“舍不得?”
纪濡将头埋在我的颈窝里:“晚上我来你这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