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就是乌台诗案。
前期,他是一个天之骄子,后期他是一个从低谷中不断攀爬的农民,渔夫,美食家。

乌台诗案后,44岁的苏轼戴着枷锁从汴京城走向黄州。昔日的锦绣文章成了罪证,俸禄断绝,全家挤在破庙。
幸好有好友的接济,他在湖北黄州城城东荒坡开垦五十亩地,取名东坡,坦然写下“去年东坡拾瓦砾,今年刈草盖雪堂”。
逃过生死,他把时间都放在了农事耕作上。每日五更起床耕种,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节奏重建秩序。

甚至开始发掘生活的乐趣。发明东坡肉时给友人写信:“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似乎一切都在好转。
不成想,59岁再贬岭南,陪伴自己很久的侍妾朝云病逝,生活中少了安稳,又多了几分孤苦。
年纪越来越大,他与疾病和解:“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中不见悲苦,反有“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诙谐给惠州白鹤峰新居写《纵笔》:“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让流放地变成诗意栖居。

62岁流放儋州,在黎族村落办学堂,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与渔民同船出海,记录“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的海岛风物。在桄榔林中建“载酒堂”,让中原文明在天涯海角开花结果。
苏轼年少苏轼年少成名,但是却一生经历坎坷。
他在黄州城躬身农耕,在岭南丧失了最后一生的伴侣,但是却能够在儋州写下兹游奇绝冠平生。

他似乎整个后半生都在低谷当中,但是在这低谷的半生当中,却维持了他的生命,延长了他文学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吟诵“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今天才能够闻到东坡肉的香气,我们今天才能够品尝到荔枝的味道,才能够感受到”大江东去”的干嘛,懂得“地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旷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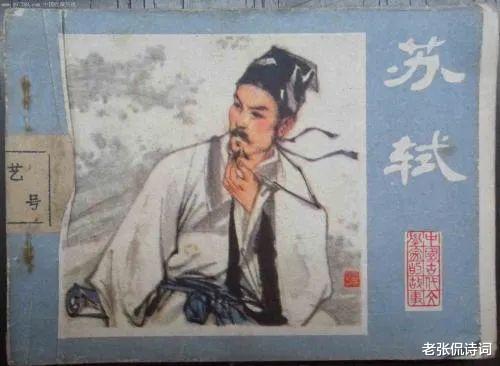
正如林语堂在序言中所写:“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愿你也能带上这份跨越千年的“东坡式松弛感”,在各自的时代洪流中,活成自己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