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我写了《封神1》的影评,以批评为主。
上个月,我另写了篇文章,专门谈了谈《封神1》在置景和服化道方面的亮色。
一部电影可以“又骂又夸”吗?
当然可以,其实这才是该有的态度。因为任何电影都不会是“完美无瑕”或“一无是处”的,它总有缺点,也总能找着优点,无非一个主次占比问题。我夸《封神1》的置景和服装,你要知道:它的美术指导可是叶锦添。
那为什么要先谈缺点再说优点呢?
因为总体上,《封神1》就是个6分水准。我在第一篇文章里指出:影片的主题、人物、剧情、特效......各个方面都存在瑕疵。也就是从“大面儿”上看,该片绝对难称佳作。
它的优点集中在一些“边角料”的历史细节方面,就是第二篇文章中提到的3000前中原的气温突变(“天谴”)、商周不同城市景观及服饰、甲骨占卜、青铜大面具(参照古蜀国)......诸如此类的小地方上——而这部分内容需要大量电影截图来作支撑,我只有等上映过后、资源出来才好去讲。

好,闲话说完,今天来讲《封神2》。
这部续集被喷惨了。可在我眼中,它的成色其实和《封神1》差不多,就连犯的毛病都一样:还是在主题、人物、剧情、特效......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明明同一水平线的东西,怎么就一部被奉为佳作、一部被骂成这样,对此我只能说:还是豆瓣“厉害”。
鉴于这种情况,如果我还像第一篇文章批《封神1》一样把《封神2》面面俱到地再批一遍,把1年前说过的话换个花样再说一遍就会显得很没意思。这样吧:既然全片的最大争议来自片中的人物形象,那我就从形象入手,重点谈谈片中的人物塑造问题。正好上篇写《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文章也是以此为切入点。
先从主角讲起。
1、邓婵玉
那尔那茜的邓婵玉形象和原著存在较大差距:
“一瓣红蕖挑宝镫,更现得金莲窄窄;两湾翠黛拂秋波,越觉得玉溜沉沉。娇姿袅娜,慵拈针指好轮刀;玉手菁葱,懒傍妆台骑劣马。桃脸通红,羞答答通名问姓;玉粳微狠,娇怯怯夺利争名......”(第五十三回《邓九公奉敕西征》)
想不到吧,原著中的邓婵玉是个三寸金莲的美女(作者许仲琳毕竟是个明朝人么)。

所以乌尔善将邓婵玉“羞答答”、“娇怯怯”的红粉佳人形象改造成飒爽英姿、独当一面的女将军就对了。这跟他改造“红颜祸水”、“妖女亡国”的妲己形象是一个思路。毕竟21世纪了,真按原著拍,再让邓婵玉嫁给土行孙,不得被广大女权主义者骂死。
但即便是那尔那茜的新人设,其实跟“女权”也没什么关系。她“愿承先父遗志”、“请为大王讨伐反贼”——看见没,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活在“父权”+“君权”的双重禁锢下,典型的儒家“君父”思维么,只是后来才觉醒。

可问题就出在“觉醒”:邓婵玉的“觉醒”依然是她爸(邓九公)教的——“真正的军人不杀平民百姓”这一人生信条依然秉承于“父”而不是源自内心的自我发现,这就叫人难受了。
还有,一部电影的主角,其核心任务与核心目标最好是不要变,否则就会令人困惑。邓婵玉在电影前半场的核心任务一直是“战死沙场”、“为大商再立功勋”;可到了电影后半程她的核心任务突然变成了:守护人民生命。从一心想当战争英雄到自愿成为“人民守护者”,这其实是两个目标、两个任务,甚至还隐隐存在冲突,可乌尔善就这么丝滑地在同一个人身上让一个置换了另一个。
对邓婵玉来说:“为大商而战”是她爸要求她做的、“守护人民”也是她爸要求她做的(“我邓家何尝杀过平民百姓?”),当这两件事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为何就能毫不犹豫地放弃前者、选择后者而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我在看到邓婵玉中途叛逃时的最大困惑。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乌尔善的叙事诡计。邓婵玉并非真的叛变,她只是为了混进周营活捉姜子牙、拿到封神榜。但问题依然没有消失:邓婵玉之所以愿去拿封神榜,是因为闻仲骗她拿到之后就可以放过西岐百姓——可见在邓婵玉心中,百姓的生命就是比军人的天职重要。所以当她知道闻仲在骗她、屠城仍会进行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封神榜扔还给姜子牙并在姬发赶到后和其并肩作战。这个角色的每一次转变都太突然了,因为乌尔善为其设计的人物弧光是“反复无常”的:
1、她是军人(与姬发的数场英勇战斗)——2、她不是军人,是人民守护者(所以带姬发叛归西岐)——3、她不是人民守护者,还是个服从命令的军人(欺骗姬发、活捉姜子牙)——4、她原来真的不是军人,而是人民守护者(“对不起,姬发,我欺骗了你...”)
这种行动上的频繁“横跳”却不深挖其内心的做法让人难受。如果邓婵玉自己的“本性”都被刻画的颠三倒四,还怎么拍清她和姬发之间的感情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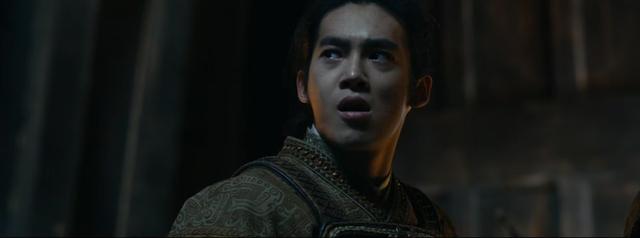
“还能再为我唱一次你初见我时唱的那首歌吗?”——当邓婵玉说出这句话时很多人感到突兀是因为它的含义很含混:这表明邓婵玉知道姬发喜欢自己还是说她此刻也有点喜欢上了姬发?
这俩人之间到底什么感情?隐而不发、彼此压抑的爱情?因具备相同理念(都极为看重平民生命)而惺惺相惜的友情?还是什么?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乌尔善压根没拍清。电影先前二人之间那点儿可怜文戏(还不如打戏多)压根撑不起结尾想要煽情的这一幕。

——因为只有拍出这俩人心照不宣的情感羁绊足够深、邓婵玉在姬发的心中足够重,结尾姬发因顾及邓婵玉生命而迟迟不愿对闻仲下手这才说得通、才足够动人。否则这一“感人场景”就废了。
“救一人还是救天下”本是个很动人、很人性的两难题目——如果这个人对你足够重要的话。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出来邓婵玉对姬发究竟怎么重要了。姬发前一秒激动地打了她一巴掌,只能理解为:他愤怒于邓婵玉对自己好心收留她的背叛,而“好心收留”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爱心而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吧!
不管乌尔善到底想拍出怎样的人物关系,可他实际呈现出的只是:姬发一开始对邓婵玉颇有好感(好奇),在被她救走后对其生出了基于大义的同情心(“是她救了我,你们不能就让邓将军这么离开,她已经无家可归了!”);而邓婵玉也被姬发“牺牲自己以换西岐百姓活命”的大义所动容,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仅此而已罢!
可这种彼此仅仅出于“大义”的“交情”不是源自灵魂深处的爱慕之情,它在西岐人的全体生命面前就显得很“轻”,姬发最后犹豫挣扎着不敢动手就会很奇怪。
为什么我说乌尔善原本是想拍好这两个人的爱情呢?——因为那首被广泛指责为“辱女”的插曲《有女》,其灵感来自《诗经·召南》中的《野有死麕》,那是一首爱情诗,“有女怀春”即出于此。

用一首爱情诗搭配姬发、邓婵玉初见时的情景,乌尔善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可惜他只开了个“爱情”的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最终导致了结尾的溃败。
再来谈姬发。
2、姬发
两相比较,姬发的人物弧线反而比邓婵玉立体丰满一些——这恰恰与大众的观感相反。虽然从实际效果看,人物塑造也算失败。

第一部中的姬发面对善与恶的选择并最终选择了善,第二部他的核心任务变成了如何守护住这善、从一个战士成长为一个领袖。起初,刚刚失去父亲的姬发并不具备成为领袖的资质(而且此时众人心中的新天下共主还是殷郊),于是尚不成熟的他就会显得变幻不定、左右摇摆。
姬发的“摇摆”原因乌尔善其实拍出来了,只是这部分文戏处理得特别仓促,加上又混在大量眼花缭乱的武戏间隙,容易被人忽略。
我帮大家理一下。决定姬发如何行动的内心驱动力其实就一个:这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只有打赢才能保全西岐城一方百姓,而一旦战败百姓就完了。如果最终会输的话,那还不如早点投降,以免百姓遭殃。

因此,当姬发觉得能赢的时候,他就是战斗派;
而当他预感到要输的时候,他就是投降派。
一开始,面对殷商使臣殷破败“死你一个还是搭上整个西岐”的挑衅,西岐上下同仇敌忾,姬发的斗志被燃起。于是就有了乔装隐身、在黄河浮筏上对邓婵玉的主动出击。
可当姬发在峡谷目睹了魔礼青‘青云剑’的恐怖威力后,内心登时凉了半截。只一个魔礼青都如此难对付,这仗还怎么打。所以他随后对姜子牙表示“我想放弃西岐城,我们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

眼见姬发气馁,姜子牙立马使出了激将法:“那干脆你把我和封神榜交到朝歌,谋个一官半职吧。”“你有勇气为自己的愧疚而死,那你有勇气为西岐的百姓而活吗!”
当姬发回到西岐城后,发现城内早已全民皆兵,而城头一个老大爷的话更是打消了他内心的顾虑:“你错了!我们不是为了你才留下的。西岐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

于是姬发重新振作起来,打算继续战斗。夜袭商营、用计诛杀魔礼青后姬发信心大增,觉得胜利在望:“能杀魔礼青一个,就能杀其余三个!”
可第二日正面战场的惨败又让姬发万念俱灰。他看到:在剩余魔家三兄弟的法宝攻击下,西岐军大败亏输、死伤无数。有这样一处细节:姬发本来在护城河的水下撇开了邓婵玉,可当他浮到水面上时,看到了熊熊燃烧的城门和正疯狂进攻的商军。于是返身潜回水里去救邓婵玉——在那一刻他就打算好了向邓婵玉投降,靠牺牲自己去挽救西岐的百姓(当时殷郊还未现身,姬发不知道事情还有转机)。

直到姬发在殷商大营发现闻仲铁了心要屠城时,他才看清自己的妥协和牺牲毫无用处。之后邓婵玉带他逃回西岐,姬发见到了殷郊,自那一刻起,他再未产生过投降之念。
经我这番描述,能明白姬发的心理轨迹了吧。一来,他还不成熟;二来,他的“善变”心态取决于战局的走势。
只可惜,这些戏还是太快了,而于适的表演也太僵。所以观众反应不过来。
3、殷郊
殷郊的特效实在太差了,这个已经有太多人吐槽,就不多说了。然而,“三头六臂”和“蓝精灵”的形象是对的,原著中说:
......只见那有一石几,几上有热气腾腾,六七枚豆儿。殷郊拈一个吃了,自觉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儿不若一总吃了罢。”......不觉浑身骨头响,左边肩头上,忽冒出一只手来,殿下着慌,大惊失色。只见右边又是一只,一会儿忽长出三头六臂,把殷郊只吓得目瞪口呆,半响无语......殷郊只一会略觉神思清爽,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上下獠牙,多生一目,晃晃荡荡,来至洞前。”(第六十三回《申公豹说反殷郊》)
其实乌尔善还把殷郊做美了,起码没让他长出像雷震子一样的獠牙。但是殷郊的人物建模水平比四年前的《刺杀小说家》都差了好远。

如果将人物做成这个样子,再解释什么“殷郊的三种情绪、三种人格”就没意思了。因为愤怒、悲哀、庄严的“人格分裂”需要高明的表演+高超的特效才能让人感同身受,可很多人一看这个形象就笑场了,还哪有心思去解读呢?
不过,虽然殷郊的形象不行,寓意却还不错:这个人的悲剧色彩在于他的一切行为被仇恨驱使,可他最终却跪倒在了自己最仇恨的对象面前。
元始天尊和姜子牙提醒过他两次: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朝歌。
尤其姜子牙,当他看到殷郊无视哪吒劝告而执意杀掉已经输了的魔里海后,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那一刻姜子牙预感到: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天下共主”有失控的危险。
于是他找机会跟殷郊说了通肺腑之言:“你不要一个人去朝歌,要去就带天下人一起去。吊民伐罪,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定天下,安万民,天下共主,固当如是。”姜子牙的意思是:天下共主当以天下苍生为己念,千万不能被个人私欲(愤怒)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众生福祉而只在乎自己,人就会误入歧途。

可惜殷郊不听,他一个人跑到朝歌向殷寿复仇,结果一招被通天教主制住。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这个人是你的母亲”——通天教主的台词很讽刺:一个对强权最仇恨的人,到头来阴差阳错地成了强权最忠实的走狗。因为你的“愤怒”和“仇恨”本在强权的算计之内,拥有“通天”手段之人就等着你上钩。这表达有点意思吧?
4、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这俩人物也被吐槽得太多了,尤其通天教主,形象与原著大不符。如果是车保罗在《决战万仙阵》中的形象,我想批判的声浪会小一些(当然,那是一部大烂片)。

元始天尊被一介凡人吸干法力也是败笔。这可是“三清之首”、“天界之祖”,竟连一点儿预见未来的能力都没有,觉悟还不如手下的十二金仙:
“师尊这个人不能救啊,怨念极深之人一旦复活,将会产生无法预计的后果。”

结果元始天尊表示自己就是没法预计:“可他或许是人间的最后希望,或许也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两个“或许”......救活殷郊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元始天尊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下共主,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这“天尊”居然是个糊涂虫,押着徒弟一起碰运气......
直到事情做完才发现“或许”不对:“看来,我们闯下大祸了”!
......

我知道乌尔善是想描绘一种“怕啥来啥”,“越想避免就越发生”的希腊式宿命感,但他不该把这个糊涂虫的角色交给元始天尊这么厉害的角色完成。你交给十二金仙的任何一人,让殷郊吸干他一个人的法力,那也是个话。
现在的搞法,到了第三部,元始天尊还怎么和通天教主斗?——
一个能吸干元始天尊法力的人被通天教主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一下子制住,一声“醒”、一声“收”就让他秒跪,这通天教主的实力得比元始天尊高多少?到了第三部,谁还能打败通天教主?
我估计乌尔善绝不会安排鸿钧老祖出手,挑战通天教主的最佳人选搞不好是:姬发......就跟这部结尾一样:一堆神仙啥用没有,最后是姬发和邓婵玉两个凡人打败了闻仲、拯救了西岐。
5、魔家四将
魔家四将在片中被处理成四个有勇无谋、接近无脑的弱智,这让很多人怒不可遏。不过要我说:乌尔善想塑造的,可能就是四个弱智。首先他们连人话都不会讲,只会哼哼咿咿地发脾气(原著里可不是这样)。考虑到雷震子也没说过话,乌尔善的设定大概是:异人都不会说话。

再看以下情节:两个魔家兄弟争过峡谷而被卡住,不知道该咋办;魔礼青见宝剑丢了只知一味追赶,直到把自己追进沼泽,被姬发射中眼后惨叫一声随即被自己的青云剑插死;魔家剩余三兄弟只懂跟随邓婵玉的鼓点儿前进、进攻......
这不是四个弱智是什么?

如果非要替乌尔善“圆”一下的话大概是:原著中魔家四将和邓婵玉的父亲邓九公是平级的(魔家四将是佳梦关总兵,邓九公是三山关总兵),电影却改成了魔家四将是邓婵玉的手下。魔家四将的法宝那么厉害,如果不是弱智的话,凭什么听邓婵玉的呢?
对这四个弱智被殷郊像玩一样打死,我倒是无所谓,因为原著中的魔家四将虽有一定实力,但放在整个封神谱系也排不上号:魔家四将死于黄天化的攒心钉,而黄天化又被殷郊的落魂钟所伤,所以这么改也还行。
6、闻仲
闻仲的形象没太多可说,“为大商尽忠,纵做鹰犬又何妨”——跟原著中对大商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老臣形象大差不差。

但这个人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了。魔家四将“脑残”就算了,闻仲指使邓婵玉将姜子牙绑到自己身边实在是智商堪忧:绑姜子牙干什么,拿回封神榜就行了么!邓婵玉就该在西岐城杀掉姜子牙,一个人把封神榜送回来,这样就不会有人给西岐通风报信。
且闻仲明知自己不能动,就不要过早跟邓婵玉摊牌:我是骗你的。这不等于给自己多招个敌人么?
从影片开场闻仲对纣王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对眼前的新君不满意的——可能也听到点纣王杀父杀兄的传闻。所以纣王一开始请其出山时,闻仲一直强调自己是“先王旧臣”。直到殷寿继续发挥自己的PUA本色搬出“先王的基业”、“我将传位于你延续大商”的说辞,闻仲这才“不得不”上了贼船。

他对殷郊说:“我听大王的,最多被人说是愚忠;我听你的,那就是谋反。我宁肯愚忠,也不谋反”——这是个固守忠君思维、死不觉悟的悲剧形象,和中途觉醒的邓婵玉恰好相反。
7、姜子牙
姜子牙延续了《封神1》中的喜剧形象,前作中看不出他有什么智慧和谋略,这部里终于出现一些。

比如“见到大鱼”的夜袭计划和对姬发贪图小胜的训斥,并能预感到前来“投诚”的邓婵玉和一心复仇的殷郊都是“不安全因素”,但总的说来作为“军师”的姜子牙还是没能表现出高超的智慧。
“哎呀!我们在找闻仲,闻仲也在找我们啊”,真够后知后觉的——他就应该坚持己见不让邓婵玉进城。
另外,片中有个很鸡肋的将军角色叫“吕公望”,这个“吕公望”在历史上其实就是姜子牙。我不知道乌尔善新设计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为什么。
8、纣王和妲己
这部中:纣王的形象有所改变,而妲己还是老样子。
在《封神1》中,纣王对妲己是纯粹的利用关系,在泳池那一幕他就想除掉妲己,直到妲己提醒他自己还有利用价值才打消此念。而到了《封神2》,纣王对妲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妲己奋不顾身将他救活了。

“你身上的每一道伤口都来自于我”——救活算一次,得知妲己为使自己痊愈还在继续转移自己的伤口又算一次,两次过后,纣王终于有点“爱上”妲己了。
影片增加了殷寿少年时的“童年创伤”,其实《封神1》里就有,只是处理得比较隐晦。殷寿曾对姬昌说过:“你又知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对待我的”。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当殷寿从冀州城凯旋而归将苏护头颅送给帝乙时,帝乙连正眼都没瞧殷寿一眼。

帝乙就是个不会当爹的,生出殷寿这个儿子依然不会当爹;殷寿杀了他爹帝乙,殷郊又想杀了他爹殷寿......一代代就这么把悲剧延续下去。所以说乌尔善搞搞这些思想隐喻层面的东西挺在行,就是不会讲故事......
正因为殷寿从小就被最亲的人无视和伤害,所以当他听妲己说:“你可以再找其他貌美的女人时”,他才会为“终于有人肯为我着想”而感动:“不,你是不可取代的。”
殷寿的人物弧光增强了,但妲己的形象没有变化,还是为了报恩对殷寿死心塌地、“一往情深”。为什么呢?
看来,妖精比人更执着、更靠谱啊。

用户18xxx30
封神第二部其实和大话西游的结构差不多,内核都是悲剧和为爱牺牲,紫霞为至尊宝牺牲,邓婵玉为了姬发牺牲,非要自以为是的过度解读
用户18xxx30 回复 Erick 03-10 21:11
从桥上姬发唱情歌开始,邓婵玉就小鹿乱撞了,后来姬发救了她,她嘴上没说心里已经爱上他,正常男女的恋爱有何不可,天天就知道瞎叫[狗头]
Erick 回复 03-10 09:09
邓婵玉为的是守护百姓而牺牲好吧,她和姬发有过一句什么情情爱爱的誓言吗?只不过都是爱护百姓的同路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