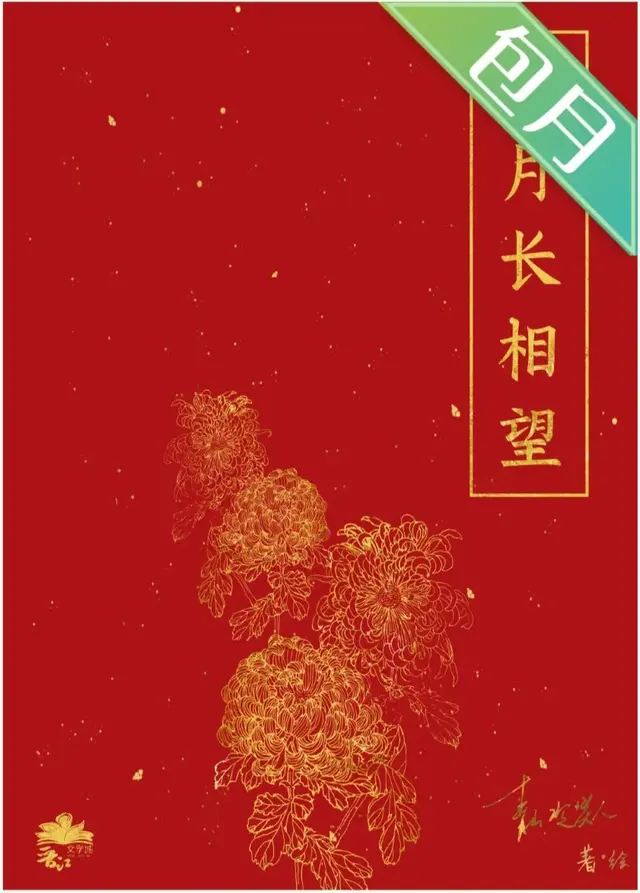“姑姑,大半夜的出去,万一碰上个毒蛇猛兽可如何是好?”梓舀巴巴地扯着我的胳膊往茅屋里走去。
“无妨无妨。你不是与我讲,弄出声响吓唬吓唬不就行了。对了,毒蛇是什么?”我被自己严谨好学的态度打动。问世间,哪里还有比我还好学的上神?
“就上次盘在梨树上的那根黑黑的,还咬了菜菜姐一口。姑姑你还说会咬人的就不是好虫子,所以在梨花林外面设了结界,不让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
我低头想了想,“唔,就是那个吸了菜菜的血还嫌恶心,一头栽倒在地上的那条黑虫子?啧啧!活了万儿八年,还没见过那样丑的虫子!还好菜菜把他给处理掉了,否则得吓死多少可怜无辜的花花草草……”我摇头着,鄙夷叹道。
“……那蛇全身打了七个结头,即使没有因为气血不通而死,也会活活羞愧死。如何吓花草?”
进了里屋,脱外衣的时候听见梓舀这句话,我又伸出半个脑袋,不解地问:“为何要羞愧?我觉得他那样还要好看些呢……”
“……”重新钻回被窝的梓舀已经俨然会周公去了。虽然修成人形,梓舀却比猪还嗜睡。掩上门,像是教导黑虫子一般,“我觉得那黑虫子你还是有点花样比较好看!黑虫虫你看啊,菜青虫身上一节一节的,毛毛虫也有白色毛毛装饰,你若那样简单,可不就突兀了……”
“蛇跟虫子怎么能混为一谈?若是给西青听到,一定会想抹脖子自尽。”
“当然能!你看,他们都没有脚、没有手、没有头,一直蠕动啊蠕动啊……”我拿手指比划着虫子蠕动的样子,转念一想,梓舀睡下,菜菜下山,还会有谁跟我说话?迟疑地偏头一看,原来是兔子。“兔子,你怎么还没回月宫?还是……”我挑眉轻笑,“你看上我这个主人了?觉得我实在太会体恤……”
“第一,我不是兔子,第二,不是外形相似的东西就是同一种族。更何况,蛇那么大那么长,虫子那么小那么短,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这兔子,见识比我还浅薄,连随意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都不知道。他没看见我的不耐,继续道,“还有,姑娘,兔子是不吃鱼的,只有猫才喜欢吃鱼。白芷不是嫦娥,是在下的妹妹。”这兔子,老是往本上神的痛处戳!本上神第一个痛处是不愿被人说天真单纯。第二个痛处就是分不清这些个外形相似名字不同的东西。
“什么兔子,什么猫,不都是白毛的!”
“兔子的耳朵长尾巴短,猫的耳朵短尾巴长,毛色也……”兔子一脸正经认真地解释着。
“那么复杂,怎么分得清?!”我白了一眼面前这不识趣的兔子,环抱着手臂坐下,觉得面子尽失,脸上有些讪讪。
“……”兔子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千秋万古的道歉的的话,想了许久也未想到。后来我气着气着就去会周公了。
我在一个黑无止境的地方缓慢摸索着,心里纳闷地想:周公的品位怎么跟他脸上的褶子一样,越来越俗不可耐。第一次见周公,在一处桃花林,大片大片的桃花,开得分外刺眼。第二次在深山老林,他说这般才能体现他的高雅品位……但这次,怎的换了如此抑郁的环境,莫非是他欢喜的人不欢喜他?
心里正数落周公的时候,听到前方有争执声。先听到一女子的声音,心里一喜,果然如我所料!但周公怎能因为女子拒绝他就跟女子吵架呢?这可不是君子所为。
前方有微弱的亮光,那泛着幽蓝的光不像一般的烛火。
桥的那边,一白衣女子背对着我,“孟婆,你这茶汤根本不能让人忘记前尘!”
孟婆?地府的那个孟婆?难道我在地府?
“姑娘,这一切皆是宿命。命里注定的,便是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正欲上前瞧个仔细的时候,一阵窸窸窣窣的窃笑声将我带离那个黑无止境的地方。
从黑暗突然转到光明,眼睛被光刺得有些生疼。我伸手遮住照在脸上的阳光,缓缓坐起身。看到一白衣背影,勾着脑袋蹲在角落,身子一抽一抽,像是在忍耐什么一般。梓舀从不穿白衣,菜菜倒是会穿白衣。不过,她不是去凡间游历了吗?难道提前回来了?“菜菜?”我出口试探。
那人像是沉浸在其中一样,对我的话充耳不闻。走近了才发现,那白衣身影不是菜菜,而是兔子。他捧着戏本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唔,兔子认真看戏本子这点倒很像我。我蹲下身,脑袋使劲往里探了探,想看看兔子在看什么戏本子。
这一看可就不得了了,这不是昨日被我扔了的戏本子么?
兔子边看边念念有词,“美得不似凡人?这霜凝本来不就不是人么?”
他这句话怎么听起来这么难听呢?怎么像是在拐了弯地骂霜凝?而这霜凝不正是本上神么?
我皱眉正偏头要问清楚的那瞬间,兔子也往我这边一偏头……
霎那间,只觉得唇上一凉。我抬起眼皮,近在咫尺的是兔子瞪得老大满是诧异的眼睛。
这情景,怎么这么熟悉?
对了,梓舀说的生娃娃的勾当!这兔子好生阴险,竟要我给他生娃娃!
虽然霜凝我修仙修了快万年,成仙后又一直隐居在瑶堇山不谙世事,但我却知道生娃娃有多疼!
有一戏本子里说过,一女子生产,相公在外着急地等候。屋里的女子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痛,一边大骂门外的男子,比如“某某,你个混蛋!”,再比如“某某,凭什么不是你来生?!凭什么两个人一起造出来的,却要……啊,痛死老娘了!却要老娘承担这份痛!”。门外男子因着急也语无伦次,胡乱安慰道,“娘子,下次你主动!或者你想要在上面也可以,我都依你!”“啊!”屋里的女子痛呼一声,然后扯着嗓子喊:“没门!你休想再碰我一根手指头!”后来的后来,那女子还真的不让那男子碰她。写戏本子的人说,‘不敢再与夫君行房事,这女子是心有余悸了’。心有余悸说的是危险的事情虽然过去了,回想起来心里还害怕。啧啧,本上神委实有才。(梓舀:姑姑,这不是你昨日看了一天的成语么?)我虽不尽然明白那女子为何心有余悸,但之前那女子形容行房事是欲仙.欲死的事情。既然连欲仙.欲死的事情都不愿再做,那真的是疼到外婆桥了。
思及此,我连忙退后,不让兔子啃我的嘴。兔子又没有救过我,我也没有说以身相许。是以,绝不能遂了兔子的心愿!
现下再瞧兔子,嘴巴微张,脸蛋红扑扑的,比起梓舀的红衣还略胜一筹。给我送戏本子的放牛小娃,当初倒在我梨花林外的时候,脸蛋也红扑扑的,额间全是汗,菜菜说小娃是染上风寒了。我看着他额上越来越密的汗滴,心想兔子莫不是染上风寒了?
我依样画葫芦地伸手贴在兔子额头上。之前菜菜诊断那小娃是否染上风寒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手还没贴上去就被兔子一把握在手里,他的手心全是汗,抿了抿嘴唇,像是下定决心一般,一字一句恳切道,“凝儿,我会负责的。”
凝……凝儿?!
万儿八年的,从未有人如此唤我。
“白公子?!”我正琢磨兔子说的负责是什么,背后却传来梓舀的声音,语调折了好几个弯,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什么。她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扯着兔子的袖子,求证道,“白公子,白公子,你方才是说要娶我们姑姑?!”我扯扯梓舀的袖子,她现在这般,委实不端庄,委实不像朵朱顶红。她不理会我,兀自紧拽兔子的袖子,不依不闹地问:“是真心的么?是真的要娶我们姑姑么?”
虽然我有点迷糊,但如今这般看来,一向聪明、有条理的梓舀比我还迷糊。方才兔子说的是他会负责,跟娶我没有半点关系。兔子的脸已经没方才红了,他看了看梓舀,又望向我,语气恳切,“当然是真的,只是还要看凝儿的意思。”
“姑姑定会答应的!”梓舀和兔子都看向我,眼神分外灼热。“虽然我家姑姑挺老了,长得也挺风骚,还喜欢看……那种戏本子,但实际上纯情得很!白公子你千万不要被表象迷糊!我家姑姑绝对是千年难遇的好媳妇!”
我实在不知道梓舀那番话是在夸我还是损我……
不过兔子真的要娶我?唔,这样我就知道行房事是怎么回事了,甚好甚好。可是……我皱皱眉头,摆手道,“不妥不妥。嫦娥现在才七千余岁,那兔子你定还要小……”
又是戏本子里写的,女子万万不可与年龄小的男子成亲。年龄小的男子容易出去沾花惹草。女子因为男子沾花惹草伤心不已,抛家弃夫,三尺白绫便了结自己。男子在外,纵欲过度,然后也死了。最可怜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了爹娘,只好出去乞讨,然后因为偷了一个馒头被活活打死。
啧啧!委实凄凉。
是以,我绝对不能让自己跟戏本子里的女子一样。嗯,重蹈那女子的覆辙。
“凝儿,梓舀姑娘说你只有一万六千八百岁,不才在下恰巧长你三百岁。”
“那便是一万七千一百岁,四舍五入一下,也是一万七千岁。”我挠挠下巴计算着,余光瞟见兔子的嘴角抽了抽,“那么……兔子你和我同岁。这么些年,总算碰到的同岁的了!”使劲挤出两滴泪,“总算体会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意境了,委实感动啊!”又见兔子的嘴角不住地抽搐。
“这下,没问题了,姑姑就算是答应嫁给白公子了。”梓舀对我偶尔卖弄卖弄文采的言语已经习惯了。
“等等!”我打断亢奋地就跟吃了黄花菜一样梓舀,“嫁给他我有什么好处?”对于自己的利益,我可是丝毫不含糊。
兔子还没来得及开口,梓舀就滔滔不绝地赞叹兔子,让我生出梓舀跟兔子一起生活了一千多年的错觉,“白公子温文儒雅,善解人意,有责任心,比姑姑大,又那么喜欢姑姑,还喜欢姑姑写的戏本子,最重要的是白公子是青丘的帝君,这样姑姑嫁过去就是帝后……”梓舀怕我不清楚帝后是什么品阶,复又挑眉笑道,“帝后可是上神哦……”
兔子若有所思,“唔,而且这样你就不用背着梓舀姑娘偷偷下山……”
“姑姑!”只能感叹梓舀的脸便的比天还快,刚刚还一脸谄媚,现在就怒眼相对。
就当没听见,就当不知道。
我眨眨眼睛,岔开话题,“兔子,成亲以后是不是就能行房事了?”不过,看二人这么不同寻常的反应,我觉得我这个话题换错了。急忙打哈哈,“行房事可以,但不可以生娃娃哈!”
话音刚落,兔子脸有红晕,梓舀无奈地捏了捏额角。
兔子说他不是兔子,而是一尾白狐,他还说他叫白柒。一时间,兔子多了两个称谓,我有些糊涂。反正也记不清,索性还是叫他兔子。我还没成过亲,不懂其中的礼数。为此,梓舀孜孜不倦地教导我。
“姑姑,白公子是个好仙,切莫红杏出墙。”我是梨花仙,想红杏出墙,还出不了呢。
“姑姑,嫁人以后就要守妇道,不要再和其他男子勾勾搭搭。”嗯嗯,恪守妇道。
“姑姑,对白公子要从一而终,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
……
已是深夜,万物俱静。就连屋外那些花花草草也收了精气神,垂着脑袋入梦。我坐在榻边,眼睛微眯,呱噪的嗡嗡声在我耳边盘旋,看着梓舀一张一合不亦乐乎的嘴,突然有冲动想拿浆糊将她的嘴堵上!甚是纳闷,为何比我小一万五千岁的梓舀懂得事情那么多。更为纳闷梓舀今晚为何如此亢奋,若是平常,老早就会周公去了。
平日最讨厌睡得晚,却得起早。昨夜被梓舀拉着说了一夜的话,但第二日我早早便醒了。因为,我要下山去了。
“离开家乡爹和娘,背起行装走远方。”这句话说明出远门是要收拾行装的!(梓舀:姑姑,你对这句话理解的真是深刻啊!)像模像样地在榻上摊平一方丝绢,东翻翻西找找,发现除了戏本子再无他。有些泄气,正想着要不将外面一干花草充当行李,兔子进来见一榻的戏本子,蹙眉问:“凝儿,你莫不是要将这些都带走?”
“不带不带。路上万一磕着碰着可如何是好。”这几十本戏本子,每本我都看过不下十遍。我视它们若瑰宝,生怕皱了、破了。那放牛小娃每隔一百年才送一本来,几千年来就只有这些。少是少,但怎么样,我都是个文仙,戏本子就是我的门面,自然要宝贝着些。说起戏本子,又想起昨日他说霜凝不是人的话。反问兔子,他盯着我看了许久,然后道,“你本来就不是人啊……你是仙子啊。当然美得不似凡人……”分明,他的语气里含有戏谑。
我撇撇嘴——本上神大人有大量,不与你计较。
出了屋子,茅屋两旁的花草身上都有水珠,不知是晨露还是因为离别的泪水。唔,总算没白养你们,我笑了笑,甚是欣慰。梓舀低着头跟在我身后,出了梨花林也没见这小丫头有所动静。梨花林外,她淡淡道一句,“姑姑,你且走好。”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折身走了十几步。虽然不能‘背起行装走远方’,好歹也得经历戏本子里难分难舍、抱头痛哭的情景。原来打算是梓舀跌跌撞撞地朝我奔来,抱住我的大腿直呼:“姑姑不要走!不要走!梓舀舍不得离开你!”
然后我伤心不已地说,“梓舀,姑姑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咬咬牙,又往前走了几步,微微偏头,却见梓舀已经转身。望了望天,也罢,不成仁便成义。我猛地转过身,胳膊肘撞到兔子,有些疼。但戏不能就此中段,用劲挤出两滴泪,跑得跌跌撞撞,哭得撕心裂肺,“梓舀,梓舀,姑姑舍不得你……”
看到梓舀回转的身影,原以为我期盼的生死离别的就要上演……但因为我入戏太深,不小心踩着裙角,砰地一声摔倒在地,只能跟大地紧紧相拥。
呔!委实悲壮。
兔子捏了个决,招来祥云。我伸出手指戳戳那软乎乎白净净的祥云,不免觉得惆怅——都是仙龄也差不多的上神,我怎么就没有自己的腾云呢?
站在云上,逗够了往来的小鸟,觉得甚是无聊,就寻了个话题跟兔子闲磕牙,“兔子,你有愿望吗?”未等他回答,我继续道,“我就想写本好看的戏本子,能流传千古就最好了,可是觉得自己学识浅薄,词到用时方恨少,每次一个成语就要想好久,想得烦了就不想写了,没有一次顺畅写完一章节的,唉……”
“未必见得,你记录那叔嫂二人行云雨之事不就很顺畅么?”兔子眼睛看着前方淡淡地道了一句。
叔嫂?云雨之事?对了,那草丛间的交颈鸳鸯!语气有些低迷,“那是因为自己亲眼看到,感觉来了自然就写得下去。这万儿八年的,我见过的女子就只有梓舀和菜菜,所以一直纠结如何形容女子相貌美丽……对了,梓舀和菜菜算是美人么?”
“梓舀……唔,我见过的女子之中,梓舀的容貌算是姣好的了。菜菜是?”
“黄花菜。也许是见多了吧,我见到梓舀怎么没有戏本子上写的那般吃惊?不是有个让鱼儿看见她的倒影,就忘记了游水,渐渐地沉到河底的西施么?我不是鱼,不知道鱼是否真的看见美人就会忘记游水……还有个叫杨玉环,她刚一摸花,花瓣立即收缩,绿叶卷起低下。羞花之貌?我是花儿,为什么我见到梓舀却没有羞愧的感觉。”挠挠脑袋,颇为不解。
“因为你比梓舀还要美上三分。”
“这张老脸看得都不耐烦了,再怎么看也不会生出那种惊艳的感觉。”话音未落,只觉得脚底下的腾云抖了一抖。
许是这云儿很少遇到我这般谦虚的上神,不由地就激动起来。
兔子说去青丘之前先要到凡间解决一些事情,我不住点头赞同——去凡间还能长长见识。见多识广,写起戏本子来就会格外顺手。
兔子收了腾云,我兴冲冲地走在前面。
唔,一般诗人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写一首诗来纪念。为了纪念我初次来人间,有感而发一下吧!沉思片刻,“这宫墙砌的真平呀,这地上的草儿长的真绿呀,这守门的侍卫胡子长的真黑呀,这城门的红漆掉的真好呀,这……”兔子好像开始适应我不同凡响的性子,再也不动不动就眼皮乱跳,嘴角乱抽。
凡间果然热闹。
有好多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奇玩意。比如闻着臭吃着香的臭干子。再比如深得我心的芙蓉糕,桂花羹,桃花面,荷花酥,丁香馄饨……望着天,好像看见九重天上那十二花神惶恐得几近狰狞的表情,我得意洋洋地一边冷笑一边将那些代表各花神的食物放在嘴里,恶狠狠地嚼上几嚼,然后心满意足地吞其入肚。再比如冰糖葫芦,就是山楂果子外面裹一层糖浆,一口咬下去,糖浆的渣蹦到兔子脸上,他也不恼,随手将糖浆抹掉,我咧嘴一笑了,“兔子,你是好人。”以前,吃油豆腐的时候,一不小心将油豆腐的汤汁溅到梓舀或者菜菜身上,她们都一脸嫌弃,说我邋遢……
“哎呦,好酸!”我龇牙咧嘴道。我算是知道为什么要裹糖浆了,这山楂果子酸得根本不能入口。
几千年前,屋前那片梨花林刚开始结果子,又酸又涩,个头又小,我觉得扔掉委实可惜,就全数摘了浸在蜜罐子里,百年后,取出一尝,甜而不腻,比新鲜的果子还要好吃三分。这山楂果子若是再浸上个百年,定十分可口。
正当我酸的龇牙咧嘴不亦乐乎的时候,瞟见一样我熟悉的东西——戏本子!我委实激动,撒着欢子就挤进人群。人间不愧是人间,戏本子种类繁多的让我都挑花了眼,什么《奴.妻》,什么《皇后媚史》……
啧啧!不禁感叹,凡间就是个好地方!这戏本子连封皮都比我那些要好看三分,不对,是十分。正想着挑那本朱红色封皮的《别样金瓶梅》的时候,就感觉身子被一股力道牵引着出了人群。兔子脸色略红,不自然地看着我,不置一词。我不耐地撇撇嘴,偏头再瞧那戏本子的摊子,已经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我不甚高兴地说:“兔子!你拉我作甚?你看,这下我挤不进去了。刚才还满口答应说要带我增加见识,眼下却……”
“我带你去看真正的戏,那可比看戏本子要强多倍。”
戏?我估摸着,戏就是照着戏本子演的,便欣喜地拉着他嚷嚷着要看戏。一处茶馆,刚踏进门,一跑堂小哥就热情地招呼着,“客官,今日您可来对了,今儿这出戏是由江南名角孔心文出演的。”兔子给茶馆的跑堂小哥一锭拳头般大小银子,那小哥乐呵呵地招呼我们上二楼,进到一间正对着戏台的雅室。小哥上了一壶茶水,一碟瓜子,一碟花生,便遂掩门退下去。
“孔心文是谁?”方才没问是怕给兔子丢了脸面。
“不清楚,但这出戏定会对你有帮助。”兔子抿了一口茶,轻声道。
“哦?是有以身相许还是云雨之事?”我认真地看着兔子道。
他握着茶盏的手抖了一抖,茶水洒出半盏。模糊地说:“有以身相许……”
“哦。”那不就是梓舀说的生娃娃的勾当,那不就有啃嘴。嘿嘿,终于能亲眼瞧瞧这戏本子里常常出现的场景。
一阵锣鼓声后,幕布便打开了。故事开讲:一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这崔莺莺年方十九岁,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生。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本是欣赏普救寺美景的张生,无意中见到了容貌俊俏的崔莺莺,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与寺中方丈借宿,他便住进西厢房。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但崔莺莺执意非君不嫁。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莺莺小姐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为张生送行,她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长亭送别后,张生行至草桥店,梦中与莺莺相会,醒来不胜惆怅。张生考得状元,得知此消息的同时也听郑恒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
这戏,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却始终没等到啃嘴的场景。等着等着就开始犯迷糊,脑袋不住地晃悠……半睡半醒,我嘴里不住地呢喃:“奴家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
一旁的白柒暗自腹诽:绝对不能让她再看那些戏本子!